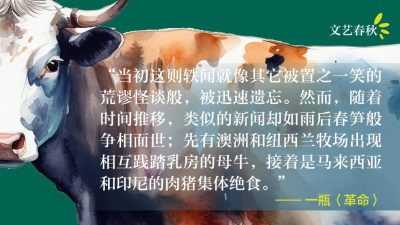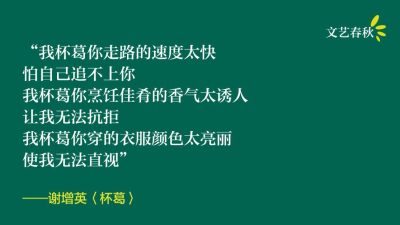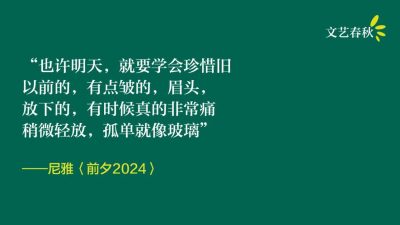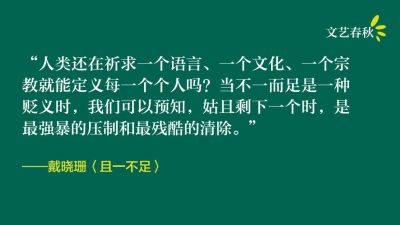在生活安定、胶价平稳中,我家收入渐渐平衡,家中成员除了幺妹,都在生产线上拼搏。大家半夜出门,头顶挂一盏煤油灯,像萤火虫徐徐飘忽。我在早上等妹妹醒来用完早餐才出门,那时刻天亮旭日东升了。我没走远,包揽住宅周围的胶树。
一天下午,工作回来大家坐下闲聊,忽然有个中年妇女满脸泪痕跑进家里,投进母亲怀里放声号啕。大家都被突发事件惊动,尤其我和二姐更感莫名。
ADVERTISEMENT
“金兰,乜事,唔使哭!”母亲比较镇定。听到母亲把搂在怀抱中的妇女叫金兰,我知道来者是大姐。我未出世,大姐已被送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金兰只是一个家中众人嘴边记挂的名字,一个在我脑海回旋已久的亲人身影;经常渴望的那个身影,却在啼哭声中翩然出现。
那年我9岁。我9年的牵挂,见到时却是因家变涕泗滂沱的大姐。原来是大姐遭受正房欺凌,忍无可忍之下决定出走。
我上前叫一声“大姐”,一副既陌生又熟稔的脸孔,带几分父亲高挑的身影。我也忍不住眼泪,姐弟拥泣好一阵,情绪稍微稳定之后,大姐从衣袋掏出一封“休妻”短笺,父亲接过读完,安慰说,“唔使哭,咁样重好,自由番!”我暗忖,大姐的不幸是父亲你一手造成的,当年送走就注定了大姐坎坷的人生。
对此不体面的家事,父亲永远保持沉默,不敢向外吐露。到覃家从祖乡重返胶园时,我们物归原主,离开那片胶园和临时的家,搬到斯那洼了。此次大姐走出覃家,促成我跟大姐缘聚。亮丽的青春遭受人为的折腾,大姐的创伤令家人愤懑与同情。年届三十五、六的大姐,依然保持娟秀的颜质,遗传着母亲坚韧的耐力。几十年与我们间隔的深谷,仿佛刹那间铺平了。分衿既成定局,大姐暂且住下来,随我们一起割胶,勤快帮忙家务,日子过得也顺心愉快。
有天我发见大姐的额间有粒豆大的疤痕,我指着问她,“是小时顽皮给阿爸凿伤的吗?”父亲气愤的绝招除口吐三字经,手屈五指向我们的头部连环叩凿泄气,是常规。
“唔系唔系,系我发冷发热,畀阿表用艾火烧成咁样,脱唔得啦!”
“好啊!阿表留个唛头畀你,真系抵哦!”我调皮说完就跑。大姐追过来,学老爹屈伸五指佯装要敲击我头顶。
这叫我想起父亲的艾灸医术,使我心惊胆战的土方医疗。我生病常隐瞒,就怕父亲那艾灸绝招;可那年代医疗落后,又偏居郊野,左邻右舍有病就来找父亲。看来老爹真有点功夫。
我们姐弟都在父亲的艾灸治疗下长大。小时候一听到艾灸,我的眼泪就自动流淌了。所以病来总想逃避,或者伪装。
但疾病来袭,再装也难躲父亲的法眼。他先悄悄叫母亲切好姜片,两人合力把我按在床榻,把我双手弯在背后,用一支木棒穿过弯曲的部位,将姜片贴在穴位上,将捻成针形的艾草立在姜片中间,用香支点燃,初时没甚感觉,火花艾草渐近姜片就感到痛,将燃尽时痛到我肺腑翻滚,泪眼簌簌而下。
我当然挣扎,还高呼狂叫,但并不能稍微减轻痛感。父亲不因我连连呼痛而改变行动,还怒气呵责:“再吵,再吵我就烧多几柱!”我常被父亲的赫赫气焰镇住,忍耐片刻。母亲较为体恤,“就得啦!就得啦!”不停安慰。口中虽说“就好”,但每次起码要点四、五柱艾粒才罢休。等我从板床上翻身的时候,背部好像遭火炬烘烤一般。也算幸运,艾灸没在我身上留下任何疤痕。
艾灸留下疤痕,父亲推说那是失手,有时姜片切得过薄,艾柱燃尽没即时弹走,以至灼伤了皮肉。父亲治愈不少亲朋戚友的病痛,都没失手过,偏偏在大姐无法掩盖的额角留疤,这会不会是大姐命途多舛的征兆。我心想这或是冥冥中的定数。
也许我比大姐幸运,腰背和肚脐灸诊后完美无疤。
大姐克勤克力,割胶家务都自动帮忙,一家其乐融融,我年纪小想不通父亲为何要她改嫁。大姐和我们生活了半年,就由媒婆介绍,与杨家结褵。大姐甫从一个恶梦中逃离,双脚又要踏进另一个婚姻的门槛,试探惘然的未来。依父亲的措辞,大姐还年轻,需要一个安心的家,一个可依赖的男人。媒婆拉了线,男士是鳏夫,有多名子女。相约见面后,大姐也满意,就缘订嫁娶了。
大姐出嫁那天,清晨5点忽然风起云涌,接着狂雨渀泻,在天昏地暗里母亲毅然依约,一手攥着我一手撑雨伞,大姐举伞随后,拧亮手电筒,赶去附近一间颓毁坍塌的废宅等待姐夫。我异诧大姐为何不从家里出嫁。父母亲都说依礼俗,改嫁若从娘家跨出,有损风水。我质疑风水之言,我家遇过好风水吗?我们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不都是崎岖蜿蜒的满途荆棘、风霜雨露,日子何曾见过风和日丽的蓝天!
那年代资讯落后,尤其偏居胶林野地,时间约定往往是一个长长的忍耐。雨帘从陷塌的罅缝漰漏下来,狂风飕飕地咆哮,油伞下的我们仨蜷缩一团,眼眸紧盯前面的荒径,期待照顾大姐的那个良人早点现身。
天将微亮,风雨未歇,迷蒙里有一辆脚踏车冲破雨帘向着陋宅踏来,果真是迎娶姐姐的新郎。他把脚踏车推进陋室,满身湿透了。他抖了抖衣襟,叫一声“阿婶”。母亲牵着大姐上前,隔在两人之间频频细语,咆哮的风雨阻隔了我的视觉,我听不到他们的对话,想无非是夫妇和顺、凡事洽商之类的叮咛。我蓦然发现母亲眼瞳淌出两道奔流,我难以分辨是雨帘还是母亲临别的泪珠……
我噎咽,一阵悒郁自心头涌起,但强忍住不让眼泪流下。
风雨狂态依然,但4个湿漉漉的身影仿佛凝住,静止不动。姐夫终缓慢地推动脚踏车,大姐撑起竹骨油伞,遮在姐夫头顶,两人的影子渐渐在荒径里变小,变小,最终消失在潇潇的雨声中。
那两个风雨中相随的身影,像常青树,一直在我心中生长。
* * *
杨姐夫住在北霹雳宜力的高拉雷(Kuala Rui)新村,从事农耕,种植烟草与蔬菜,虽非富有,三餐温饱,难得姐夫却对大姐甚好。姐夫知书识礼,也爱好文学书籍。新村背后有道很长的铁索吊桥,吊桥下是滚滚泱漭的霹雳河,直泻千里。当时从江沙到宜力的公路九曲十三弯,但读书的时候每到放假我都要去高拉雷,在姐夫家里小住三几天;顺便去走一遍摇摇荡荡的吊桥,享受那份惊险的刺激。
大姐为杨家添了二女一男,生第四胎时不幸因失血过多,又未能及时送医而逝世,说来也是悲剧告终。大姐的人生经历的皆为荆途,没有过片刻清闲,莫说享受安逸了。
大姐未成年就远隔亲情,不曾享受家庭温暖,自小失去童年的天真快乐,被送去身分暧昧的家庭中蹭蹬。大姐终生遭遇波折,以至遍体鳞伤。若说寄养是父亲的一时“失手”,那大姐脸颊上的艾灸疤痕,便为父亲的再次“失手”。两者都在大姐身上引起大伤害,烙成一抹挥之不去阴影。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