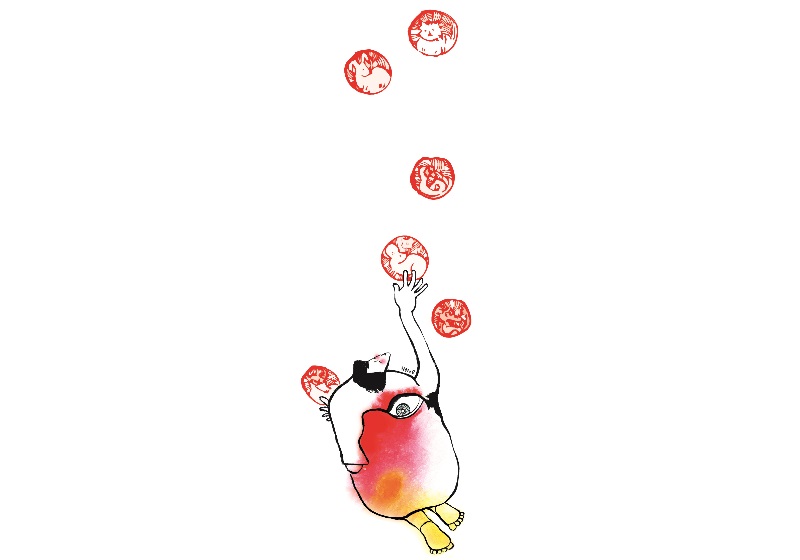
7
柔佛因为王储大力推动足球,下重本打造柔佛球队JDT,一连夺下好几个国内联赛冠军,甚至一举登上亚洲足协杯冠军宝座,整座城市挂满了球队的巨型海报,妈妈档周六晚也不再播放英超、意甲,全心全意直播JDT的赛事。拉庆体育馆主场比赛时,球迷更是挤爆球场,热闹非凡,新山一下子变成一座狂热的足球城市,一个柔佛民族的概念也借足球还魂,仿佛冥冥中,王与子民的神秘连结。
于是搭德士和马来司机又有了新的话题。
有个司机大叔这样形容梅西:sedap。意思是美味,一个字,将梅西无人能及的天才,与美食挂勾,真绝,我喜欢这样直率的修辞法,足球风格就应该是放进嘴里,直观地(甚至是不理性、暴力地)感受,直观地喜欢或不喜欢。
就像《食尚玩家》,浩子和阿翔形容食物,如果他们开始斟词酌字,顾左右而言他,那东西大概就没什么可吃的了。有一次他们到一家烤肉店,老板祭出什么澳洲进口五花肉,烤好两人试吃,浩子就开始形容口感很不同,试图勾勒层次,阿翔则在一旁捧哏。接下来,老板烤了雪花牛肉片,浩子和阿翔才放进嘴里,眼睛都爆出烟花来,整个小宇宙像炸开的红炮辟哩啪啦绽响,连说“好吃”,有些事,骗不了人的。
或是“makan angin”这样的形容,把旅途吃进肚子,贪婪而且强烈的欲望,“走,我们去吃fong。”
足球于我,启蒙语言其实是英语。英殖民留给我们的,除了《内安法令》《刑事法典》377条款,还有英语、共和联邦运动会和英超联赛————身边都是利物浦、兵工厂和红魔的球迷,世界杯周期,自然也更倾向于支持英格兰,看球赛转播也都听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英国评述员,那英伦风味的形容词,spectacular、unbelievable、sensational、magnificent…………太多太多,总学不来,却很少听到有人用delicious啊,我斜眼掂掂那个字的量,还真不错,梅西的球技,当真sedap。
8
Grab司机终于逮到机会,问我是不是本地人。
我说我是新山人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也许是我说话有点台湾腔的缘故,更何况我说话的时候少了叻啦咯这些,关键的语助词。
嗯,可能是看太多台湾综艺,也或许是读直排书的关系?我自己也说不明,胡乱找个理由搪塞:可能是因为采访工作发问时逼自己字正腔圆,才会习惯成自然吧。又或许是因为我不谙方言的关系。
不过我知道,腔调不是一天形成的,那需要反覆言说,反覆练习,口腔里那些半自主肌肉群————舌头啊,软口盖————慢慢积习成就。
于是我们习惯凭声腔判断,甚至分类人。
在新加坡当记者,尤其如此,能讲流利华语者,尤其年轻人,一定先怀疑他或她的出身,琢磨对方的南腔北调,带着有点抱歉又小心翼翼的语气探问:“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总要如此中断对话。我也经常被这样问到,尤其在中国大陆,在台湾,经常被“哇!你怎么会说中文?你不是马来人吗?”我唯有不厌其烦地解释我的出身,我的教育背景,我生活经历的一切,因为我知道,我的腔调放置在任何时空都显得格格不入,就像一头四不像,误入高速公路,被飞速来往的汽车鸣笛呼啸逼问,哆嗦地滞留在隔离岛上,两头不着岸。
久而久之,我竟享受起这种异乡客的窘态,好像这样就可以比较不负责任地存在了。
9
在新加坡,能说方言的年轻一代就更不可思议了,一旦邂逅,就像濒危动物一样珍稀。
我曾采访一个少年,父亲是英校生,母亲是华校生,福建话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对孩子,夫妻俩无意间三语齐发,于是我问少年:你的第一语言,你的思考语言是什么?他眼珠子转了转,面无表情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少年的外公外婆却又只能讲广东话,一家人沟通起来,语音声调相当复杂,就像几首歌的mashup,有时厘不清,有时竟意外的好听。少年努力学广东话,想跟外公外婆沟通,他说,当他终于掌握了语言,才发现祖孙之间的隔阂,原来不在语言。他好不容易懂得广东话了,面对外公外婆却无话可说。
那种苍白和无力,我颇感同身受。
另一次我遇见一个少女,她的华语完全不行,却报名了广东话初级班。和她交谈才知道,原来婆婆患上阿兹海默症。平日与孙女用英语对话的老婆婆有天忽然像是大脑某个机件松脱了,某发条不再运转了,从此再不讲英语,张口闭口都是她原生语言————广东话。少女告诉我,婆婆原是位经验丰富的英文老师啊。
(如果有一天,我也患上阿兹海默症,我的语言系统会如何瓦解?哪一块最先消失?哪一块最最核心?也许根本不必疾病,世故就足以消磨天真,不是吗?疑问变少了,好奇不见了,剩下不耐烦和肯定句。)
女孩爱婆婆,想要把握与婆婆相处的最后时光,亡羊补牢,才到会馆报名上课,想从另一个语言,另一角度,重新理解婆婆,为婆婆捡拾一天天剥落的记忆碎片。
10
关于母语,我有一套歪理。
“当你被问到身份证号码的时候,脑海中自然浮现的语言,那一定是你的母语。”
无论在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面对公务部门,我都无法顺利背诵我的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我总无法将数字自然转换成英语或马来语,瞬间口吃,慌得像是罪犯一样。有一次在新加坡红山租的房子和同屋友人一起在客厅看戏,两个制服警员上门宣导恐怖袭击防范相关资讯和电子资源,顺便做做检查,跟我要了名字和工作证编号,我本在下班回家放松的状态啊,突然间来了警察,加上要用英语念出工作证号码,突然有种不安,我慌乱地说了一串数字和头尾字母,一回头就隐隐察觉不妙,果然没多久警员又回来了,要复查我的证件,我才赶紧到房里取证,证明我只是一时错口,但我心里明白,那不仅仅是一时的错口。我仿佛变成着这座城市里潜伏着的恐怖分子,随时爆炸。
前辈同事告诉我,老一代人还有一种“方言计算机”,算数只能用母语。
“我嘛,生肖的话,只会用潮州话背:一鼠、二牛、三虎、四兔、五龙、六蛇…………都是我妈教我的。”他说。
我的生肖记忆却只有标准华语,然后是卡通版的传说故事:猫被老鼠骗了,最后排行十三,无法成为十二生肖代表,于是猫咪恨老鼠入骨————那是胜利者才能上正传的传统啊。(待续)









fecddf19-ef76-4434-8507-e74d7784da4b0ccbf16e-a852-4818-8eb5-5a675835b2e5.jpg)
403a8220-f10a-4dde-a467-e4451853e7c3cd1755be-02af-4d31-ac0f-1f896a000765.jpg)
7a0947f3-cf5d-46c2-b077-0e21c7b97f162fad18c7-7a5a-40a1-975f-35c041fd0ca8.jpg)
c3c689d0-e3dd-4455-84d6-18ff96c0439f183f5f88-b397-43b1-b9bc-fed917a5b493.jpg)
692940bf-f699-4886-99a0-d51294b0c5a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