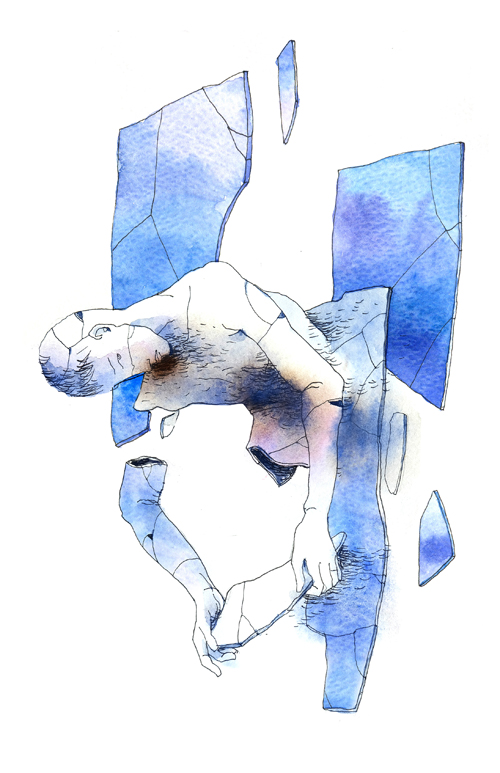
最近养成读诗的习惯,每天早晨或夜晚临睡前关起房门,一个人坐在床上念两首或三首。我发现这和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一样的,能够抵消生活的浮躁和不必要的焦虑。我的第一本诗集是辛波斯卡的《我曾这样寂寞生活》,九十八首诗,一个半月的时光,虽然很多时候读不懂那些诗句,却还是能够沉醉在诗歌节奏的跃动和她们所传达的对生活的爱之中。这也是诗歌的魅力和魔性吧,即使不懂,也还是会深深受到感染或挑动。音乐也具备这样的魔力和诗性。我曾见过一个男人,他一边弹吉他,一边用对我来说无比陌生的西班牙语悠扬地念诗,那琴声和那听起来无比忧伤的诗真的会教人泪流满面。
因为不会写诗,所以在看到诗人在一个很短的句子里使用了两个(看似)毫无关联性、使人一头雾水的意象时会心头颤动,仿佛自己也随着那两个意象的跳跃而跳跃。在辛波斯卡的诗里,这样的组合有蝴蝶和熨斗、帽子和云的碎片、护身符和橄榄核等等。有时候则是重复的句子开头和递进的诗句使人感受到诗人对生命的思考、态度或追问。那些排比和跃动如小鹿的词句,底下却流淌着一条静谧的河流。
你看这首〈种种可能〉:
“我偏爱电影。
我偏爱猫。
……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
我偏爱不去问还要多久,什么时候。
我偏爱惦记着可能性,
存在自有其理由。”
还有那些“也许”、“为什么”和“既不是……也不是”,种种这些看起来像是碎语(絮语)的呢喃,却强有力地散发着哲学谜样的光芒。
说起意象,我总是会想起大学时代的诗歌课。我是念中文的,那时候我们的学院里有一两个(公认的)诗人,他们是谜样的存在,有时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一次诗歌课上,老师给我们念一个学弟的诗,那是首关于什么的诗歌我已经记不清了,却永远记下了老师强调的诗中的意象——兽衣和御寒。“用兽衣御寒”,那个诗人学弟这样写。这真的是冰寒彻骨的一组意象,我至今还是能够清楚感受到当时透过词语将教室紧紧围困的寒气(空调确实也很足)。
我们还读夏宇的诗。她的那些文字游戏一度使我们大惊失色。毫无意外,为了交作业,我自以为是地躲在宿舍里写下了今生仅有的两首诗,那都是最最蹩脚和不知所云的诗。
我去过波兰,可惜那时候还没喜欢上辛波斯卡,不知道她被葬在克拉科夫。关于死亡,辛波斯卡这样写道:“死亡?在你的沉睡中到来,这才是它应有的样子。”她后来真的是以这样的方式经历了自己的死亡。这是一种幸福吗,于不知不觉中死去,甚至来不及回眸或眨眼?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华沙街头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辛波斯卡的诗集《结束与开始》,想将它买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朋友。可是,当他翻开诗集时,他读到了〈一见钟情〉,这首诗的主题正好和他正在拍摄的《红》很接近,于是他决定将诗集留给自己。后来普莱斯纳为电影配乐,那首〈一见钟情〉的歌词就是这首诗。
我喜欢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当我在辛波斯卡的诗里隐约瞥见那些似曾相识的对命定或偶然的思索时,我的灵魂也在颤抖。“如果从未相遇,他们确信,他们之间将什么也不会发生。”可其实他们曾经无数次擦肩而过,曾经在不同时间碰触过同一个门把,在同一个场所聆听同一首曲子。还有还有,当女主角瓦伦丁在红色幕布前摆出那副哀愁的神态时,谁又曾想到在即将到来的某一个风暴天,她会在真实世界的一场海难后露出一样的愁容,背后恰恰也是一片红色?此时此刻,她又再次和那个年轻法官奥古斯特擦肩而过……
Déjà vu。我们经常这样说。或者是似曾相识。“这个妹妹我好像见过”,当年宝玉见到黛玉时也这么说道。这些事情基耶斯洛夫斯基和辛波斯卡都曾经思索过,并深陷其中,如今我们也一样。
那些诉说诗歌的美好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是贾木许的电影《帕特森》。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叫帕特森的巴士司机的平淡生活。他每天重复同样的路线,晚上遛狗和去同一家酒吧喝啤酒。他写诗,随身携带一本记事簿,默默地观察周围的世界和聆听乘客之间的对话。
帕特森的读者只有妻子劳拉。但这并没有使他放弃诗歌。就像辛波斯卡说的,诗人最终是要关上门,在寂静之中面对空白的稿纸,耐心地守候他们的自我。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对一个极其卑微的读者而言也是如此的。我这样关上门,寂寞地读诗,感受那些诗句一次又一次的轻拂,在一个寂寥的早晨,我竟在瞬间真切体会到诗人所写的——“不再确信重要的事物比不重要的更为重要”。









fecddf19-ef76-4434-8507-e74d7784da4b0ccbf16e-a852-4818-8eb5-5a675835b2e5.jpg)
403a8220-f10a-4dde-a467-e4451853e7c3cd1755be-02af-4d31-ac0f-1f896a000765.jpg)
7a0947f3-cf5d-46c2-b077-0e21c7b97f162fad18c7-7a5a-40a1-975f-35c041fd0ca8.jpg)
c3c689d0-e3dd-4455-84d6-18ff96c0439f183f5f88-b397-43b1-b9bc-fed917a5b493.jpg)
692940bf-f699-4886-99a0-d51294b0c5a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