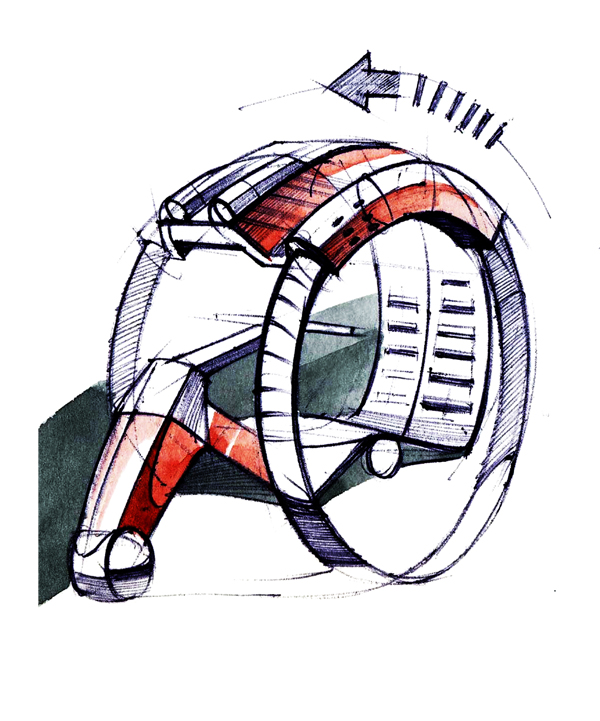
那是实一记得的第一辆车子。首先是车牌号码,数字连同他始终觉得难记的三个字母,用力想一下就能记起。然后是型号,日产Toyota Corolla LE,白色,总觉得过于四四方方而呆板的车。是后来才予以全部印象的,一开始只认得形貌而不贡献更了解它的兴致。最后一次见它,记忆装多了一个人,以及出于装满容器的本质而不断灌进车里的江水,从此他想起那辆再也不见的车子,是连人及水一并看见的,三者合一沉入深深的记忆之海中,海马回带着漂,有时浮,更多时候是漂到别人的脑里去而被唤醒的,比如父。
父告诉他人淹死了的时候,那辆车也跟着一起报废了,父唯有以低价卖掉它。他后来从相簿抽出一家人站在车子侧前方拍的合照,倒不是怕一家人触景伤情才拿走的,也不是怕自己忘记什么。车子的白很干净,人人笑得极衬那白,明亮亮的场景,直到后来连时间浊黄了,它好像仍不受影响的白。他把那照片钉在房间墙上小小的软木布告板上,和一堆游戏海报、新闻剪报、相片贴在一起。死掉的人是姐姐,当时姐姐开着那辆白色LE冲进江里。他想像姐姐在水里打不开车门挣扎的样子,瞪圆了眼睛像平时怒气满满和他吵架的样子,最后渐渐无力的样子。明明什么也没看见,可是光是想像,便看完了。
姐姐大实一五岁,实一十岁那年两人偷偷开父亲的车出去,姐姐开的车。江边公园是世界的另一个世界,炎热午后父亲在睡,少女儿童在边界滴着汗望着江水晃摇,眼中耀出鳞片闪闪,打开入口一般。看了一会他掉头跑去荡秋千,姐姐沿着江边揽抱太珍贵的风,偶尔看看他,在离他不远处走走停停。姐姐喊他回家时,他已经玩遍滑梯、摇摇椅、摸够公园里奇怪的姓氏石,坐回轮胎做成的秋千,硬是不走。姐姐先去开车热引擎(已经够热的天),他听见发动引擎的声音,马上起身跑向车子,未来得及喊出一个追得上的音,车子抢先发出巨响,也许是那平时总是吱呀吱呀的栏杆先出声的,接着是江水加入的和音,合奏出大声的噗通,被栏杆打痛的车子冲向水的温柔里面,像是为了止痛而刻意摒息的伤口,关闭入口一般。
从此实一觉得车都是离他很远的事。那年不过十岁,便听从了命运的恐吓。警告,只有大人才可以坐上那驾驶的宝座,握住方向盘的手、手排档的心。他仿佛不参与车的怀抱,更多时候是望窗外的风景,专心看前面那是掌权者的视线,好像为了陪着走一段路,也不大为了目的地。丢了一辆车,生活很快又催人开往前方,家里不得不买第二辆车,后来每一辆车父都驾不久,几年就换。说起来第一辆车开了五六年吧,几辆之中算久,也沉得最深。然后便是现在父开着的车,是第四辆,实一十七岁时买的,一直开到现在。
十七岁是合法考车的年龄,实一身边同学一个个趁着假期或打工或考驾照,实一只是按兵不动,关在狭窄房间,上网打游戏;或把攒了的零用钱带上,到游戏中心投篮、开模拟摩托,以及开跑车,拼命地撞,拼命地翻,拼命地摔,输了又投币。荧幕外开车依然是大人的事,荧幕里戴上安全帽看不见脸的赛车手背对着实一。现实中,实一总是坐在车子后座看向右边车窗;在游戏中心坐在荧幕外看向前方,只得到一个后脑。
一家人坐进车里的时候,实一偶尔也看父的后脑,父说话时则用倒后镜看他,借用车辆的眼睛扫过他,再回到跟前的路。两人的路似是不同,实一的路像永远在旁边,总是更接近转弯处,转着就回到原点。姐姐没了后,他常想起在公园玩的那天,姐姐的视线随着他荡秋千玩滑梯。他觉得,自己从此缺了一个看他后脑的人,自动成了最后一名。最后一名走的路缺了一个赶紧,实一总是慢吞吞的,漫漫想着考车的事,要,不要,要,不要。要,却更多是已经在母胎中就灭绝的念头,以水阻断而造的死路。强大的经历总是强大,它一下就让实一害怕上两件事,一是开车,二是下水。炎热午后同学约去泳池浸水、看女孩,实一也不怕同学笑他是旱鸭子,说自己要当小白脸,要睡觉。关于水的游戏,比如水枪,以及水中套圈游戏机,实一以前常玩,后来想着想着就慌,水像子弹会要人命,水是牢笼要把人给紧箍着困进圈套。美丽的甜甜圈,可口的汽水,都是陷阱,催促你玩,你玩,要你往尽头去看它的完结。
有时候,实一会装作不经意地问:要考车吗?双手和双眼都尽可能自然地翻阅报纸。父亲总说:你自己看看,多么危险,每天都有人出车祸。他明白自己是站在父这边的,就像照片中,车外的人才站成团圆;开车,却各自有去路,他去上学,父去上班,分成别离。于是他不说话,他知道他的沉默就是安全带,不让尼斯湖水怪用影子若隐若现挠得人心痒,却又不拿真身浮出水面,让人失望伤心。在副驾驶座上,从左边拉长系紧的安全带,护住了实一的心。
●
后来实一做了个梦。喜欢的女孩开车载他,两人却翻了车。车子从中间撞开左右两车,然后是墙,冲击之大,车子往回弹,就翻了。实一带汗醒来,花了一些时间确认自己在大学宿舍,热,换了衣服骑脚车到冷饮店去写期末报告。他点了雪花冰坐在靠墙座位,座位对着大门,也对着冷气口,实一偶尔抬头看玻璃门,都是外面的人撞进来的时候,等那门的摇晃安静下来,实一才觉得店里是一辆大型的休旅车内部,冷风习习,有歌听,有挡风玻璃,可以坐很多人,吃进口里的是冷,吐出来的气息也冷。黄昏后,他带着店里的余冷回到宿舍房间,感觉自己有了方向,他伸出双手假装自己握着什么,直到拿起电话,告诉她,期末放假我去考驾照。
回家那天,实一就和父说了。父没说什么,指着自己的车说,开开看。那是实一第一次坐上驾驶座,父则坐在副驾驶座,一个个步骤教他,那是油门,那是刹车器,那是雨刷,那是打讯号灯。在大学不是没有坐过同学的车出去玩,也观察过别人开车,但自己实际坐上那个位置后,却像婴儿第一次伸出双手,抓得住的尽是没有。方向盘抓住了,先要退车,一退、踩油,转弯,马上就撞了花盆。搞错了方向,倒退时要逆向地想。实一慌张解开安全带,下车看车,没事,看父,看了父察觉自己的怕,心虚收回眼神看地,又是旁边的路。父只是叹气,说赶什么呢,开车不能毛毛躁躁。实一想,他说的是开车不能早,正如十七岁时,父觉得没有考车的必要,也许他觉得现在也是。
实一还是去学车了。笔试顺利过关后,就是实际开车,包括留下最初恐惧记忆的退车,以及停车、上坡、转弯,以及开世上各种路(Z字型、S字型、T字型路)、换档。实一坐在冷气车厢里直冒冷汗想,开车真是一件太考验技术的事。几时要换档,听引擎声;几时可以转弯,看感觉。久了就会了。师傅总是酷酷的,又有点老气横秋,说出这些仿佛说了几百万次的答案,有时又笑嘻嘻安慰他,放轻松放轻松。实一觉得,教车师傅扮演另一个父亲形象,那另一个有相反的意思,和他站在同一边,坐进同一个机制,要让他走出双腿的极限,顺利上路。那些话带着实一往前开。
有时候实一错觉,开车其实是在语言范畴里的事,会不会开车其实不真的是行为上的,而是从语言说成的,别人问,你说什么是什么。父陪着实一在自家附近练车时,实一总是不小心就开出错误,吃到别人的路、太早转弯、停车格装不好一辆车。他想像笑话中的场景,有人频频追过他后会摇下车窗问他:少年人,你会不会开车?(快教我怎么踩刹车)而他会怎么回答。(是不是答会,就变得会了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实一想,不是笑话,如果我会开车,对方是不会问问题的。大家开自己的车,互无照面而共享一条路,安静的,互不干涉的,除非是实一逾越犯规。没有人问,可是实一还是开不好车,好像神没有说要给,就得不到。
说话的人唯有父。父总说开车心静就会定,要静,却又忍不住纠正实一开车的方式、速度,甚至实一未行动就被指引方向。语言,是语言一早奠定实一开不了车,即使坐上驾驶座,开车的还是父。始终说话的人是开车的人,说话的人决定了后来事。
父总说,车考来干嘛,你上个学开什么车,考了不开很快又把车技荒废了。买车也不到时候,等工作后再说吧。开车的危险你不是不知道,报纸看看。父的叨叨絮语刀刀致命,把实一的脾气从血管皮肤砍了升天,在空气中爆破。其实那也不是气,更多是待冷的水蒸气,看错了权当是熔岩,其实也并不热,是两人准备进入冷战前那欲滴的汗。实一知道,等散场剩下自己与自己对峙时,现出原形的不过是泪珠。每每在这种时候又想起下沉的场景。那时,他竟眼睁睁看着车子下坠,也未发出求救,哪怕一声。直到车子淹没,实一眼里全是江水,是望久了,江水才会全跑进他的眼睛。后来每一次哭,那水就从眼里筛掉一些。要哭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水都还给世界呢?人体内有70%是水分,实一觉得自己超出那个。实一想,多么污浊啊,那些江水,用自己的泪水去掺也洗不干净,即使那车和那人活在他眼底,他却永远不能清楚看见了。一滩死水永远活在实一眼里,水起初动的时候,他的观望就承接住那死的蔓延,那个下午双眼渐渐死去,他只能动也不动死盯着,从此重复流转反噬的殇。
双眼有死角,开车从此有盲点,后来连耳朵也渐渐封闭。父所有的话语,他都明白,但那与其说是担心,更像是诅咒,对实一预设未来的灾难。实一有时不禁觉得,如果学会开车倒辜负了父的苦心,想想自己竟也如此扭曲,又潜入深深水底。开车是风,水底的漩涡,有时竟靠一点心底的风,添一点意念就卷起海啸。陆地的水都是天上给的。下起暴雨的时候,实一用雨刷滋滋扫走一些眼前的水,然而那些旁敲砸碎在右边车窗的滴答总叫他分心,看一眼就错觉似地回荡成眼里的泪,让他投向车镜的视线,总是盲目,盖掉路上分线,甚至淹掉整条路。实一于是更喜欢晴天,闷热上午即使能用皮肤听见灼热的阳光烧烤地面的声音,只要踩下油门出发,不只车里凉快,也为世界拉出一阵一阵长长的风。
师傅说,车子都是孤狼,不互相亲吻,不以撞击任何东西为目标,只与风雨交手。这些话高速撞进实一心间。实一一一记住了,从此想,要用车摩擦出风,然后迎撞逆风。他想回答其实车不孤独,他只是并不。
原来开车不是一件向前的事,从风的擦肩加入那一刻起,开车也是逆行。有时候是雨。这逆道原来一直布满溺水之险,实一觉得这危险甚好,每个人都是这么在潮湿中找路的,他也不过是普通人,没有比谁拥有更多汪洋。一旦知道陆地的水,水里的陆仿佛可以计算。
车是比心房更专一的容器,并不太管那风流,最多是与那擦肩的风击掌,就把那风雨扫去甩去,致志地往目的地开。专心,专心就好,实一念着。(待续)
(本文获第二届海鸥青年文学奖小说组首奖)









fecddf19-ef76-4434-8507-e74d7784da4b0ccbf16e-a852-4818-8eb5-5a675835b2e5.jpg)
403a8220-f10a-4dde-a467-e4451853e7c3cd1755be-02af-4d31-ac0f-1f896a000765.jpg)
7a0947f3-cf5d-46c2-b077-0e21c7b97f162fad18c7-7a5a-40a1-975f-35c041fd0ca8.jpg)
c3c689d0-e3dd-4455-84d6-18ff96c0439f183f5f88-b397-43b1-b9bc-fed917a5b493.jpg)
692940bf-f699-4886-99a0-d51294b0c5a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