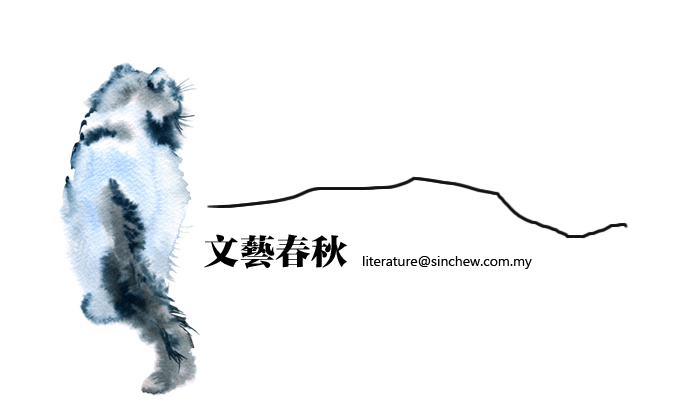
小时候不容易有糖果吃,那时糖果是奢侈。早餐涂抹了白兰他菜油的白面包,沾点白砂糖,已是甜的最大享受。
父亲过世后,住在新加坡的小姑心疼我们小小年纪就没了爹,假日里常搭巴士越堤到新山来,大包小包的带着水果、零食、小玩偶,在我们苦涩失落的童年里挂些闪亮缤纷的彩球。记得,小姑坐下来和妈妈比手划脚聊,聊家里的男人我们的未来。激动的时候,她脚上圈着的那条秀气脚链子,金闪闪的心形叶片旁有小小的金铃铛,会细细发出叮铃铃叮铃铃的碎声,似圣诞老公公雪橇上的梦幻铃铛。多希望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远远的,就能第一个冲到门口迎接小姑,抢在哥哥弟弟之前把糖果拦截下来,拽进口袋藏多一些。谁叫哥哥力气大,动不动吼人,弟弟又可爱调皮轻易得人宠;最乖最静的,总抢不赢。
舍不得,吃完了还要把五颜六色的糖衣舔一舔,再平整地压着收着。怕被妈妈发现,就偷偷压在枕头底。入了夜躺上床,鼻息下果真预期般满是香甜!窗外浑圆的黄月亮在被单上洒满了粉粉的幼白糖霜,翻个身就扬起甜滋滋的细响。小眼睛一张一翕缓缓晃进梦里,眼皮底下,梦仍不停咀嚼着快乐滋味。
第二天放学回家,不动声色回房。掀开枕头,哇啊,蚂蚁大军不知何时已四面涌来,黑压压一片让人头皮发麻!我吓得赶紧抓来毛巾胡乱擦打,蚂蚁大约也不知所措,逝者已逝,留下的不是死命钳着毛巾,就是落荒而逃。我沿着窜逃大军找到蚁巢穴,杀虫剂对着喷,瞬间哀鸿遍野。而沾满蚂蚁的糖衣再依依不舍也只能一股脑丢进垃圾桶,盖上,毁尸灭迹。疯狂忙乱了一阵,确认床上没留下任何黑点点才稍微冷静些,尔后无奈苦笑起来——没人知道的,那糖果梦会这样一直藏在枕头底,却让人从此无法安眠;总会有那么一两只露出前额锋利之大颚,无坚不摧一般反复噬咬我的酣甜。
其实糖果有如人心,也分阶级。
最平民的是粉红色的草莓糖和白色的薏米糖,滋味平易近人;登高一阶,是内里裹了巧克力的椭圆白糖或藏着细盐的橘子糖,懂得花俏变化,富有层次感;最高阶呢?唯属黑不隆冬的咳糖,深藏不露又老又辣,刺激又冰凉,只有勇敢的小孩才敢放进嘴里尝试。糖衣上拿着手帕擤鼻子的老人,是一众小罗喽爱炫耀比较的膜拜图腾,谁拥有最多,谁就是孩子王!但在我眼里,糖果里的极品以上皆非,我的最爱是——软糖!什么棒棒糖拐杖糖千层糖麦芽糖的,似白骨精一般上天下地变换模样搔首弄姿,其实都一个底,快都给我退一边去!软糖不同,它朴实柔软却颇具韧性,要说人性也行,至少不伤牙,可以抱着一包包吃,一年年吃,老了也还一定还能吃。
软糖,最没阶级之分。
后来大人说我太爱吃糖,得管管,却没说吃了糖要漱口刷牙,也没提醒夜里睡觉不能含着糖;大人看事情总是如此不用心,本末倒置。心一直认为,是妈妈嫌我笨手笨脚恼我罚我打得太狠,咬牙一再强忍,那夜里才会牙疼。有时,我也流着泪怪自己脑袋笨,就故意让牙疼来惩罚,微微电击,有一下没一下来袭的痛就让它去痛。拖到底严重了,疼得厉害,也只绻在被子里低低哭泣,不敢放声。最后当然哭肿了眼,被妈妈拎到诊所补了牙。有时牙医说蛀得厉害,得整颗拔了。他举起钳子,我脑子里立即闪现连续剧里因拔牙失血过多而死去的爸爸那张铁青的脸。我没喊没逃,已习惯打死也不能逃,能躺在床上失血而去也是不错的宿命。幸好,这样的惧怕与自我安慰次数不多,经常补一补就可以平安回家。可补好了,银黑银黑的一个个小牙洞让人哭笑都不敢张口;渐渐长歪长斜了的一排黄牙暗暗豢养了自卑。妈妈不懂,还说我很能忍痛,最安静最乖。被称赞真是好,该珍惜,于是忍痛慢慢也成了我的拿手绝活儿。后来,学校教小学生如何正确刷牙。下课用餐后,大家拿着漱口杯盛水,整齐地排在沟渠旁蹲下;兴奋把一个个嘴巴都刷成了冒白泡的甜甜圈,甚是壮观!班上最凶的宋老师见我的甜甜圈没冒泡,蹲下来握着我的手示范正确的刷牙方法。我是害怕的,怕老师的权威,可那只大手像妈妈偶尔难得的温柔怀抱,暖暖的,是小小的我唯一的仰望与引导。牙刷刷毛一根根活了起来,以四十五度角贴近我的两排牙来回唰唰唰。第一次明白——原来刷牙需要这样温厚的内力!之前都一直给牙齿瘙痒痒吧,怪不得蛀牙总来找!
不是糖果的错,总这么想;偏爱糖果,就不能把错推到它身上。那错要推给谁?穿好一枚针,把自己的嘴缝上。
长大后糖果多得到处都是,餐厅里付钱的柜台理发院或红白事现场,随意拿了便吃;甜的快乐却犹如炎阳底下晶莹水珠之蒸腾,匆匆看一眼皆来不及。觉察到如此变化,我开始小心翼翼,尽量不让大量的贪婪与需索无度破坏了心底最珍惜的有限甜蜜。这时,养身也酝酿成了时尚与必须,癌症嗜甜的说法更亦步亦趋天天增值,只能在生活里开始斤斤计较,这里添一点那里减一分,以防哪天如厕后蚂蚁来袭,老来便要失明锯腿坐轮椅,把下半生过得淡而无味没人搭理。不是怕死,只是不想这样死。即使想到了这份上了,仍旧不会是糖果的错。我手上那枚穿好线的针,这回把耳朵、眼睛都给缝上了。
枕头底一直留着的糖果梦,真是可惜了,那是沾了许多哗啦啦哗啦啦乱窜的,有黑点点的梦;幸好,我一直认得它的黑。其实,就只是想好好吃颗糖,回到当初最纯净最轻柔的渴望,如此而已。
最好最好是软糖,没牙了一样可以吃,一辈子。









fecddf19-ef76-4434-8507-e74d7784da4b0ccbf16e-a852-4818-8eb5-5a675835b2e5.jpg)
403a8220-f10a-4dde-a467-e4451853e7c3cd1755be-02af-4d31-ac0f-1f896a000765.jpg)
7a0947f3-cf5d-46c2-b077-0e21c7b97f162fad18c7-7a5a-40a1-975f-35c041fd0ca8.jpg)
c3c689d0-e3dd-4455-84d6-18ff96c0439f183f5f88-b397-43b1-b9bc-fed917a5b493.jpg)
692940bf-f699-4886-99a0-d51294b0c5a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