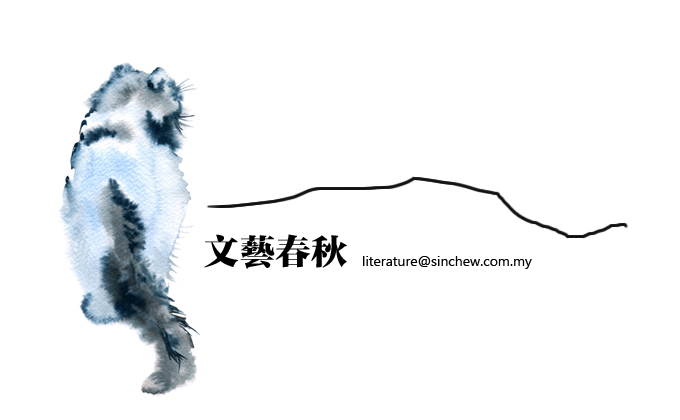
阿勇很会游泳,而我不会游泳。
说起游泳,总想起我的朋友阿勇。十七岁那年,学期快结束,而长假却还没开始,那段模棱两可而闷热黏腻的时光,日光刺眼的下午,阿勇怂恿我一起跷课。他说:“走啦,我们去游泳。”我们从学校的后门离开,招手就搭上蓝白色相间的海边四号巴士。我们坐在最尾的那排座位,阿勇把校服从裤头抽出来,手肘抵着车窗,任由从窗口灌进的风把头发吹乱。
随风翻飞的白色短袖子上,别着一小枚黑色的方布块,显得特别显眼。阿勇还在服丧。他的父亲在一场车祸里去世,从奠仪到送葬,阿勇整整一个礼拜都没来上课,错过了所有科目的期末考。在往半山行驶的巴士上,阿勇一路没有说话,到站时他才用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促狭地向我眨眼睛,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在他身上一样。
波光粼粼的露天泳池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阿勇用标准自由式的姿势,在蓝色的水池中往返地游着,来来回回,已经数算不出他到底游了几圈。阿勇的手轮番不断穿进水中,双脚踏出无尽细碎的浪花。而我却连泳裤都没带,水中只穿三角内裤,像一块浮木一样漂在水中,领受着阿勇掀起而不断回荡到我这里的波浪。
是薛西弗斯啊。那个永远都在不断地推动石头的薛西弗斯。他把巨石推上了山,石头却总是从山顶滚落,周而复始的无限回圈,重复着耗力而徒劳的命运。
我上大学之后,才读到卡缪的《薛西弗斯的神话》,那时已和阿勇失联很久。农历新年的高中同学会,也从来不见阿勇。这也难怪,那一年长假结束,阿勇还是留级了,和我们不再同班。我只记得一些阳光充沛的光景,包括那日阿勇在泳池里不知来回游了多久,而终于停下的时候,我们靠在池畔休息,有一个打扫的马来人走过我们面前,阿勇抺掉额间水滴,看着那人的背影,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认真地悲伤?”
也许卡缪会说,因为一切都是荒谬。一如他在《异乡人》一开始就写莫梭几乎没有理由就开鎗枪杀人的情节。要知道,人生就是荒谬的。你再看一看,这些死亡、悲剧和哀伤。一如至此仍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小说家的卡缪,他在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不久,就在一场车祸中骤然死去。而原本他是打算和家人一起搭火车的,他的大衣口袋里还留着一张未剪过的火车票。
我后来才知道,或许阿勇那时候在泳池里想问我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终究可以选择一个怎么样的方式,来度过此一生?
我往后总会在不同的时间里,想起卡缪,以及十七岁的阿勇。在SARS肆虐的瘟疫时光;在和警队对峙,催泪弹烟雾弥漫,抗议的人潮聚集又仓皇逃离的吉隆坡街道上。或者,在一个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城市里,开始猜测关于一个词的各种岐义。异乡人。STRANGER。外来者。陌生人……。我许多年以后才开始可以体会,为什么没有人认真地悲伤,以及阿勇在十七岁那年,比我提早遭遇死亡时的那种陌生、疏离和无感。
一如多年以前一个跷课的下午,我看着我的朋友阿勇在无人的泳池里一直不断来回地游泳,像是寂寞的薛西弗斯。我记得,一直到日光渐渐昏暗,我撑起身体,爬上了岸,向远处的阿勇挥手,叫他回来。
阿勇回过了头,喊我的名字,他大声说:“再让我多游一会儿吧!”









fecddf19-ef76-4434-8507-e74d7784da4b0ccbf16e-a852-4818-8eb5-5a675835b2e5.jpg)
403a8220-f10a-4dde-a467-e4451853e7c3cd1755be-02af-4d31-ac0f-1f896a000765.jpg)
7a0947f3-cf5d-46c2-b077-0e21c7b97f162fad18c7-7a5a-40a1-975f-35c041fd0ca8.jpg)
c3c689d0-e3dd-4455-84d6-18ff96c0439f183f5f88-b397-43b1-b9bc-fed917a5b493.jpg)
692940bf-f699-4886-99a0-d51294b0c5a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