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花踪颁奖礼上,评审在台上宣布报告文学奖首奖从缺之后,评审之一的谢裕民笑着对另外两位评审说:“我们要向主办单位要求,从缺的首奖奖金应该分给我们3位评审啊!”
看大家附和,谢裕民忍不住再说:“真的啊,我们评得多辛苦!”
ADVERTISEMENT
新加坡作家谢裕民曾被评为“新加坡华语语系的10个关键词之一”,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建国》更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18年年度小说。
谢裕民说话直接,没架子,说草根的话,毫不忸怩造作。用他的话来说,自己的“心里还有个乡下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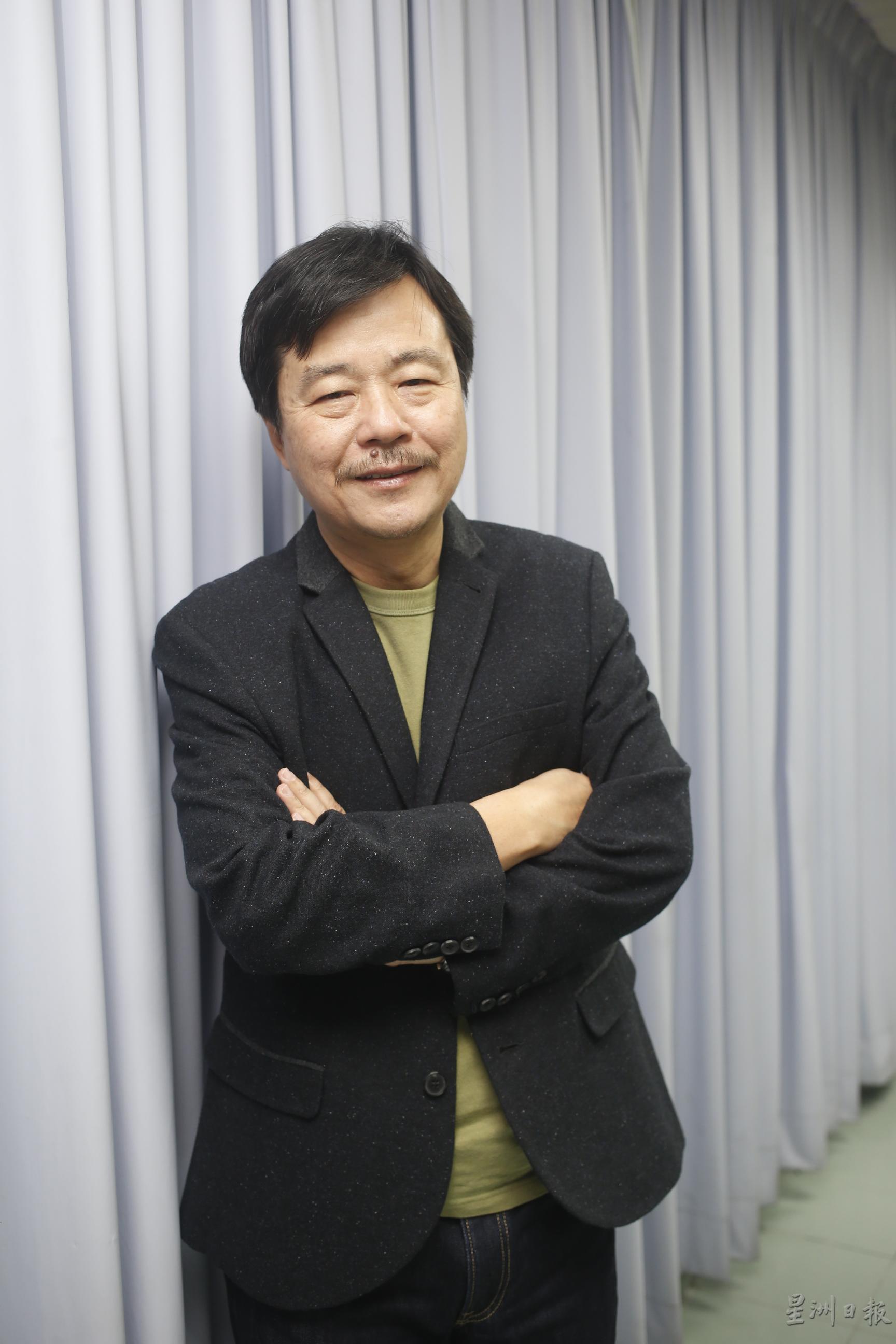
生于1959年的新加坡,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并非钢骨水泥的花园城市,而是刚刚向英殖民政府取得完全自治的“小红点”。
忆起童年,谢裕民只想到贫苦:“我是从苦中来的,出生的地点是加冷巴鲁(Kallang Bahru),以前那是片沼泽区。”
加冷巴鲁位于新加坡中部,曾是盆地区。谢裕民形容,自己的报生纸上注明的出生地便是加冷沼泽地上的一片小岛。“以前很多小岛,涨潮时,我的朋友都需要坐船才可以从学校回家。”
直到后来填土、盖楼,加冷巴鲁成了建满公寓与公共组屋,以及现代体育场的规划区。
谢裕民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性风格。例如在小说《M40》中,谢裕民笔下面对中年危机的主人公凭着昔日记忆,寻找早已被拆除的老屋。老屋原址已被现代化建筑取代,主人公在附近徘徊,寻找着记忆中的那棵老树与那条下水道。
他的小说不只是书写“一个散逸的家”的状态——“父母一走,家就散了,老屋也没了”,更纪录了一个时代的情怀已然远去。
一个还有点理想的时代已远去
17岁那年,谢裕民以笔名“依泛伦”投稿到《新明日报》【新风】版,没料到稿件会被录用,更被当时的编辑、新加坡小说家姚紫要求见面。

谈起80年代的写作氛围,谢裕民形容当时是个“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写作的年代”。“以前我们写稿,很谦虚,很怕别人知道,都用笔名。后来的人都用真名写作,而且要昭告天下。”
“当然怕啦,作品不成熟,没有信心。”对于谢裕民而言,80年代的写作氛围是作家各自努力、默默耕耘。
谢裕民认为,这或许又与自己是个乡下孩子有关:“从小总被大人告诫要谦虚、藏拙,你就变得更没有信心咯。而且你看别人的作品真的是比自己好,那别人称赞你的作品时,说‘过奖、过奖’,是真的过奖了。”

从一个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有进行创作的年代,进入一个要昭告天下自己在创作的年代,谢裕民也反思自己受到过去“集体主义”的社会氛围所影响,不敢宣扬自我。
然而,80年代初期对于二十来岁的谢裕民而言,是个“还有点理想”的年代。“还是有理想,不然也不会写稿。但大家都不谈(理想)。”
“因为谈理想就显得你非常笨,你懂吗?”80年代中期,新加坡整个社会都进入了拼经济的年代。谢裕民形容,当时的报章财经版从一版,变得多版面,财务管理也成了热门学科。
在新加坡整体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普遍变好之后,谈理想似乎成了太沉重的事。“大家不再谈理想,人生目标换成改善生活。新加坡华校生也从谈论主义和理想,改成谈论生活。”
“整个社会气氛就是,没有人再谈理想了,大家都转变了。当时大家都想着过更好的生活嘛。”

与岛国一同长大
《建国》中到处可以找到谢裕民的身影——主人公建国也生于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的年份;6年后,李光耀在电视屏幕前洒泪,马新分家,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当时主人公6岁。
从新加坡的两次独立,进入李光耀时代,直到李光耀逝世之后,今年60岁的谢裕民经历了整段新加坡现代史的历程,仿佛是个陪伴岛国成长的一代人。
谢裕民坦承,自己那一代人受到权威教育影响,难以跳出国家所定下的框框。“其实我们就是(受到)李光耀时代教育的一代人,……我们即使能够跳脱那一套思维方式,也跳脱不远。”
“我们很多东西是跨不过去的。”他无奈表示,即使被年轻一代批评为保守,但也无法改变,更赶不上年轻人。“我们的养成是这样,整个都是这样的。即使我们做再多,也比不上年轻人轻轻一步,就跨过去了。”
虽自觉地待在舒适圈里,没有直接批评国家论述,但在《建国》中,主人公却以一种调侃的语气,尝试追问国家历史是怎么被建构的:
“建国不明白,今年——2015年,为什么国家会庆祝‘建国50周年’。……自己与国家同龄,怎么自己56岁了,国家才50岁?”
除了写小说,谢裕民也在报章副刊担任编辑。身为编辑的他,写作也受到新闻室的影响,《建国》像是一本半新闻的小说,里面记载了许多新加坡小人物的故事。
谢裕民表示,自己本身做新闻,对于这些在报章上出现的小人物故事特别感兴趣。“这些故事满有人情味,令人感动。我看到这些故事就想,现实中有这么touching的故事,我何必再去虚构呢?”
2018年,新加坡庆祝独立50周年,谢裕民收集了一年的《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纪录,将有趣的故事收录在《建国》中,成为SG50新闻剪报辞典。
国家给的套餐
《建国》中,主人公建国在25岁那年参与国家庆典,在典礼上和群众举牌、看烟火,忍不住心情澎湃。谢裕民说:“那种特殊的氛围之下,会忍不住产生爱国的感觉……所以我才写说,他都看不起自己,干嘛自己会有这种情绪反应?”
身为小说家,谢裕民在书写国家历史进程时,也面对强烈的挣扎与矛盾。一方面,认识国家体制的缺陷,另一方面,却又需警惕陷入“爱国情绪”当中。
谢裕民回忆,在书写关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谈话时,他思考许久,该如何下笔?该为当政者说好话吗?是否令人感觉讨好政府?
“那一段我想了很久要不要写,会不会让人感觉我亲政府……有时候我认可他(执政者)说的话,那我该不该写?”
书中又有一段描述李光耀的葬礼上,墓碑上放着一朵致敬的鲜花。谢裕民说自己见到这一幕,内心忍不住激动:“你会想到,这个人用一辈子,换取小孩在路旁为他欢呼。”
“这种时候你会忘记很多他个人的问题,或者是体制的问题。真的。”
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他只好接受——“人是会有这样子的反应的(对国家心情澎湃)。”但他也自我警惕,这种爱国情绪正是产生集权国家的来源。
谢裕民在小说《放逐与追逐》里面提出一个类比,说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形容:“每个社会都是一个配套,好像去餐厅吃自助午餐,你不可以随便换菜,那可是要加钱的哦。”
他说:“你可以要求各种菜色,但你哪来那么多钱?而且,眼前这家餐厅算是价格相对合理的。”
谢裕民无奈地表示,一个人若不满自己的餐厅(所身处的社会),就只能将就地吃,或是必须拥有财富,才能要求更换餐厅。
“年轻人或许还可以找别的餐厅,但我只能选择眼前这间。这道菜不好吃,我就放点酱料。”
“就必须这样子啊,”他摊摊手,平淡地说:“大环境改不了,但你可以创造你的小环境。”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