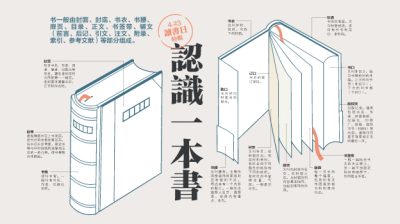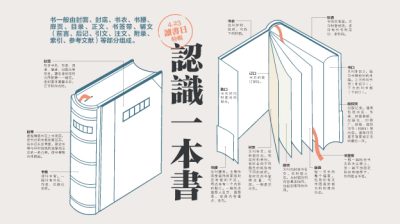要用寥寥数语归纳许裕全的作品特色并不容易。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阅读手记、脸书小品……他几乎什么文类都能写,并且能写好,甚至手写字都很不俗,然而彼此间的样貌又各有不同。例如散文情深、小说热闹、新诗幽谧、报告文学义正词严,不不,这样数来还说少了他的诙谐与风趣,远远不够描绘他的多变。他还非常会唱歌。他似乎就是一个全身长满手,且都拿着精致工具的写作人。啊这不是千手菩萨的形象吗?可你若真这样想,恐怕他又要回你一句“菩萨最难写”了。
ADVERTISEMENT

家乡倚山傍海,近玄天上帝庙旧街场有两间老咖啡店,一间叫“东岛”,另一间冠名“东洲”。
两间传统咖啡店不约而同取了个山头大名,一念便觉气势恢宏磅礴。无奈局促在鱼虾蟹的弹丸之地,“东洲”或“东岛”都和地形字义无关,它们厕身路口各自招徕,说到底,仅是带着潮水情感的乡愿而已。
渔乡慢,时间作息以潮水度量。
一天总有那么几段魔术时光,一洲一岛尽是海脚人,仿佛潮退后被冲刷在岸上行走的人鱼,吞烟吐雾,吆喝喧嚷,缥缈不似人间。
那时,我常“东岛/东洲”傻傻分不清楚,它们的名字身世距离如此相似相近,倒是后来发现一间毗连“东洲”咖啡店的麻将馆,才将它们从我的地理版图里各自独立起来。
从此“东洲”在我心里成了“麻将馆隔壁那间咖啡店”的隐喻。
会记住那间麻将馆,说来惭愧,因为爷爷就暴毙在那里。
人生无常,死法千百款,天可怜见,让好赌的爷爷命终麻将台也算功德圆满。当他被好心人载回家时,还眷恋依依的在人家车里撒了一泡尿。这就让人难堪,一群小毛孩诧异围观,无有禁忌悲伤,倒是我记得车主满身大汗从后座抽出脚垫出来甩,发现经已湿濡一片,都甩不出水了,苍白的脸嘴里仍喃喃念着:没关系,没关系,水为财,水为财。
不晓得最后倒楣的车主有没有收下家属歉意的红包?细节不复记忆。
倒是爷爷走后,父亲接钵,成了麻将馆里的赌二代。
午后焰阳仍有余威,滞闷的空气让人萎靡不振。
我常会骑脚踏车去“东洲”打包,那里有我爱喝的茶冰,兼及糕粿点心,来驯服我精神的鸦片瘾。然而,每次到了那里,总会在胡乱停靠的车堆中,一眼认出父亲红色野马哈的老摩哆车。
它仿佛一个鲜明的标志,提醒我:车在人在,令伯就在烟雾缭绕的麻将馆里砌墙造屋!
我船头怕人船尾惧鬼,行色匆匆、惶惑不安打包了就走,不作片刻逗留。
那时性格孤寡,自诩识几个字就骄纵傲慢,觉得麻将馆是个藏污纳秽的地方。父亲镇日留连那种所在,想必也是个不堪的男人。
为此感到羞耻,也常被这样的羞耻感提醒。
同学的父亲不只一次对我说:“你老爸博麻雀真臭款,屁股长坐了不要起来,完全不给其他人‘颤死’(机会)。”
啊!换个简洁文雅的说法是:赌品不好。
后来同学的父亲再补上一句:“赌技很差,一直输钱。”更让我挫折,深受打击,还差点和他绝交。
父亲生来从不怀疑自己的手气,一坐数小时,一赌经年,也不体谅身旁身后那些伸长脖子枯站着的、巴望着轮替的人。一日将尽,我常从他随手带回家的东西判断是日输赢,小至燕菜果冻,大至热腾腾慢煎糕,只要我把这些当成歉意和补偿,心里阴影的面积就会小一些。
在那里,打麻将叫“博麻雀”:动词、从鸟。几双手游走推搓,一桌麻雀飞来扑去啁啁啾啾。
那时,如果父亲不在家,便在麻将馆;若不在麻将馆,便是在前往麻将馆的路上。这推测不难,永远不会出错,毕竟家乡那么小,一条街两排屋小径深处有人家,三人行必有近邻,谁都是谁的谁和谁。
曾有一回,我像往常一样在“东洲”前看到那台老摩哆车,狐群狗党似的挤在车堆里。心想立马打包就走,却意外的和坐在咖啡店里的父亲四目交投。
像被雷电劈着似的,他一定看到我突然僵硬的表情。我手上的韭菜粿差点掉下来,慌张付钱溜走,一路风风火火踩回家,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在熟悉的摩哆车噗噗声传到家门口后崩塌了。
一进门,父亲就以极愤怒、厌恶的表情叱责:“在外面看到自己的老爸也不叫一声?不肖子!”
明明努力闪躲的、那么一个从秽浊的麻将馆走出来的——一脸不晓得混杂颓丧或是亢奋表情——男人,突然打开错误的任意门出现眼前,要我如何瞬间切换一个虚与委蛇的表情?
该厌恶的人是我吧?
后来,生命中也只有那么一次,我踏进了麻将馆。
也是赤燄燄的午后,家里突然来了一个说要汰换旧电箱的技工,彷徨失措的母亲叫我把父亲找回来。
从大马路顺着斜坡滑下去,过了叔公的“新腾兴”杂货店,远远便看见父亲的老摩哆车停在那里,直觉告诉我:车在人在。
走近麻将馆,发现入口两扇木门开启,再以一直立的三夹板挡在前方。于是,路人即便从外头经过,只闻麻雀沙沙啁啾,却窥不见葫里乾坤,必须从两旁绕过那片虚设的三夹板,拐进去才算走入麻将馆的大厅。那片阳春三夹板,怎么看都像廉价的遮羞布。
大厅烟雾弥漫,几盏日光灯从没有天花板的樑柱垂挂下来,四周灰蒙蒙的像暗潮把海床上的泥沙不停翻搅上来,整间麻将馆俨然一缸经年未清洗的巨大水族箱。闲散的男人像深海鱼围绕游走,烟雾如水荡漾,个个表情模糊莫辨。
兴许观赌也是乐趣,以上帝全知的视角周游各家底牌,不时咬耳窸窸窣窣,怕声音太大,还用手做做样子遮住嘴巴。这才了然同学父亲说的:要给其他人“颤死”(机会)。
原来,有位子坐着摸几圈是极大的荣幸啊!
我逡巡一番,在人潮中把父亲认出来,他就坐在中间那桌。想必那天手气不顺,桌上只剩小额筹码,站在他背后的男人窃窃私语,尽是婉惜和亟欲指导些什么的眼神。
我怯生生趋前喊了一声:爸!
他没听见。用我从未见过的专注,蹙眉深思。
爸!我再喊了一声,声量提高。这会儿,像突如其来的裁判吹了暂停的哨子,桌上的男人全都转头看着我。从他们当下惊愕的反应,有千分之一秒的瞬间错以为我就是他们的儿子,而叼在父亲嘴里那根烟,却掉了下来。
那也是我最怕看见的,赌桌上神色漠然的父亲,陌生得像路人甲乙。我们不应该在这种地方相遇,我本不应该推开那扇门,看到他一生终将在那里消融腐烂……想到这,突然觉得自己委屈了。
父亲很早便退休,那时我刚毕业不久,打了份薪水微薄的工作,每月摊还学贷缴保费,七除八扣,所剩无几。他对我说:“以后轮到你养我。”
心没感觉被重重挥一拳是假的。
父亲终于告别海洋,像一尾鱼登岸而去,搁浅在烟雾绕缭的麻将馆,一片风浪不惊的水域。他比以前自在快乐,一厢情愿以为可以在家乡继续平凡慵碌,把人生虚掷耽溺直到老去。然,一场疾病却把他的命运和我拴在一起。
离开麻将馆或许比离开海洋更让他不舍。
父亲被我从北部家乡漏夜载回南部的翌年,麻将馆也被改装成燕屋,镇日啁鸣啾啾,召魂似的呼唤那些不知去向的男人们。父亲过世后我偶有回家乡,每每走到“东洲”咖啡店,听着扩音喇叭轮回的燕啼,悲伤莫名。人生仿佛烟火一场,最后都将烟消云散。如果能再遇到他,这次我会牵他的手回家。
坐浪一辈子,若要为父亲的生命做个小总结,只能被归类为:一个辜负海洋的男人。
小舅在家乡算是个有气魄担当的男人,父亲曾随他的船当副手。“副手”名堂好听,我为此欣慰,觉得至少父亲为自己的人生扳回一局。
两年前和小舅谈起此事,他止不住促狭的笑,说:“因为你爸爸懒惰呀!就安排他开船。”
“他在船上有个外号,叫‘大师’,出一张嘴,只念不做。”
小舅这样说他姐夫,我这样笑我爸爸。我们笑着笑着,突然都流下了眼泪。
许裕全 简介
1972年成形的宇宙小星球。
闷骚乏味、沉默厚道、多愁善感且温情的摩羯座男人,常躲在生命低层深处仰望星空,以感官认知世界,喜欢人与人之间零点零几的距离。
从渔村出生,山林原野奔跑长大,生命偏旁携山带水,总为发光发亮的生命体着迷,选择用文字在地平线慢步经心,遇到的人物风景都是幸运,都是恩赐。
曾获国内外文学奖,出版作品有:《山神水魅》、《女儿鱼》、《菩萨难写》、《47克的罪愆》等。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