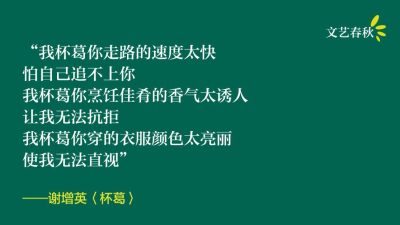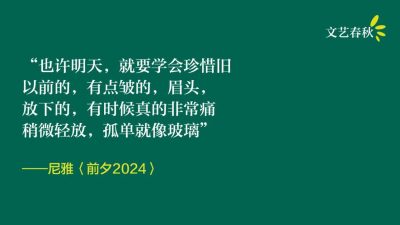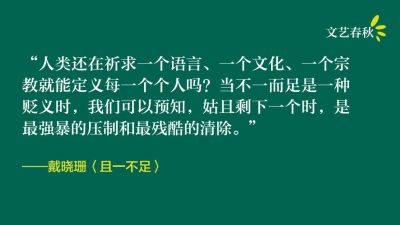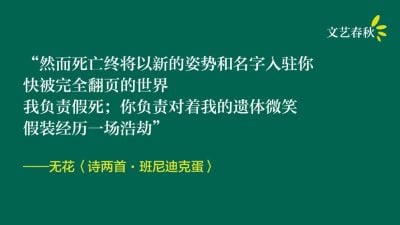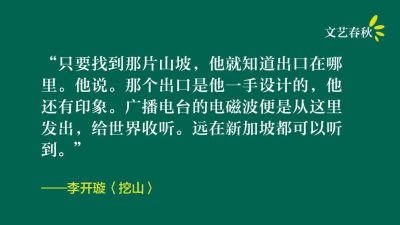ADVERTISEMENT
0.
淫淫肉身,都在繁华灯火的尘光中衰老了。你感到前夜的你已在璀璨的烟火中熄灭,你的青春你的爱情,还有你狂狂的欲望,在一朵朵五颜六色爆开的幻影里如花事开到了荼靡,时光浮漾,散成一圈圈的涟漪,把你围在中间,囚你淹你,让你最后无声无息的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时光的河床之底。
陈望生,电话!廉价旅馆柜台处的师奶敲着门板,丢下一句话后掉头坐回原位。窄仄的柜台后藏匿着她那略微臃肿的影子,蓬松的头发遮掉了半张脸,侧对着电视,新闻正播报着昨夜香港移交的仪式典礼。中午刚过,你对着电话喊喂,喂喂,没有回音。系边个?转过头来你问正专注看着电视的师奶。唔知喔,听把声系女子来D。你把电话盖下,感觉有点头疼,睡眠不足,精神乏乏,你一步一步把自己送进深暗的房间里,关上门,不管谁来敲门你都不打算再打开了。
记忆阙如,空白地带上孤立的身体静静守着时光的离去。是离去还是离弃?你试着想找到一个比较贴切的词汇,像孤单情书里不断写信给自己的痴者,说着梦话,不管快乐或悲伤,都想努力的瞒着自己,让自己在自己设下的欲望迷宫里迷失。是的,像爱总是迷失在爱里。或许,在许多年后,你会隔着某段时空,收到自己寄出去的那些情书,一个字一个字的躺在封死的信封里,等待着被开启,让一批批沉睡的文字重新被时间唤醒,然后赤着身体猛力地敲打着记忆的窄门。
2754388,东方日报副刊记者,黄牧涵。ChatrineWong。名片上的名字与电话号码静静的在光影中漫漶,模糊、虚幻不实。而昨晚的微雨停了吗?你躺回床上,凝视着天花板,想着在这十二层楼的上方,还会住着哪一些旅客呢?台湾的,牧涵说这间廉价旅馆多是台湾光观客入住,便宜,又在旺角中心,下楼转个弯就是地铁入口站了。方便,所以常客满。难怪坐在柜台的师奶偶尔会用不咸不淡的普通话对着一些住客招呼着:“肥来了啊,今天又去哪里逛啊?”肥和回,你有时候也分不清这腔调混杂中的音阶,港腔得很正道。窗外筛进的光线细细游移,路过有声,把时间踏得窸窸窣窣,幽渺的像说不尽的余情,却不断扰乱人心,让心烦的,慌得不知所措。
你把自己蜷缩成了一只幼蚕,躲在时间深厚的茧内,而深感安全。茧外是别人的情感世界,你把思绪放平,躺下、不让它流动,或流淌向外面的世界去。牧涵说,每次遇到情感的死结时,你总是把自己困死在自我的囚牢中,关闭所有的感官,懦弱成了等待被人拥抱的婴孩。你听后只是笑笑,却不多加辩解,仿佛所有的言词都只为了成就一个故事,而说着故事的人却是他者,与你无关。然而实际上,你总分不清楚,是因为有了你和她,才生出了你与香港的故事,或因为有着这样的爱情故事,才有了你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是以这之间关系的交际和纠缠,让悬在十二楼半空的你,常常迷惑于命运的戏谑与嘲弄,尤其自爱情的殇失之后,你只觉得处于这陌异的天地之间,就剩下自己孤伶伶的一个人了。
前晚你与牧涵撑伞躲进了一望无际的人潮里,成了一片人群中的两个小点,抬头等待七一回归夜晚在维多利亚港口燃放的烟花;那时微雨弥漫,在灯光照耀下翻溅出一片凄迷,并让夏季夜色漓漓地湿进到深深的人心里去了。而你们挤不到前面去,在一大片人群与人群之外,伫立于金钟添马公园的边缘处,混身在街灯的光影晃晃之中,落寞地感觉到了浮岛上末世提早来临的冷肃气氛。一百五十二年英殖民故事,租借的历史,终将要在烟花迸发的华丽火硝中归于暗寂,寂暗之中,历史翻到了另一页,又将会书写出怎样的另一个故事来呢?
你想起了牧涵在九五年毕业前,写了一篇散文叫〈不翘家和不翘国的人〉。那时在台湾南部一间著名的国立大学,蝉鸣如潮,嘶喊出了凤凰花六月血红鲜艳的花瓣,一簇簇的,烧亮了整个南部的天空。牧涵说毕业后她就要回去香港,不会留在台湾,虽然她本身具有中华民国护照和身分证,也知道香港再过两年就回归了,但香港那边终究有她的家,所以即使回归,她也不打算当一个翘家和翘国的人。那时不少香港的学长姐都是毕业后选择留下来,毕竟回去后,很快就会面对到香港回归的茫茫前程,再说,他们也习惯了台湾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氛围,因此在台湾找工作,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但对牧涵而言,回去是一种必然,而不是一种选择,因为翘家和翘国,都是不被自己认同和道义情感所允许的。然而那时你们的感情却刚开始,原以为这么快就要被分割两地给掐断了,像一团刚点起来的火,还没燃放到最炽烈时,却硬生生要被熄灭了一样。而那时你还是大二生呢,没去过香港,却在港剧里熟悉了香港的一些景观,如警匪片里的旺角和油麻地;商战剧里的中环和铜锣湾;青春偶像剧里的尖沙咀、太平山顶和浅水湾等等,而且也在港剧里学会了一口蹩脚的粤语。你的香港想像仅此于那些声光之内的画面,香港人的生活与香港人的故事,都在港剧和电影里不断重复,并且全贴进到你对香港的认知里去,但牧涵说,那是与现实香港有很大差距的。
在毕业典礼结束,你与牧涵进行了两个星期的环岛之游后,牧涵就飞回去了香港,只留下你在那岛屿南方的校园内像孤魂野鬼似地寻找满地亮丽的阳光,可却常常照见脚下孤影中被时间搁浅的寂寞,细细画出了无尽的思念。而一星期三次的国际电话,在无数张一百元台币电话卡的吞吐中,累积了许多说不尽的絮语,因此在短短三个月,你就已经收藏了用过的两百多张画面精美的电话卡片,静静地堆垒在阴暗的抽屉角落。而两地的感情,也在电话卡不断累积中,堆叠成了小小山丘一般地,逐渐稳固了下来。
你甩了甩头,似乎想把过去的记忆甩到身后去。微雨仍然在夜中无声翻飞,在灯光下闪烁着丝丝银亮。牧涵就在你的身边,你可以嗅到她身上惯用的卡地亚香水气味,薄荷清新爽朗地骚动着你的嗅觉神经,可是站在旁边的她,感觉却是那么的遥远,像那些挽不回来而只能回望的日子,隔着重重烟山和云雾,想抓也抓不回来了。雨伞下的人,都在期待即将来临的时刻,烟花爆出满天空的炫灿,五颜六色,七彩斑斓的,如金菊怒放,如牡丹盛开,如虹彩飞舞,粉红、艳红、碧绿、淡紫、金黄、橘黄,不断在夜空闪爆,然后宛若昙花般在漆黑的眼眸中凋落,足足三十分钟,仿佛所有那一刹那的辉煌,都只为了见证没落,所有的美好也是为了迎来一片黯淡的孤寂。仿佛七一夜里的雨丝和烟花,都只是为了注释一座浮城的回归,以及你们在这座岛上爱情的终结。
你缩入了小小房间中的窄小世界里头,没有窗口,探望不到外面的世界,这里就宛如一座迫仄的洞穴,你是一只自我疗伤的兽,不断用回忆舔濡着情感的伤口,让它慢慢及至结痂为止。时间如流水淌过,也不知将会把你漩入到哪一个深渊里去,你就只是一心一意钻入更深更深的内我世界中,那里无光,却能让你沉浸在黑暗中而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并由此感到一种超级稳定的安全感。
九七、七一、夜晚、微雨、烟花、爱情和香港英殖民地故事,全都已荡荡漾漾地在光河里流走了。英国人离开后,再过几天,你想,你也应该会离开这座岛屿吧。
1.
二十二年后,你从吉隆坡飞到了香港,为了出席一场现代诗学术研讨会,在七月一日的晨早,飞机降落在赤鱲角国际机场,却让你想起九七前每年你到香港总要落在九龙湾的机场上,每次飞机以九十度弯角下降时,几乎是贴着高楼而落,你常可从机舱窗上看到外面楼窗内一些住户简陋的住家景观,但现在则是大岛空阔,无障无碍地,轻轻巧巧就降抵于机坪之上了。
妻在送你到国际机场时,就嘱咐你要小心,没事不要到香港民众游行闹场的地方去,免得遭受池鱼之殃。你诺诺以答,却想到这么久没再到香港,不知香港会变成怎么样的情景了。想说在上世纪九五年到九七年那两年多期间,每到寒暑假你都会到香港去住一两个星期,小小的香港岛和九龙新界等地,都已经走透透了,甚至连周围的离岛,也留下了不少你与牧涵的足迹,那些走过的路和故事都还留在你的记忆里,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与时间的冲刷而消失。
从机场出来,你转到了巴士站选搭A21号城巴机场快线到旺角,尽管许多年没到香港,但你的粤语依然流利至无需思索就可随口而出,盈耳的广东话也让你听起来有一分旧识的亲切感,这让你想起以前第一次到香港的情景,从九龙启德机场出来,搭上计程车,刚好听到电台正播放许冠杰唱的〈半斤八两〉:“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籴直头系坏肠胃/揾嗰些少到月底点够洗……”突然整个心情全都沉浸到了八○年代的香港世界里去,你少年时从港剧中耳濡目染的画面,轻轻碰触到了你多感的内心,而涌起了一分怀旧的情怀;那时你静静坐在一路奔驰的计程车里,贪婪地捕捉着车窗外不断向车后翻逝而去的城景,终于让你感到与港剧里的这一片土地,有了亲临而真实的接触。
此刻,翻逝而去的,也包括那一片蔚蓝的海与十多艘静止在海湾上的船只,而贴着巴士明净的车窗,你看到九点多的阳光明亮地敞现出一座又一座的城楼,穿过了青屿干线和碧海蓝天,连青马大桥也很快被抛在后头了。你盯着窗外从聚鱼道到浪澄湾不断流逝的风景,耳背后却一直传来吵杂的四川话,你稍微扭过头去,看到车厢后散落着几个四川游客,兴奋地高声谈笑,宛若在自家庭院一般,无视于其他搭客的存在。你原想提醒他们,巴士内厢属于公共空间,讲话请小声一点,但念头一转,却想自己何必去当公民老师呢?于是也就装聋随他们呱噪去了。
其实你知道这些年来,大陆人移民到香港越来越多,游客更是随着自由行的开放蜂拥而至,许多以前认为不会变的事物其实早就已悄悄在变化之中了,最明显的是,回归前,香港人许多都不屑于说普通话,所以当年你初到香港,对着茶餐厅的服务生以普通话点餐时,常会先被喂以一顿白眼,或当着阿灿看待,并引来了“唔识听,讲广东话啦唔该”的回应,那以粤语唯我独尊的态度,让你恨得牙痒痒而又无可奈何。当时牧涵就曾说,香港庶民的自我认同就在于广东话上,不然只要你的舌头转入英语频道,他们就会凛然以对,或换上另一副敬重的嘴脸了。所以那时你在香港,不是常常用蹩脚的广东话暴露了非在地人的身分外,就是以尾音黏滞的美语装成英语,打混成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普通语却严实地被你匿藏在舌头底下,静静地不敢声张。
而七月,香港清晨的天气真好,蓝天晴日,云白山青,高楼之外的高楼,霎而淡远;时空悠悠,光阴惚惚,在明亮的阳光里蒸若烟散。而二十二年了,你爬梳过的记忆都很虚幻,一些在脑海中晃过的画面,凌乱破碎地找不到可以连接的关键,却又不断在你的意识间浮沉,且随着巴士滑进了逐渐熟悉的西九龙,向旺角的方向驶去。
离研讨会的日期早两天抵达香港,这是你特意的安排,目的是想来观察香港反送中的街头游行,但实际上你似乎可以摸索到潜意识里的另一个你,无限渴望回到旧地寻找那二十二年前,迷失在旺角街头,忘记带走的一册爱情故事。所以在研讨会主办当局安排入住X大学学人宿舍之前,你订了两天住进那二十二年前常住于旺角弥敦道上十二楼的廉价旅馆。旺角是你最熟悉的地方,旅店就在雅兰中心的对面,银行中心的旁侧,转了个弯,后面是西洋菜街和通菜街,那是你以前常常等牧涵下班溜跶的街巷,许多二楼书店都集中在那里,有时你就把那些等待的时间耗在里头,天荒地寂的,用书里的文字修练你那稍微躁动的灵魂。所以你曾跟牧涵说,即使闭着眼睛,你都可以认出旺角的每一个角落来。
因此当巴士转进了亚皆老街驶向惠丰中心商场时,你所有潜伏的记忆都浮现了上来。街边的高楼、商店和景象,经过二十二年的洗刷,并没有太大变化。是以你知道巴士左转进入弥敦道,就会停在不远处的雅兰中心前面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往昔的自己,以及与牧涵走过的街景,陌生而熟悉地叫醒你那压在意识底层的旧忆。你从朦胧的记忆里窥探,隔着一大段时间距离,那个洋溢着春华正茂与朝气的年轻人,是否依然迷失在那旺角的大街小巷中呢?而坐在巴士上的此刻,你却已临近天命之年,华发逐渐丛生了。
拖着小行旅箱从威利大厦的电梯出来时,你看到了十二楼极其熟悉的旅馆铁门敞开着,仿佛那年你离去后,它就这样一直敞开着等你回来。柜台还是在老位置,只是以前守在柜台的师奶却换成了一个妙龄女孩,口操纯正的普通话,语调抑扬顿挫温婉有致,不存半点粤腔。你问起台湾游客入住多吗?不多,现在住户以大陆客为主呢,女孩秀丽的短发在她说话时轻轻晃动着,娥眉淡扫,公式化的回应。待到护照资料填妥后,指了指四号房,就将房间钥匙交给你。你顺着指示,往那有点阴暗的走廊走去,打开房门,里头迫仄窄小得几近没有转圜的空间,只安置了一张床,以及小小浴室。无窗,宛若悬于高空的洞穴,这是你熟悉的场景,三百五十元港币,与二十二年前港币两百一晚对比,无疑涨了接近一倍。然而你知道香港居大不易,寸寸黄金地,所以人命有时贱得比不上香港的房价。上个月你才在报纸上读到香港两坪大的“劏房”,竟然月租要五千港币,与妻谈起,她头抬也不抬地说:啊,那是人住的地方吗?
你把所有的情绪和行旅箱安放在床边角落,在这可能不到两坪大的房间内,扭开了电视频道,映入眼帘的新闻报导,是反送中群众聚集于金钟一带的画面,示威者有些撑着雨伞或挂着口罩,企图占领金钟政府总部,而正与举着警盾的防暴警方叫嚣对峙。添美道和夏悫道上的示威群占领了一大片街道空间,处处杂沓喧闹,腾腾如沸,突然听到有人竭嘶地高喊:我哋有二百万人!我哋有二百万人!声浪由电视画上涌出,在狭小的房间内不断回荡,如潮水般冲撞着你的耳膜。于是你默默地把电视关掉,让房间瞬息回复一片寂静,回复到千古沉睡如洞穴一般,就只听到门顶上老旧的空调呼呼呼地轻送着凉风,而灯光却把你的影子,淡淡薄薄地贴在了白墙上。
你想到二十二年前的七一那晚,一大片人海,大家也是在雨中撑伞,却没有叫嚣和呐喊声,只是静静,兴奋的看着烟花开出了缤纷七彩的夜空,维多利亚港上的繁华大梦,随着乍开乍灭的烟火,投影在高楼大厦的玻璃面上,激溅出了万分亮眼的幻影,蓬蓬盛开与累累凋落,成了历史划出精美弧度的赞叹,嵌到记忆中去,却也亮到了心里。
那时牧涵说,回归了,她更没有翘家和翘国的理由……(待续)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