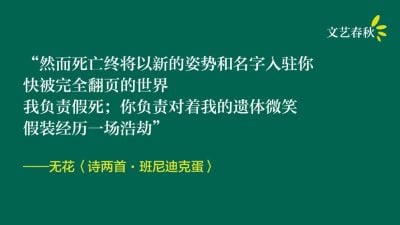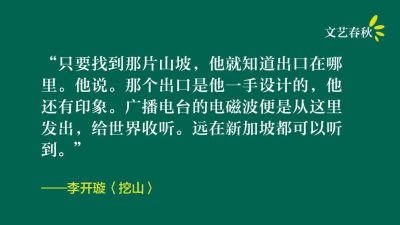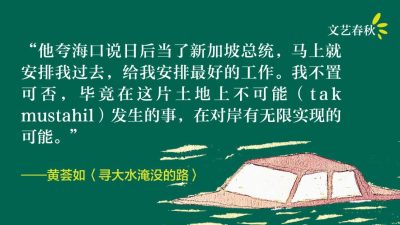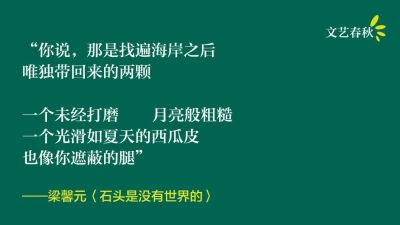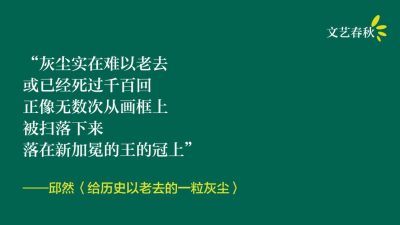ADVERTISEMENT
黑夜追逐我,我追逐太阳。失明或许是迟早的事,但我没有放弃阳光的毅力。
人们以时间与钞票交易,白天变得很短。当我从钞票堆里爬出来之时,大地已是成熟的橘橙色,鲜亮而通透,令人想咬下一口。
我总在那时忍不住直视最后的余晖,直到它被黑夜吸干。
据说隧道的另一端拥有全部的光,不分时间与地点。那里的人们不知夜之孤寂,他们一直醒着,但他们不疲惫,是光给了他们能量。他们趋光般生长,永远以朝拜的姿态,仰望有光的方向。
关于隧道的另一端,吸引着我和阿火,如孩子对圣诞老人的渴望。我们想要的并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一个愿望。近来,阿火的渴望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话题,快从他的胸口爆裂出去,再也谈不下去。他想到隧道的另一端。他说,只是看一看。
我犹豫许久——万一,万一隧道的另一端只是传说?我如何能轻易放弃我的碉堡?我所知道的人,他们去了隧道的另一端,就没回来。我没有认识哪个曾经往返的人,告诉我一个事实。
阿火没有再找我。我知道他已经抵达隧道的另一端。
他必定带走了所有钞票,在抵达那只有光的另一端之后,一路花光。
我只是猜测。阿火未有给我捎信,诉说另一端的消息。那隧道,那光,那些拥有全部光的人们,是否有令人向往的形状和温度?
我带走所有钞票,准备在抵达那只有光的另一端后,花光就回来。见了阿火,我一定回来。
夜班的巴士沙哑地发出引擎声,排气管呼出疲态的烟,藏了往事与秘密的黑烟,如此刺鼻,如此难噎。
双程巴士,一天一班,回程是明天早上。目的地是隧道的另一端,坐满即开。巴士里仅剩一个空位。每双眼睛轮流瞄向那张空座,或许瞄了九百九十九眼,空座会出现人影,巴士便能出发。
第三百六十五眼时,背着双肩背包的男子跑上了巴士。我听见那些被压抑的欢呼声,在巴士里此起彼落地绽开。那些曾瞄过空座的眼睛,为了避开和男子四目交投,凌乱地扫视巴士的顶部、地面、前座人的后脑勺。
男子戴着小圆框眼镜,巴士内的灯光反射在镜片上,我仍可看到他恍惚地寻找那唯一属于他的空座。我用食指伸向斜后面,倒数第三排的位子。他依循我指的方向发现位子后,快步走进去,驼色背包紧附在他的背后。
我好像看见他嘴角微幅的上扬,但那不重要,我只等着巴士开动。
冷气孔洒出的冷气拨动着绿色的窗帘,绿色的窗帘拍着雾气的窗,雾气的窗朦胧了路过的景色,路过的景色垫在投影在窗子的我。我的眼睛很透明,可以直视我脑里的空白,里面没有阿火也没有光,只有因等待而停顿的思索。侧身倚在椅背的身子很僵硬,而朝往隧道另一端的心情是一条直线,在无人相识的巴士里,它不会上升或跌宕,只会跟着巴士向前驶去。
当我的眼珠想闭上的时候,巴士此时于隧道的关卡前停下,给折返的乘客下车。他们只有一分钟,下车或选择前进。一分钟很长也很短,可以爱上一个人或忘掉一个人,可以恨一个人或原谅一个人。在难以拒绝或被拒绝的沉默里,一分钟等同于永恒。
在最后十五秒,我身边的乘客迅速站了起来,大跨步地走出去,然后传来他步下台阶的蹬蹬蹬。他走过我的窗外,走向回去的路,走在他改变决定的仓惶中。
司机踩下油门,吃力地拖拉着巴士前进时,窗子的倒影出现那背着双肩背包的男子。他静止了两三秒,就在我身边刚空出来的位子坐下。我一直没有转头看他,继续假装睡着,继续我不想应对的应对。我记得他展翼的粗眉,深蓝色的外套,以及进入错误时空的表情。
隧道是长长的食道,吞下我乘搭的巴士,夜空被隔绝在外。隧道的黑淹没视野。黑仍追逐我,我仅能寻觅隧道墙上忽隐忽现的照明灯,逃避空气中弥漫的压迫和窒息感。我追随光,赖以为生,即使在移动中的巴士里也如此。
我身旁的男子仰着头,但他的脸不存在于我的余角视线,凭直觉猜测他的举动太吃力。在我准备用睡眠为自己设下一道屏障,他却用只有我听得见的声量,缓缓吐出关于他的事情。
我不想知道,却记起他说的每个字。他嗜光的情人偷溜到了隧道的另一端。他预想了各种隐情。可能情人在另一端已有新的情人。可能情人已经不爱他。可能情人只要有光就什么都不要。
他们曾一起到过隧道的另一端,并且彼此约定不再回去,但情人毁了承诺。
他斩断几年的胡思乱想,现在要去找他的情人,只为一个答案。此趟独行的他谁也不认识。他一上巴士,我是唯一一个跟他“说话”的人,因此他选择坐在我的身边。我漠视他,比深夜的街道安静,比晚风冷。我不愿留下或带走任何声音或眼神。
我不想接近光,虽然我沉迷于光。当光贴近我,我只看见白,没有深浅。美丽的事物必然具有限制,才会持久美丽。阿火对光的渴望,区分了我和他的深浅。
阿火和我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手里各自握着一杯热茶,杯里长出白色轻烟。窗外有大雨,薄雾萦绕外头的山与房屋。空气中的湿冷有一种既郁闷又安定的味道,无奈的认命。
如果拥有了全部的光,你想做什么?
阿火看着窗上的雨珠问我。
我从不想如果的事情。我用清脆的声音回答。
阿火没有追问,好像他接受了我的答案。我当时没有想到,那次之后我将到隧道的另一端与他相见。
巴士总有抛锚的时刻,比如在距离目的地还有五公里的地方。巴士上的灯亮了,冷气没了,空气像死了似的。呼吸声、叹气、私语没有目的地闲晃起来,悬浮在空中。
我和有些人一样,从另一个世界刚醒过来,而隔壁的男子和有些人一样,他们一直醒着,并且第一时间知道这个世界的每个过程。
凌晨三点半,我们终究来到了隧道的另一端,虽不是终点站。
光怎么进来?何时进来?我后悔我是闭着双眼来到这里。有些事只能在乎结果。坐在我隔壁的男子曾经来过,但我没有问他。我不想因此开口对他说第一句话。
饱满。浓烈。珍珠色。这里的天空没有云。光从蓝天赤裸而下,直至地面。我脚下的石板路,享受着光的覆盖,平滑而明亮,有点骄傲。我是一个不起眼的路人,鞋底与地面之间没有欢快的摩擦。
看得入神,光几乎吞噬了我,身体快不是我的身体,随即在空中云般飘走。当我想起对街的狗越过马路叼走一只小狗,想起花斑纹的鸽子停在电线杆上落下颜料般的粪便,想起绿色的蚱蜢攀附在我的窗上摊开每一条腿,想起楼上晾的衣服被强风卷到空中终于自由,我就闭上眼睛。我终究想起失明的事。
双肩背包的男子走在我的前方,他从口袋拿出一张纸,边走边看,一会儿就收进口袋。走到分叉路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双唇微微抖动。或许是想问我什么,或许是想跟我道别,但那都不重要。在他可能开始下一步行动前,我已转身走在自己的路。
过了写着“市区”的标示牌后,我没有遇见一棵树,或一片草地,只见一座宽阔的广场上坐满了人。钞票四散一地,没有人在乎钞票。他们来到这里后,才知道光是一切,钞票毫无用处。他们仰着头,张着松掉的嘴,和光对视。
在一个仰卧的人和一个盘坐的人之间,我找到容我坐下的位子。
嗤嗤笑声在各处奔流,混着没有高低音的歌声,揉成一团细碎的杂音。我寻找音源时,才看见人们的眼珠都是白色。黑色的眼珠在光下日久褪色,眼睛附属在光之下。他们似乎都看不见我,但我确定他们只看见光,因为他们会张合眼睛,贪婪地汲取光的滋养。黑色越来越少,稀释在迷蒙的满足里。
只要有光,他们就能活下来。他们忘了水与食物,仅剩下呼吸的自觉。脸庞瘦削,身子如薄纸,他们仍旧在光里苟活下来。我看见他们,却感觉不到他们,干枯的躯壳里有破碎的回音。
背着双肩背包的男子来到我的面前。他的身子遮挡了光,形成一道黑色的身影,完全看不见他的脸,我却记得他的声音,那是一路上萦绕在我右耳的声音。
我垂下头藏起惊讶,捂着脸忽视他的存在。他知道这广场上一半的人,他们坐在这里已有许多日子。光给了他们一切,他们也给了光他们的一切。
那盘坐的人曾拍了三百万张照片,有逆着风整理懒洋洋浏海的女孩,有松了的鞋带上一只鬼祟的甲虫,有侧躺在枕头上的发像在追逐某个不能实现的愿望,有毛毛虫在叶上啃噬出一个歪曲的心型。他的相机从来没有给他带来名或利,他在暗房里挂起每一张怀才不遇,彩照日渐黯淡,甚至开始曝光过度,都变成白。他就追随了光。
仰卧的人曾错过回望一双眼睛的凝视,而那双眼睛后来住进了别人。他错过一场将被表白的约会,而那场约会的对象变成了别人。他错过说我喜欢你,只问了你是否曾喜欢我。他追不回时间,就在光里幻想他倘若改变选择的当初。
这里的光究竟从哪里来?我仰望天,闪亮的颗粒如尘埃落下,在空中活脱地游移,以为是蝌蚪,却没有尾巴。光里的颗粒线条过于明显,我因看穿了而失去兴趣。必然是谁或什么造了光,迷惑容易动摇的意志。我追逐的是太阳,随时间变更颜色的光芒,照映在我的振作和倦怠之间,阻隔在我的堕落和迷惘之间。在思念和绝望之间,一束阳光有蒸发泪水的能力。
背着双肩背包的男子走出我的思考,去寻找他久违的情人。我从静止的人们走出来,去寻找我的好朋友阿火。回程的巴士就要开了,我要带阿火离开这里。
如果他也能清楚看到闪亮的颗粒,他便会明白我们不应被支配。
我向空中高呼了他的名字,却没有人看向我,仿佛我没有发过声音。光紧紧包裹着他们。他们的其中,必定包括了阿火。
当我想再高呼,我被摀住了嘴,带到广场外。
唤醒沉浸在光里的人,是危险的。背着双肩背包的男子怒视着我,瞪出龟裂的双眼。
情人呢?我忍不住问了他。
找到了。(待续)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