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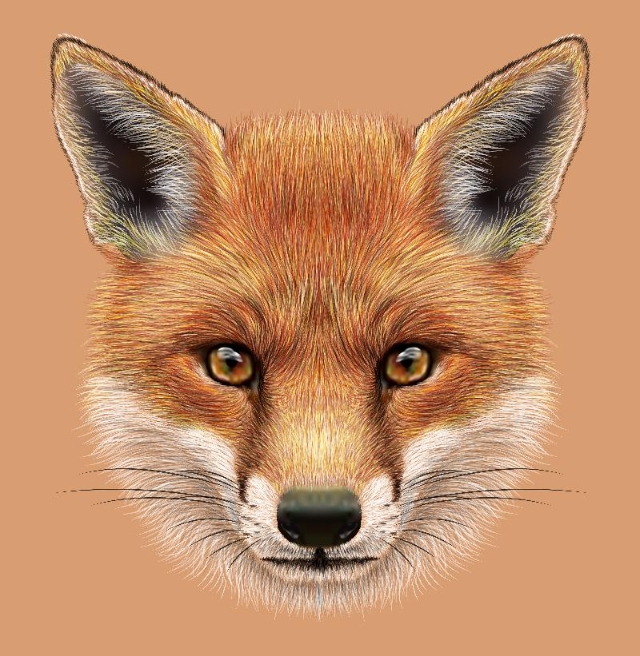
ADVERTISEMENT
旧港来的?
穿著卡其色制服,神情漠然的马来入境人员,从口中吐出发音跳跃的英语。也许是因为面对官员查问的焦虑(纵使我事前已经多次默默地练习应对),或者是一直折磨著我的肠胃不适依然未曾平服,我在第一个瞬间没有听懂她的提问,以致心虚地呆了半秒。在下一个半秒,当我察觉到对方的眼神流露出些许的不耐,我才恍然明白她的意思。
我连忙用英语说:是。
可是,在我恭恭敬敬地递上的护照和临时工作批文上,不是已经把我的来处写得清清楚楚的吗?何必多此一问?难道明知故问是彰显权威的方式吗?转念又觉得奇怪,她刚才说的是「旧港」吗?如果明明说的是「旧港」,我为甚么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
在我的脑袋繁忙地作著各种推想的时候, 入境人员已经像拨开秽物般把文件在案上推过来,不屑一顾似的别过脸去。我一手抓住文件,一手拖著手提行李箱,狼狈地穿过了检查通道,感觉犹如受到难民的对待。我好歹也是被邀请来当访问学者的,绝不是黑市劳工或者偷渡客。这个国家对待客人不是应该客气一点吗?「旧港」是甚么鬼话?
我的肚子又再痛起来了。
今天早上,打从坐上的士前往机场的一刻,心情已经有点不安。当车子在东涌的公路上停下来,我便知道堵塞机场传言真的应验了。我那反映现实的肚子,也开始发起了不合作运动。幸好我已做好准备,提早了两小时出门,情况未至令人绝望。我和许多因为交通瘫痪而需徒步前往机场的旅客一样,顶著当空的烈日,拉著大箱小箱,气喘吁吁,合成一条长长的逃亡队伍,低头认命地往目的地进发。
沿途还有为数更多的穿黑衣的年轻男女,浩浩荡荡,容光焕发,青春可人,有说有笑,心情显然截然不同,好像在大伙儿远足一样。他们在空旷的路上戴著口罩,拿著标语,边走边喊口号,一呼百应,情景煞是壮观。几个青年见我苦苦挣扎的样子,主动上前帮我拖行李,还连连鞠躬说:不好意思!辛苦你了!我听得有点莫名其妙,但有人帮总好过没有。
足足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达机场客运大楼。善意的青年们把行李交还给我, 跟我热情地挥手,转头便加入堵塞机场的队伍里。我还奢想著他们会帮我开路,但看势头他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我的敌人了。说敌人的确是有点夸张。他们对旅客全无敌意,但是,唉,就是很抱歉但也要堵塞你的去路的意思。恕我孤陋寡闻,这种抗议方式应该是世界首创的吧。虽然被拖延得很无奈,但至少也算是长了见识。
人到绝境,有时会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干劲。我压抑著肚子的叛乱,顶著沉重的行李车,发挥推粪虫的毅力,在厚厚的人堆中挖掘隧道,花了半小时,好不容易来到了办理登机的柜位。寄运了大件的行李,又经过另一轮奋斗,才到达离境大堂的禁区闸口。就在我向守卫人员出示电子登机证的一刻,手机震动了一下,萤幕上出现了一条讯息。
是秀彬传来的。她原来也身在机场,问我是不是今天上机。
我回过头去,伸著颈,踮著脚,尝试在人群中寻找她的身影。那就像在万头钻动的蚁窝里寻找其中一只蚂蚁一样,当然是徒劳无功的。还来不及眨眼,我便如同被吸进黑洞的光子一样,身不由己地随著焦急的旅客们越过了事件视界,堕入了平行世界的领域,跟原来的现实完全截断了关系。也记不起自己是怎样通过保安检查和离境身分确认系统的,只知道自己站在禁区的免税商店外面,手心冒汗,颤抖著手指在手机上写了回复:我已入闸。
在等待登机期间,我有一半时间瑟缩在椅子上,盯著头顶的萤幕,深恐自己的航班会宣布取消。另一半时间则躲在厕所里,为肠子绞痛却无法脱颖而出所折磨。不希望出现和渴求出现的结果成反比,对疲弱的心脏施以两面夹攻。最致命的是,秀彬一直没有回复,持续处于离线状态,令人濒临心死。我觉得自己随时会在候机处倒下来。
对于自己猝死的情况,已经设想过不止千百次。所幸亦已不止千百次生还的纪录,要不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每次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的,但每次之后还是需要再次的安慰。结果安慰也成了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因为你没法知道,哪一次的安慰会无效。那也即是真的最后的一次。在候机室没死,不代表不会在机舱里死。在地上没死,不代表不会在空中才死。未死的一刻,总会接续著将死的一刻,如此类推,假死复假死,直至真死的临降。人生终必在果然死去的一刻,才能得到永恒的解脱。我从小怕死,可能就是我研究好运和厄运的数学理论的动力。把疾病转化为科学上的创建,是祸是福,也讲不清楚了。
老实说,在机上真的有一次死掉的机会。当我在自己的座位颓然坐下,抬头一看,一位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纱笼式制服的空姐,正踮着脚尖,高举着双臂,帮客人整理头顶行李柜的物品。那完全伸展的纤长的腰身,把我吓到差点儿心脏蹦出。那身形和姿态,竟然和当年的海卿一模一样,害我以为自己回光返照,命不久矣。
在晕眩间听到有女声以唱歌般的英语跟我说话,对准焦点才发现是刚才那位空中服务员,正弯着腰问我要不要什么帮忙。看来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我向她要了杯清水,把放在衬衫袋里的镇定剂拿出来,却因为手抖而无法把药片折成两半。结果又要劳烦对方帮忙。喝了水,服了药,空中小姐收下了杯,嫣然一笑。此时我才发现,她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海卿。
服药之后症状稍微舒缓,至少觉得离死还有一段距离。在4个小时的航程中,飞机多次遇上气流。我靠着看烂片企图挨过凶险的南海上空。空姐的殷勤服务,却慢慢由安慰变成滋扰。这当然不是她的问题,只是她刚才令我想起海卿,关于海卿的回忆便没完没了地涌出来。那曾经让我自视为一生最大的幸运的海卿,那激发我创造出好运的数学定理的海卿,那陪伴着我在严寒的北国完成博士论文的海卿,那给我诞下至爱的女儿秀彬的海卿,此刻竟然成了世上最不想相见的陌路人。那是不是说明了天道的公平,行好运后必行衰运的定理?最后还是要多谢海卿,用离婚来启发我完成学说的另一半,以衰运定理和好运定理互补,找出了熵均衡和最佳讯息点的计算方法。没有这些学术成就,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个远赴新加坡的航班上,接受命运的戏弄了。
◢样貌不能原谅的俊男
先生,需要什么帮忙吗?小姐,需要什么帮忙吗?
看着空中服务员无差别地分派着细心的关怀,我开始觉得有点生气了。她那挽成白果形的发髻也由贤慧而变得碍眼。这样的对白她每次航程也不知会说上多少遍。殷勤的态度也不过是伪装吧。当慰问变成了例行公事,最温柔的声线也会令人生厌。我想说:你以为我是那种不断苛求别人关心的可怜人吗?或者是那些借机亲近女服务员的色中饿鬼?你尽管去照顾那些吹毛求疵的乘客吧。这样一气,居然暂时忘掉了身体的不适。飞机也在此时徐徐降落樟宜机场了。
于是,乐于助人的空中小姐和木无表情的入境人员,都同样刺激着我的神经,令我发狂。唯独是等待行李的时候,手机终于收到秀彬的讯息,才在窒息中透出一丝清新的空气。她祝我一路顺风,又叫我不用担心她。我想回复,但又迟疑,害怕过于频密的联络会令她觉得我唠叨,徒生厌烦。我情愿最后是她回复我,而不是我回复她,眼巴巴看着她已读不回的标记。真是一种连自己也觉得可怜的心情。
领了行李,我拖着这半死不活的残躯,继续那才刚刚开始的苦路。在通透的玻璃墙外,站满了接机的人,清一色挂着充满期待的神情。受到他们的感染,我也不免要装出被人期待的期待,向左右四方展现没有目标的笑意。正当我逐一搜寻那些写着访客名字的牌子,有人便在后排叫出了我名字。我朝那方向望去,一个高个子男性向我挥手,并且大踏步往左侧的出口走去。
欢迎来到新城!
迎上来跟我握手的是一个样貌不能原谅的英俊的年轻男人, 约三十来岁, 穿醒目的白色恤和天蓝色窄长裤,乌黑浓密的头发梳理得油亮坚挺。
胡德浩教授!您好!幸会!我是江志旭,是江英逸院长的儿子。我父亲这几天出国,我是代表他来接您的。
英俊男以华语跟我打招呼,同时抢着帮我拿行李。我一时间听不清楚他的名字,幸好听懂他父亲是谁。江院长就是邀请我来南洋科技大学当访问学者的人。
趁对方递上名片,我悄悄瞥了一眼他的名字怎么写。看懂了怎么写,又忘了怎么念,于是便只有含含糊糊地回应道:
啊!是江公子吗?令尊一定很高兴,有一个像你这样一表人才的儿子!
我本来是想说“出类拔萃”的,但不知道后面两个字的华语发音,便及时换了另一个4字词,同时很厌恶自己说出了这种奉承的客套话。
没有啦!我这些只是小角色而已。胡教授才是真正的大学者,大天才!谁不知道您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专家,领导风潮的大人物!
这个后生口若悬河,像变魔术般一顶又一顶高帽扣下来,令人难以抵挡。我因为华语不流利,便只有克制地含笑以对,慎防露出了过多的洋洋得意的神色。
我记起他刚才好像说欢迎我来到“新城”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叫法?也可能是我听错。隔了一段时间,不好意思回头去问,也就作罢。
听这小子自我介绍才知道,原来他是念机器人学的,在美国拿博士学位,再做了几年博士后研究,去年才回到南洋科技大学任助理教授。
回来贡献国家嘛!
他有点尴尬地笑着说。我便恭维他说:回来当父亲的左右手吧。
他谦虚地摇了摇头,说:我跟家父还差很远呢!
我心想,这个人说话会不会太乖巧呢?于是便忍不住调侃他说:你长得那么“衰”,不去当明星真是太浪费。
老师,你说的是“帅”吧?
想不到我自作聪明,反而自取其辱。我连忙更正说:对!是“帅”!不好意思,我的华语太烂。
不会啦,老师不要介意。
我的意思是,像你这样的外型,搞什么robotics呢?他举起右臂,做了个健美先生的姿势,说:
人体不就是一台机器吗?
就是,就是。有没有听过“年纪大,机器坏”?
是广东谚语吗?他好奇地问。我指了指自己,说:就是说我。
不会吧!胡老师还很精壮,只是五十出头,知天命之年呀。
天命,我也想知啊。
老师不是已经知道了吗?用您的理论,连天命都可以算出来了。
人算不如天算。我摇摇头说。
那也对的,有时候人的确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我听他这句话很熟,但不知道出处,顿时有点心虚。他不像一般只懂说英语的新加坡仔,似乎颇富中华文化素养,把我杀了个措手不及。

◢到Jewel Changi看巨型水柱
机器男问我来过新加坡没有。我回答来过两次,一次和家人来度假,一次来开研讨会。他问我家里有什么人。我便直言和妻子已经离婚,女儿20岁。他立即说了声抱歉。我心想,抱歉什么呢?又不是你害我离婚的。他像是为了补偿似的,兴致勃勃地说:
那老师一定未去过Jewel Changi了。我对珠宝没兴趣。
不是卖珠宝的,是樟宜机场新建的室内奇观,被誉为新加坡的新地标。从客运大楼可以通过去。老师应该会感兴趣的。
类似Garden by the bay那种东西吗?你们新加坡人最喜欢把树种在鱼缸里。
哈哈!是这个概念,不过比种树更夸张。反正就在旁边,去看看啊!老师肚子饿吗?里面有很多餐厅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
虽然给肠胃不适折腾了大半天,但给他一说,也觉腹中空虚,便硬着头皮跟着他走向那什么Jewel的地方。志旭给我在入口寄放了行李,说这样可以走得轻松一点。
一走进Jewel的内部,确实是给眼前的景观震撼了。完全料想不到,在机场3个客运大楼的中间,会有这样的一座感觉诡异的巨型装置。抬头望去,天穹呈稍不对称的圆形,整个外壳以网状支架组成,每一个三角网眼上是透明玻璃,形成一个采光极佳的笼子。屋顶中央像个漏斗般凹陷,线条向内弧成一个圆圈。环绕着圆周有大量水流如圆筒形的瀑布般倾泻而下,形成一条垂直矗立的巨型水柱。流泻不断而又维持固态的水柱,动极而静,似实还虚,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的幻影。
这是全世界最大型的室内瀑布。有个名堂的,叫做HSBC Rain Vortex,汇丰银行雨漩涡。不知是象征吸金大法,还是预言某种金融灾难。
志旭以带点调侃的语气说。
网上有人说它像a toilet bowl flushing all day long。其实从外面看,整个建筑是一个巨型的doughnut。一点也不像Jewel。
是黑洞。我冲口而出说。
胡老师,您的想像力很惊人啊!听你一说,那些线条和结构又真的很像科学书上的黑洞构想图。
就是啦!就是啦!你也看出来啊!那个漏斗形瀑布的入口位置就是event horizon。
我好像找到难得的知音似的,有点激动地指点著。
老师您想上去看看吗?上面有一条Canopy Bridge,可以从近距离观察。
不用了!太近event horizon会没命的。我连忙作出严正的拒绝。
志旭也不勉强,只是耸肩笑了笑。这时我才注意到在玻璃球的下方,在接住瀑布的圆形中央水池的外围,是个种满绿树的山谷。不是一个普通的花园,而是一个可以沿斜坡拾级而上的人造森林。
下面绿色的这一块也该有个名堂吧?
没错,叫Shiseido Forest Valley,资生堂森林谷。听来是不是有点滑稽?
不,是恐怖。你听过恐怖谷理论吗?
当然听过,搞robotics的怎会不知道。这是个活生生的恐怖谷。里面活动著的,说不定都是automatons。
我们都是automatons啊。
就是!这样理解就顺理成章了。
老师我们去逛逛恐怖谷吧。从中间穿过去就可以。
我不爬山了。太辛苦。
穿过所谓的「山谷」, 绕过瀑布水池, 猛烈的冲击声震耳欲聋, 强劲的水势令人心跳加速。汇丰银行柱插进资生堂谷,这是怎么样的鬼配对?我好像被不断当头棒打一样,开始眼花撩乱。
拐进树林后面的空间,团团围绕著店铺,几乎都是外国名牌,看不到半点新加坡的东西。说白了,这其实是一个假装自然奇观和户外历险的购物广场。我很快便对它失去兴趣,只想快点找个地方医肚。
我们在最近的一间日式餐厅坐下来。我随便地点了个炸猪排定食,志旭则要了刺身拼盘。可恨的是食物来到面前,胃口却又全失,只能勉强地吞几口。志旭为了尽接待之谊,努力地拉扯各种话题,一下谈新加坡的状况,一下又问到香港的情形。说到今天堵机场的行动,他露出不解的神情,我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志旭侧著脸,瞇著眼说:
很难想像,如果这个Jewel给人群堵了,会是甚么样子。
应该会很壮观吧。
他半笑半咳出来,说:也算是一种奇景。
我其实不觉得好笑,虽然想陪他笑一下,但实在笑不出来。而更不好笑的事情即将发生。筷子从我的指间掉落,我连忙以双手按著桌面,觉得整个身体也在颤抖。我问正在把油甘鱼刺身放进口里的志旭说:
你觉不觉得,这个东西在动?
甚么东西?
这个doughnut。
哪个?
这个。这艘太空船。甚么太空船?
你不觉得这个Jewel其实是一艘spacecraft吗?中间的瀑布其实是量子发动机。
老师您又想像力爆发了。
不是想像,是真的。这个doughtnut,「它」就是新加坡!它要升空了!你感觉到吗?它在震动了!
我紧紧地抓著椅子的金属扶手,浑身不能自控地抖动。
老师,您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志旭有点担心地凑近,轻轻地摇著我的肩膀。我摘下眼镜,把脸埋在双手里,深深地呼吸著,试图压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奇怪情绪。
没甚么!从今早开始已经有点不舒服。不好意思,我吃不下了。
没关系。这样吧,我给老师买个便当,然后送您回去酒店休息。晚点觉得肚子饿的话,可以拿出来吃。
志旭关切的语调令人安慰。真是个好孩子。他好像不想加剧紧张气氛一样,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向餐厅经理招手,跟对方说了几句话。然后不缓不急地走出餐厅,左右张望了一下,向左方走去。过了一会,他拿著一个纸袋回来,打开向我展示,说:
我见附近一间店子的 很不错,便买了几种口味,老师可以带回去慢慢吃。
不知这个人是天真、幽默,还是恶作剧,居然还买这东西给我,但我已没有力气拒绝。
外卖便当送上来, 志旭便抢著结了帐。在Jewel出口拿回行李, 到停车场坐上他的白色。年轻人嘱咐我不要说话,又问我要不要听点音乐。我说不必,他便默默地开车。看他的样子,如果我是年轻女生的话,会觉得他除了是个「型男」,也同时是那种体贴入微的「暖男」吧。想起便立即打了个冷颤。
听他说机场在岛的东端, 南大在西端, 车程要大半个小时。我并没睡著, 但意识十分模糊,像半个死人一样挨在座位里。只知道窗外很多树,有很多光鲜的高楼,有一种人工的整齐感。当志旭说,老师我们到了,我才注意到草坪上的一块南洋科技大学的招牌。在校园内绕了些路,车子停在一间小型酒店前面。我会在这里先住两天,然后才搬到教职员宿舍。
可能因为还未开学的关系,校园气氛冷清,郁热的空气中渗透著莫名的寒意。进了酒店,同样是光鲜而无人。志旭帮我办好入住手续,送我到三楼的房间,恭恭敬敬地和我道别。临走前不忘把那袋doughnut塞进我手中,说:
家父本来叮嘱我要帮胡老师洗尘,但看来今晚还是不要打扰老师了。您好好休息,我明晚或后晚再请老师吃饭吧。
在英俊和体贴之外再加上客气,这个组合教人难以忍受。我禁不住说:
谢谢啦。不过,请不要再用「您」字。这个称呼在我们广东话里面是没有的。也不要胡老师前,胡老师后的。大家是同事,即是同辈。叫我胡德浩。
是!胡德浩──。他即时把后面两个字吞回去。
关了门,我把纸袋抛到床上,五颜六色的甜甜圈掉了出来,滚动了一阵便四散在雪白的被子上。也顾不得那么多便冲进厕所里。被镇压了一整天的肚子,终于得到解放了。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