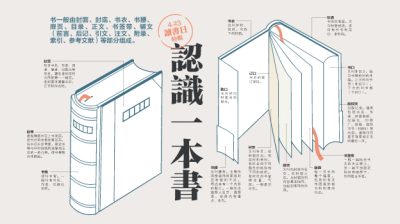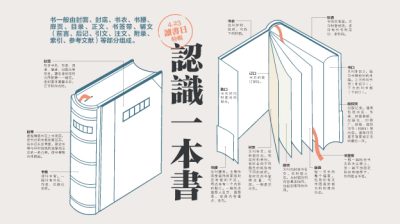这一天,我如常开车载母亲去兜风。这时候的母亲特别安静,这是她每天都切切向往的活动。转个弯,发现天边的明月,我指向那里,问她:“妈妈,那是什么?”母亲望了一眼,欲言又止,想用马来话回答我,却说不出来。我说,那是月亮。母亲笑着点点头。
自行动管制令实行以来,母亲的沟通和表达能力可说是每况愈下。行动管制令和这有什么关系呢?那段时间,我滞留在工作的地方;二姐一家也不能和过往一般,每周日带着孩子回家。母亲的生活作息一下子被打乱了,在时空的混乱中,母亲各方面更显退化。那段没能回家的日子,偶尔我会担心哪一天可以回家时,她或许已经不记得我。每想一次,心就揪一下。
ADVERTISEMENT
一直以来,我都以“头脑退化”来陈明母亲的情况。终于这一天还是来了,我要面对一个自己从来不好好记住的音译外来词——阿兹海默症,或说失智症;然后,我的指头显得笨拙、不自然的在键盘上打出这几个字。经过搜索,原来,失智症是一种疾病现象而不是正常的老化,患者实际上已经生病了,应该接受治疗。资料上还说,失智症患者的记忆、行为及日常作息能力将不断恶化。母亲的情况正是如此。
为这事,我难过了好久。我总禁不住反复问自己,如果哪一天母亲已经忘了我,那会是怎样的画面和心情呢?内心的大涟漪往往止住了这样的想像,想不下去。对我来说母亲犹如一座山,稳稳踏实的,似乎人生各种狂风或暴雨都不能让她为之而动摇,她仍然屹立着让我倚着她,紧紧的。这是我对母亲最简单的陈述。这个家,因为母亲而叫每个回家的人有了归宿和安慰,尽管她如今像风中残烛那般脆弱,也像孩子般嚷着满足她的许多要求。
多少时候,我望着母亲,那是熟悉却也遥远的面孔。熟悉,那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是我生命的大山;遥远,是因为她不断走向老去的一方,我在这里望着远去的她。后来渐渐明白“岁月是一把刀”是怎么回事。一次遇见一位长辈,16年没见,他无法把我记起。他说,人老了,已经分不了是男是女了,都一个样子。这话深深烙在我心里,对年老的长辈多了一份怜爱。
母亲在13年前中风,虽然行动受影响,却仍能自理。两年前,母亲在一次摔倒并动了头部手术后,一下子破残了。破残,因为她开始不愿意行走,也开始失去部分的语言功能,同时不再能自理生活。
一次陪她到医院进行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师让她扶着两旁的栏杆学习走路。在她前方是一面大大的落地镜子。当物理治疗师指示她望向前方的镜子,往前直行时,母亲抬头望了镜子,很快又低下头,久久都不愿把头抬起。我在母亲抬头的那瞬间看见她脸上的错愕!大半年来她都不曾照镜子,那瞬间,她和我一样,看到了熟悉却也遥远的面孔。我鼻酸,忍住眼泪扶着她,鼓励她继续前行。
母亲还记得对我的爱
记得母亲那次摔倒后,我都睡在她身边。一个晚上,母亲起身夜尿了好几回,我就这样好几回在睡意中扶着她,内心有点烦躁。同时我却想到,我小时候也是这样,一夜让母亲醒来好几回,如今换我照顾她了。不久前听一位长辈朋友分享他过去把生病的母亲接回家住了好几年,照顾她直到她终老。他淡然的说:“小时候我跟着她,现在她跟着我。”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我看见小时候老是拉住母亲衣角的自己,那时候我老跟着她,紧紧的。是的,如今她跟着我们,紧紧的。只是,我懦弱的害怕陪她走到终老的那一刻,深怕自己站不住。始终,我需要母亲把我撑着才能更坚强。
母亲的失智症正迈入中期,很多事、很多人她都记不起了。但她记得我们是她的孩子,她知道我们叫她“妈妈”。还有,她还记得对我的爱。到今天我仍会对母亲说:“妈妈,我想吃榴梿,请我吃榴梿可以吗?”她都毫不迟疑的说好!近来我们的对话就只有那几句。“妈妈,我是谁?”“丹萍”“丹萍是你的谁?”“Anak!”然后接着说:“ Yang kecil.”我会再说,“妈妈我爱你吗?”“有,你爱我。”母亲知道女儿的爱,足矣。
母亲,虽然仅为风中一支残烛,但她却依然发光,依然温暖着我。小时候我跟着她,如今我依然跟着她;或许一天她不记得我了,我必然会把她记牢,紧紧的。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