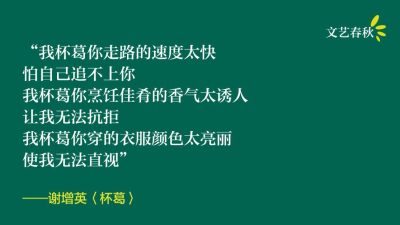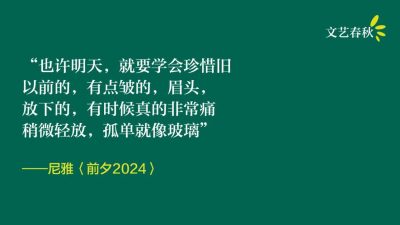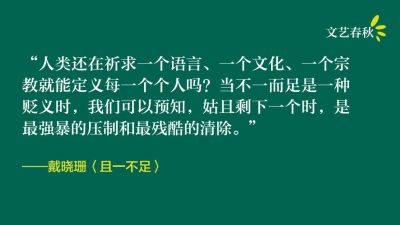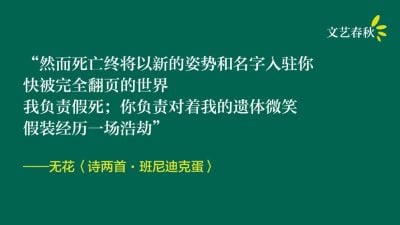ADVERTISEMENT
前文提要:我在客厅穿着鞋子走路。脚底和地板隔着一层薄垫,发出暧昧的细语声。它们初次相遇,对谈如此投机,像久别重逢的老友。我聆听着它们,在客厅来回踱步,直到夜晚降临,直到客厅的暗让我看不见自己的双脚。
这么一走,我不想只有自己穿着鞋走了。
我想起那只我错过的鹰。
我将几双布鞋装进我的背包里,背着它们翻越到黑先生的阳台。然后,我再从黑先生的阳台,翻越到黑先生隔壁的阳台。
这个家的主人是年轻的厨子,他和年轻的教师女友住在一起。两年前搬进来的时候,我在电梯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们如死去的人那般苍白,双腿像失去齿轮的机器,从电梯里不协调地走出去。这两年来,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们,但他们阳台晒的厨子制服、教师西装,总在每个早晨如盛夏的花醒着。
我把两双布鞋安放在他们的客厅里。不知尺码是否合适,仅凭一种直觉,去相信他们会把鞋子穿上。
死去的人不知道鞋子,装死的人不敢穿鞋。鞋是罪,仅限在这个国里。
我翻越了湿冷的墙,爬过人们的梦,在他们浑浑噩噩的日复一日,嵌入可能会带来恐惧,或惊喜的布鞋。多少个黑先生和他的妹妹都进入了陌生人的客厅里。
我沙发底下的布鞋越来越少,我偶尔会在路上看见穿鞋的人。他们穿的未必是我悄悄派的布鞋,也可能是他们自制的,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鞋子,各种颜色,各种材质和款式。
他们睁着眼睛走得很快,像是要到一个辽远的地方去,赶在某个时间,又或者赶在什么时候之前抵达。
“穿鞋的人都是妖魔,抛弃了自己的灵魂。”这个国如此宣导。
穿鞋的人被憎恨,也被诅咒。穿着鞋子变成一件危险的事情,很可能会被暗杀,但他们不会再把自己杀掉了。没有人比穿鞋的人清醒,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前往何方。
后来,少年们都穿上了鞋。他们穿着鞋子,快乐地奔跑在烂泥里、湿滑的公路、无人开垦的荒原。他们互相交换风景,攀过山的人知道海的味道,攀过峭壁的人也知道平原的狼嚎可以唤醒多少沉睡的兽。
少年们好奇鞋子可以带他们走多远。
我沙发底下的布鞋派完了。人们不需要我的布鞋,他们知道了获得鞋子的方法。
黑先生把自己杀掉的8个月后,我坐在空旷的草地上看少年们互相追逐嬉戏。他们穿着鞋,掌握自己行走的速度。跑,不是一件疼痛的事情。
嬉闹声在逐渐昏沉的景色中消止。一千名警察包围了那几个穿鞋的少年。他们除了穿着鞋逃跑,便无其他抵抗的办法,可他们连跑的出路都已断绝。警察堵满了他们可以移动的任何空间,连吸进的空气都是警察呼出的二氧化碳。
警察扒走他们的鞋子,然后折断他们的腿,从身体拆卸出来,只剩下大腿。警察又把他们的手拧断,又从身体拆卸出来。最后,少年们只剩下身体和头,躺在空旷的草地上,仰望天空中的云。
草地的草都被压扁了,破碎成屑,紧紧黏附在泥土上,直不起腰来。
这时候,天空中的云有的变成了雀,有的变成了鹰,少年们想向它们飘荡的地方追去,却已无法动弹,唯有眼珠在悲凄中转动。
少年们哀嚎却没有求饶,只为失去的手脚而悲伤。
警察将我带走时,像当初他们搬走黑先生的那个臃肿大水桶一样。这次他们没有携带搬运器具,他们喘着气,左摇右摆地扛起我的手脚,我离地两三尺,没有走路的机会。
厨子和他的教师女友把布鞋放在我的家门口,我自此不能走,也不能再说一句话。没有人会问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见过谁。他们都不觉得重要了。
我被安置在一个比冬天更白的冷冻库里,四面的墙没有一丝花纹,或浮凸的印记,门没有缝,也别说会否有一盏灯在这里发出温暖的光。
他们要我回到我的梦里醒着,在我醒着的时候死去,如摆布那些装死的人。
我看见我走到比这个国更远的远方,去寻找一种会让人大声发笑的草,听到荒唐的谎言会笑出眼泪,看到无耻的劣行也会笑到在地上打滚。以及,一种喝了会让人大声说真话的酒,无论对象是高是矮,是恶是善,都会勇敢地看着他们说话。这个国不存在这种草和这种酒,我把它们带回到这个国里,送给从未离开这个国的人,他们便会活在睁眼的时候,睡在闭眼的时候,而死去便在心跳停止的时候。
我看见我乘鹰归来,最终要让人们相信那云会化成了鹰,不是梦境。苍穹中一朵白色的云,我是里头凝结的一颗小水滴。
据说,少年们被警察拘留的时候,从一楼的抽风孔钻出来,然后自己坠楼而死。他们的头部都如蛋壳般裂开,血像蛋液弥漫开来,黏稠的血迹紧贴在地,一直都洗不去。
许多年后,会不会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死去?
据说,我也是自己从一楼坠下而死。我没有流一滴血,仅碎成一地的冰。
鹰和我在空中擦肩,在我死去的肉身上盘旋,盯着我光滑的脚丫,等待我溶化后释放第一抹血的味道。
我和所有杀掉自己的人都溶成水,渗透到地里,泥土像海绵那般吸收了我们,和我们融为一体。
地上长出了刺,人们不能再赤脚行走,痛会让他们不得不醒过来,痛到活过来,哭着走路,或愤怒地走着,不得不穿上鞋。
人们穿着鞋走路时,磨出嘈杂的声响,他们一天比一天走得更远,终究会走到这个国最高的地方,然后俯瞰这个国,便知道他们活在什么地方。
走得太远,知道太多的人总让原本站在高处的人恐惧。
看见这个国的人都穿上了鞋,我就能安心地笑了。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