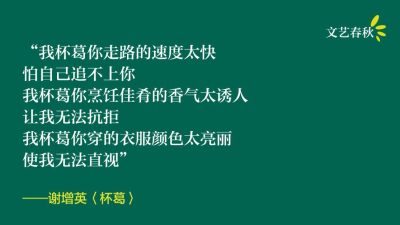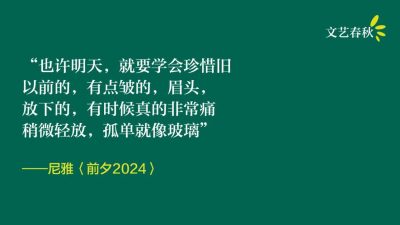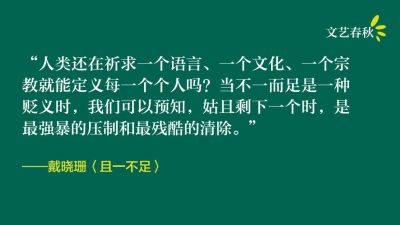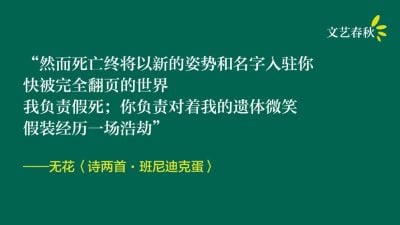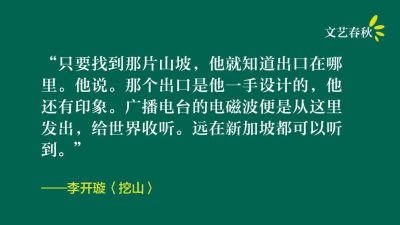ADVERTISEMENT
前文提要:我用香烟盒制成四方形盒子,铺盖适量的枯草,引诱白头翁来生蛋,可是等待好久,到了我的人工窝巢被风雨摧毁了,尚见不到任何鸟蛋……
山楂树绽开淡红的花朵,茂盛且常花期不断。成熟爆裂的山楂深蓝色,略甜,小鸟中以白头翁最常飞来啄食。说实话,在我童稚的心中,和品尝角度,无论风味或甜度,野山楂都不比山枣。只有在无可选择之下,我才采摘山楂以满足味蕾。
有一次,我在山楂丛里遇见黄国光,他在砍山楂树U型的枝桠,我好奇,问道:“阿光哥,砍枝桠做什么?”
他笑笑,“等下你就知道。我顺便给你扎一支。”
傍晚,他送来一支U型枝桠,U字尾端系紧两条橡皮筋,他说是“拉矢笛”,可以“射”鸟和“打松鼠”,说完他把一颗小石子挟在橡皮带的布块里,一手抓紧“拉矢笛”,另一手拉长橡皮,迅速一放,石子向天空飞驰,“啪啪啪”穿透叶片,不知坠落在哪个角落。
以国光的力度,真个足以打死一只松鼠。但我年幼力弱,胶皮筋拉不满,也射不远。从此我跟母亲割胶,颈上就多了一支橡皮“拉矢笛”,也无形中替我添加一份壮胆的力量——射鸟和松鼠,不过是幼稚的幻想。
黄家两兄弟,大哥国强已婚,只有二弟国光找我结伴同乐。
乡野间的男女都早婚,国强已18岁,我们搬来不到几个月,便遇到黄家办喜事娶媳了。黄崇叔颇有人脉,远亲近邻估计请了十多席,觥筹交错,酒罄席散之际,有个宾客步履蹒跚,有人要搀扶他,被他口唤“我没醉我没醉!”拒绝,径自要醉步走回家,不料“噗通”一声堕进井里。众人见了一哄而上,七手八脚把他抱上来。我生平第一次目睹酒徒失仪的尴尬和丑态,记忆深刻,所以一再警惕自己饮酒要适度。
在通向马路泥径旁边的那口井,是我们两家饮用的依靠,井湄有洋灰圈围绕,因我曾溺井几乎死亡的阴影笼罩,冲凉都结伴去小河。水井围灰涵也未必安全,醉汉掉井事件没造成悲剧,可谓幸运之至。
跨过马路,对面是一片汪汪的稻田,群鱼活跃,国光去田芭垂钓也常约我陪伴左右。他一连插下多支钓竿后,我们静静蹲在田埂上等鱼儿上钩,两人目不转睛望着那些鱼竿和丝线,浮子一牵动他即快步拔起钓竿,最常钓获的是鲫鱼、生鳢、塘虱,回来时手里握着一长串腥味,成为我们晚餐的桌上佳肴。
割胶虽辛苦,但也有享乐的时候,除了稻田钓鱼、小河摸虾,我们每个月也结伴去太平闲逛。“阿桂婶,我带亚弟去太平玩,可以吗?”有一天“水限”国光来我家,问母亲。
“好的,过马路你得多留意他。”接着母亲给我几毫子,嘱说:“买车票和吃东西记得自己给钱,记得啦!”
我高兴得像飞上天空。太平,呵太平,在大人口中车来人往的城市,我终于有机会去领略它的热闹了!
我们居住的地方叫“十三碑”,距离该从太平算起吧。十三碑意即13里,再上就是峇都古楼了。这条东北线由红黄巴士经营,从十三碑到太平路上让乘客一路上下,也不过半小时就进入市区车站了。
走下车站,我四处张望,汽车、行人、商店,四处一片繁忙景象,我根本没有目标,寸步不敢离开国光,担心一旦走失回不了家。那年我6岁,腼腆又胆怯;国光约十五、六岁。车站旁边排满水果摊和冰水档,国光东看西看,然后在一档冰水档前坐下,要了两碗红豆冰,我们嗦嗦地吃。首次吃红豆冰,红豆渗入玉米、葡萄干、冬瓜条等多样化的冰霜,那种甜而又冷的口感,真是舒服得难以形容。吃完我要给钱,国光压住我的手,说:“你不必,我付!”
吃完红豆冰,国光牵紧我的手,“来,我们去看电影戏。”说完我们一起跨过马路到对面街,进入游艺场,有座大建筑,就是电影院。游艺场内商店各行各业,琳瑯滿目,人影杂沓,但最集中人潮的地方是戏院,戏迷在小窗口买票。国光嘱我站在票窗的栏杆外,别走动,他去挤票。
国光持票进场,小孩全部免票。以木板搭建的戏院,虽有风扇,但人气拥肿,显得又闷又热。戏院里灯光昏暗,带票员用手电筒带我们去找座位。不久音乐停了,放映的时候,更是漆黑一片,银幕上出现人影。原来电影戏是这样的,我好奇地自言自语。
那天上映黑白粤语片,我似懂非懂。我懂得咚咚锵锵的震耳鼓声,故事内容虽国光略作解释,我像牛皮灯笼,略懂一二,但观众都静静看,我也只好沉默。电影戏人物的对白与移动,都深深地吸引我。似乎凡去太平,国光招我同行,形成了惯例;车资食用不让我付钱,母亲也渐渐不再追问了,但裤袋里总积着几毫子。有时我用作零钱打包红豆冰,让二姐也享受透凉冰冷的滋味。
某天,二姐和我在马路边玩,忽然一辆往峇都古楼的巴士抛下一包东西,我们追上去,有个人从车窗(注)伸出手往外望,指着地下,我匆匆一瞥,认得是堂哥。抛下的那包竟是饼干,一些压碎了,但我俩依然欢天喜地,蹦跳着抱回家向阿婶报告。
不久,堂哥就托人传话,他工作的园坵要招请数位胶工,是新树“街头”,问阿婶要不要接受。与父亲商洽结果,觉得好过啃老树,于是我们告别了那些接触经年的山枣树和野山楂,最依依魂牵的是我与国光哥的情谊。
早期大园坵的规划似乎千篇一律,我们住进的咕哩长屋与在硝山的如同一辙,吊脚、锌板,前门踏板斜梯。在工作上割新树比老树轻松,早上6点钟听到敲钟胶工才提桶执担子出门,由罗里分别载送到“行头”。天亮才开始工作,母亲的煤油灯悬之高阁了。
与长屋相隔不远有间独立平房,由洋灰与木板组成,周遭围着铁蒺藜,门栅开向两边,屋边由两只凶猛的狼狗守护着,看去气派十足,听说是“管迪力”(Contractor)的居所,像这样宽大的房子有好几间,每间却只住着一个“管迪力”。我心里对独立平房满是诡谲,连趋近都胆怯。
母亲和堂哥的行头相隔甚远,但早上6点准时出门,下午两三点钟就乘罗里回来了,园坵胶片是由胶厂制造的,胶工收集胶液过滤秤称后,即告完工。
●
园坵离开马路约两英里,两边不是排列有序的橡胶树,而是高耸繁杂的丛林,要走半小时才抵达路口。这是迁移峇都古楼园坵唯一令母亲纠结的地方。那时马共退居森林与英政府对抗,为防止华裔为马共提供粮食,英政府施行白米配给制,家家挂有米牌,以人头购置米粮。
这原本也非大问题,难处在于我们原居十三碑,米牌属于太平区,峇都古楼商店没有我们的米粮记录,我们的粮食依旧得回到太平购买。每月为采购而奔波,母亲也委实疲累不堪!而那条从园坵至马路的泥径,在我童年的心里,仿佛比十三碑的山径还更漫长呢!
来到大园坵,堂哥与我们又再合成一家了。母亲依然为家中的中流砥柱,去购买米粮和其他日需家常,全由母亲一手拟定,故去太平成了每月固定的行程。母亲勤劳克俭,总在工作后才和我出发,到太平采购完毕,已是薄暮时刻;回程在路口下车,大地早已昏沉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了。幸亏有堂哥,每次他在路口等候,准时且风雨不改。我们下车,把东西搬下,逐样放进藤框,由堂哥挑着走,母亲用电筒照路,三人踢响泥径的砂尘,树高而林密,天高而星远,到家灯火已阑珊。中流砥柱的母亲,为一家而默默付出,无怨也无悔。
注:40年代的巴士没有冷气设备,车行时木板/玻璃窗都推下,下雨时拉上。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