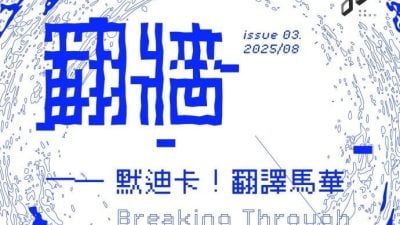【读家说史】廖文辉 / 著史难,读史亦难



编按:廖文辉的《马来西亚华人史》,全书不在“专”与“详”,而是“通”,着重在通识的掌握与历史意义的探索。关于“通史”,作者有话要说……

ADVERTISEMENT
胡适曾说:“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认为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我私淑的钱穆,个人认为是这方面的典范,能有广博的《国史大纲》,也能写出精深考据的《先秦诸子系年》。作为后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通史的著述是史学编撰的一种书写方式,在史学研究还没有转为专精之前,这种体例或者著述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史学书写。当论文撰写高于一切,社会学科所强调的问题意识胜于一切时,启蒙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书写难免渐行渐远,遥不可及,甚至有的学者还将通博书写视为洪水猛兽,最好不要碰触,似乎中国通史、东南亚史、西洋通史、世界通史,乃至环球史的书写,都必须倒入垃圾桶,这无疑是对史学研究不明就里的盲动。
通史的著述自然有它的特色和局限。通史强调“通”而不在于“专”,在“博”而不在“详”,为此在书写时就有几个须要考虑的面向。首先是主轴,也就是论述切入点的确立,即所谓的视角,是要站在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来论述,乃至立志将各方方面面皆加以完备记述,都是可以选择的角度,不一而足。我的主轴是以政经文教四条主线来突显华人如何异地建家园之建国者身分的全过程。这四条主线又以社会为重,社会力是这两百年来华人之主要力量所在,为此在论述上,先行论述社会史,有别于一般以政治史为起始的处理方式。
主轴确认以后接着就是框架的设计。一部通史的论述一般上都涉及上百年或者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分期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手段。分期的作用和目的是在于更好的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尤其是每一时期,每一段落的特色。这个分期同主轴息息相关,是在主轴的关照下展现出来。这是部他乡变故乡,域外另开天的华人从蛮荒、垦荒到建国三部曲的故事。1800年是个关键节点,展现华人社会力的社团记录开始频密出现,如1799年是华人会党的最早记录,华人最早的社团在1800年成立,各种相关的组织从这里开始大量的涌现,华人社会逐渐成形于此。第二篇前两章是社会初成、社会成形,篇幅不可谓不重,展现了华人社会的迅速发展;第三篇开篇就是社会发展,也体现了华社的全方位茁壮成长,这都是在主轴关照下开展的框架。
主轴和框架确立后,接下来是如何书写,书写就会面对取舍问题,取舍涉及观点和史料两个方面。当对某一事件、人物的观点出现两个或以上的看法时,作者的取舍就视乎上述的主轴、框架、视角等因素,不一而足,如果非得以非此即彼来要求,那绝不是通史的书写。至于史料则多如浩瀚的海洋,无法照单全收,必须有所拣选,否则就是断滥朝报的流水账,这就无需赘述了。
《史记》不符合通史体例?
《太史公书》是部上下两千年的通史,列传第一篇从伯夷开始,伯夷以前的人物全部不写。第二篇是〈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和晏婴又过了数百年,期间的人物众多,直接略过,一概不写。〈伯夷列传〉区区六百余字,大多数还是太史公个人对伯夷的看法,伯夷的事迹极少。伯夷生平资料极少,传记简短,还能理解,但管仲和晏婴的资料不少,记述也同样简短,所记还不是主要的历史事迹,都是交友、老婆相处的轶事。《史记》要表达的是以礼让为国的观点,强调五伦的重要,自然在史料的使用和观点的书写就不得不有一番取舍,这种取舍无疑是在主轴、框架、视角下所作取舍而有的结果。如果以此来批判《史记》不符合通史体例,那是没有读懂《史记》而产生的看法。
著史难,读史亦难。任何体例皆有其特色和优劣,任何书写皆有作者的关怀,一篇好的评论至少在这两方面都必须有所了解,否则随意论断,这就对作者有欠公允了。
更多文章: 廖文辉.新南洋史——史话式书写的再兴 廖文辉 /《五月雪》对513事件的历史再现与文化记忆重构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