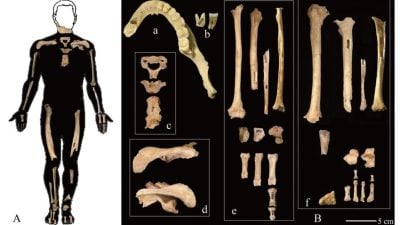理发/张温怡(沙亚南)



那是一间小而不起眼的密室。走进里头,理发阿姨用温柔和慈祥的笑迎客。听口音推断,是客家人。
村里也有这样的阿姨。白皙的肌肤、有些丰腴,穿搭V领宽裤卷发,第一句见面语给人满满的亲切感。
ADVERTISEMENT
“就等你们来这坐坐。”
好像这里好久都没人进来了。细碎的发丝落在发廊间那几张椅子。扶手留下好多未知而又神秘的线索。关于来去的人某种特有的记号。微卷的、碎片的、褐色的。长短不一。
隔壁的隔壁,还有更符合时代的发廊。这些遗留下来的头发,曾经的寄主都去哪儿?
不停思索,从阿姨的话里探出市区小镇之人的故事。他们啊,这座城市和密室都将躺在这里。有人书写他,就交给写作的人;只是他们还是都得守在这里好久好久。可能是10年、20年、30年……
没有太多选择的时代
阿姨我,在这里51年了。以前的人从来不是一出生就有的选择,狗或猫、萝卜菠菜、裁衣理发。
她的妈妈曾说,“总得去看看,学些手艺,抓住能活着的东西。”
从她话语里想像,那时还懵懂的女孩,聪明伶俐,却又因未来得及看见世界而处处活在大人的话语,左右着生长。
那年代的人,在隐形的生长痛中长出了一株成熟的枣树,一口咬下去甜甜的,小小的鸡枣味。很快很快的,刚熟的枣被摘下来煮成粥。甜甜的红枣粥,她们是这般的存在。理发,学手艺,解决当前火烧眉睫的生活。
第二代的他们,是一颗巨大空心的枣子。我看见那时候的母亲,让孩子躺在她的腿上抠耳屎。
只是一个简单却巨细的工作。
“嘿,你的发尾长了,要修剪。”
妈妈总是如此,哪儿不干净,哪儿长了,立即变换角色帮我修修补补。一会儿,她就带我来到小小的浴室。里边没有浴缸,浴室摆满盆具,水中有灰色的浮点泡沫在中央形成不规则的油垢,无以名状的细菌与汗水。盆里浸泡父亲的衣服总是灰黑色的,咸咸的海水气息。母亲耐着性子,打捞起又厚又重的衣服,放在一个干净的盆子,搁置屋后。
缓缓地,她拿起小板凳、剪具、梳子,轻声说:“来,坐着,妈给你剪发尾。”
丝丝缕缕落在石灰地板上,后来地面换成蔚蓝的硬皮手工拼图垫子,那是我上小学的事了,她还是坚持在家务劳动的席间给孩子定期理发。
平头、无规则的刺猬头、斜线刘海。
母亲剪的发,区区3种款式,撑过我小学六年级。
小的时候剪发,赤裸着身子。大时,脖子多出一条旧围裙剪下的料子。母亲对着眼前的孩子视为哺食的婴孩,折好围裙,塞进领口。发丝落在布料上她小心翼翼,用手指捡起细碎的发丝,拍拍它们,好像安抚眼前的孩子:小东西,没事的。
我记得母亲黝黑粗粝的手。闻起来,是蒜头味道、洗衣液、虾水、海水咸气。
在还没变成理发师前,她已经变换无数个角色,剔除曾是这样单纯、等待有人为她剪发、理发、绑发的自己。女孩的她,孩子时的她,长发的她,到如今老时,愈发显短稀疏的头发。
剪刀落下的瞬间,咔嚓咔嚓,孩子从她细碎的修剪声长大。
阿姨和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长得如此相像。她们是一个时代的女人,所有的光影、声音和被修剪的发根,落在小小的密室里。走在时针尖上,从未止步。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