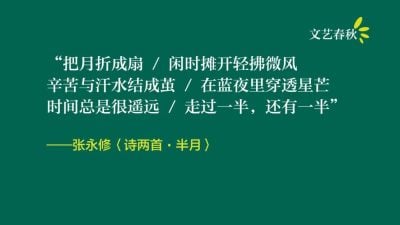林美妍/洋娃娃




再见瓦西,他躺在硬木床上,胳膊因用力过久,缝隙处已露出线头,里头的棉花因潮湿而发霉。
我劝他去缝补线头,别让情况恶化,他却说他的塑料币只能勉强买得起食物,买不起修补线头的针线。我又劝他和其他洋娃娃借塑料币买针线,他告诉我大部分娃娃都将塑料币汇去洋娃娃星了。他们的布袋空空如也,无法帮助他。
ADVERTISEMENT
提及洋娃娃星时,他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亮得惊人,令我想起了许久未见的表哥。
我很清楚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洋娃娃星的洋娃娃。有人嫌他们说话不顺,有人嫌他们抢了别人的饭碗。有人嫌洋娃娃爱惹是生非。来自不同洋娃娃星的洋娃娃自然地散落在这座城市里,散落在大街小巷中,食肆、夜市摊,公交车等城市各处,像是这座城市的居民。久而久之,你甚至会分不清,这座城市到底属于居民还是属于这些洋娃娃。
洋娃娃们肮脏、粗鲁、不守规矩似乎是居民约定俗成的暗语。他们在街角低声交换着这些词语,像在传递某种无形的信号。每当有洋娃娃经过,话题便会戛然而止,只剩下带着戒备或嫌恶的目光在空气里凝结。孩子被告诫不要靠近他们的宿舍,妇人在晾晒衣物时刻意避开那片阴影。可夜深之后,楼下仍会传来笑声,混着异国语调的旋律与笑声像另一种被拒绝承认的生命在暗处呼吸。
初见瓦西,我也未能免俗,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或许也有其他洋娃娃的陋习。当时的瓦西是我的同事,与我一同负责餐厅中端茶送水、清洁打扫等零碎的工作。他不太爱说话,眼神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别人,动作却快得惊人。送餐、收拾桌子,刷锅的动作都比我利落。
吃饭时,我们会闲聊。他告诉我,洋娃娃星萧索,街上只有几块残旧的木牌,上面写着寥寥几样工种。偶尔有一份活儿出现,便有一群人围上去。僧多粥少,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抢不上活干,只能空等,等到手里的布袋轻得似一张纸,纵使猛烈晃动都毫无声响。
每每谈及此处,瓦西总是格外开心。离开洋娃娃星后,他找到了工作,所赚的塑料币能让他一家过上好生活。
“Gaji kamu berapa?”他用蹩脚的马来语问我,我毫无防备地说了个数字,然后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出现了裂缝。我发誓我无意向他揭露数字的真相,毕竟我此前一概不知,但我的话对瓦西而言大概是个很残忍的真相,他发现了他的塑料币总是勉强买得起食物,却永远买不起一台通讯器的真相。
“你是不是和瓦西说了什么?”瓦西消失几天后,老板异常愤怒。他那双眼睛恨不得生吞活咽我这个将他的廉价劳工挤兑走的“临时工”。
为此,我付出了代价。惨遭开除的我错过了苹果的新款手机。离别前,餐厅里的其他洋娃娃偷偷告诉了我瓦西的下落。瓦西如今在工地打工,那是个只要付出足够的劳力就能换取更多塑料币的好地方。为了更多的塑料币,瓦西干活干得手脱线了。
我和瓦西陷入了无限循环,我不断劝他去缝补线头,他不断回拒:“Tak ada.”我马上拆穿他的谎言,他只是选择先将塑料币汇去了洋娃娃星。
“和老板先借下个月的塑料币,去缝补线头。”
“Tak boleh.”他又有新理由了,他说有些娃娃选择偷懒,靠小伎俩欺骗主人,换取更多塑料币,甚至曾有洋娃娃谎称家人有难预支塑料币后逃回了洋娃娃星。人们说起洋娃娃星的时候,总会摇头,觉得娃娃们都是一样的肮脏、贪婪。
沉默似突生的裂缝,将原本机械的循环生生折断。我们相顾无言,但瓦西那双黑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无法拒绝那双和表哥相似的眼睛。
最终,我带瓦西去看裂缝。每一批来到这里的洋娃娃,都必须偷偷穿过一条裂缝。穿过裂缝很危险,许多娃娃在途中丢了性命。瓦西很幸运,和其他洋娃娃成功来到这里,遇到老板,开启一路东躲西藏,赚取塑料币的生活。
裂缝处,一股带着海腥味的晚风迎面袭来,吹得头发乱七八糟地贴在我们的脸颊上。瓦西那双布满红丝的眼睛静静地望着前方。明明裂缝处只是一望无际的海水,但他那双浑浊的眼里闪着一抹柔润的光,像是从远方折返的微弱光芒。
我想,那是他的塑料币漂洋过海,变成了学费落在孩子的课桌上,又化作材料填补起家中破烂屋顶带来的光芒。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瓦西,在那之后瓦西换了工作。
没人联系得上他。
近日,又有几起洋娃娃偷窃、行骗的案件发生,居民愈发讨厌洋娃娃净干些非法的事情,将这里搞得乌烟瘴气。
我突然想起,不知道去新加坡打工的洋娃娃表哥过得怎么样,他也会如瓦西般遥望着柔佛的裂缝吗?
几年前的春节,表哥难得回来,报喜不报忧的他告诉家人他在新加坡过得很好,但他那日渐消瘦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出卖了他。他偷偷告诉我,新加坡像一具庞大的身体,所有人都在有序地输送、消化。只有他,是那块无法被吸收的组织。无论他多么努力模仿他们的语调,但洋娃娃的身分让城市将他悄悄排出体外。
表哥正学着那边的语调,将舌尖一点点磨成异乡的形状。
我希望表哥一切顺利,也由衷希望他不要学坏。我可不想因他犯了事,导致我们也被归类为洋娃娃星上粗鲁野蛮的同类。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