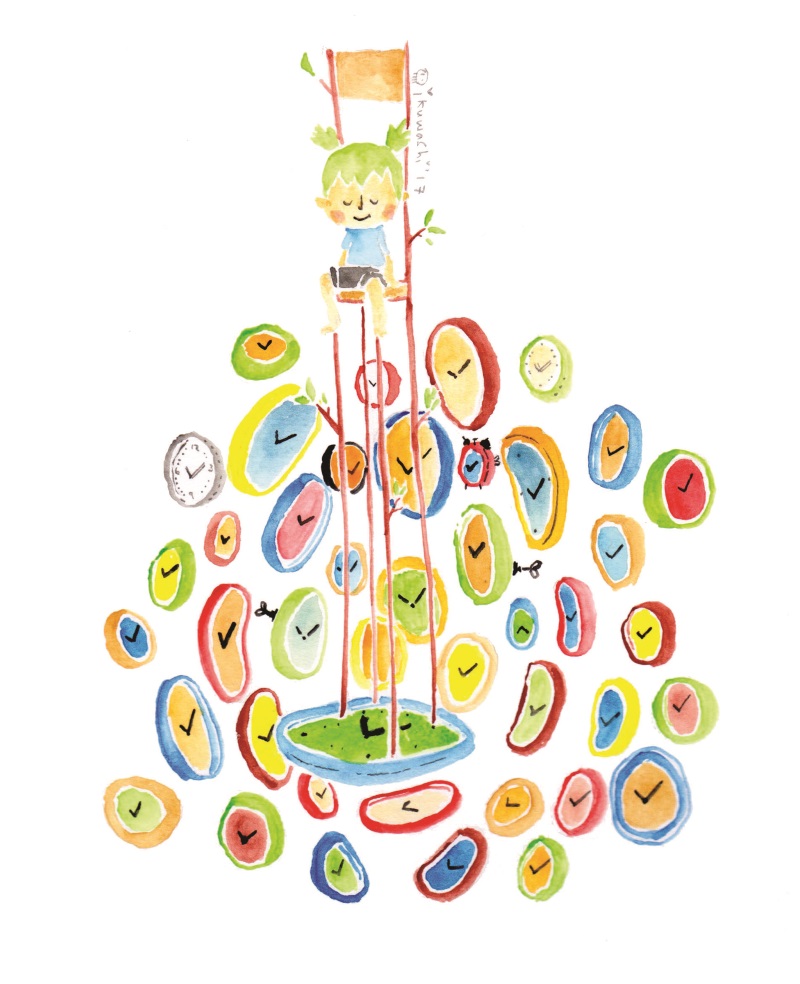
德士转到我熟悉的街道,这条路我十六岁的时候一直走。这一带是住宅区结合商圈,左手边是排屋,右手边是一整排的商店,多以婚纱店为主。我叫德士司机停在一家小旧旅馆门前,幸好它还在,我的伊莎贝拉。德士司机坚持收我整数五十令吉,我身上的现金不多,看来迟早要用到我的提款卡,到时候行踪难免曝露。但目前为止我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在伊莎贝拉二楼最左边的房间住下。打开酒店玻璃窗,可看见不远处有一座教堂,我又回到了这里。
我曾经是信主的。我的家乡偏远,家乡中学的名声不太好,所以小学毕业后爸爸帮我报读吉隆坡一所出名的女校。那时起我都在学校的宿舍寄宿。我的室友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周末我都跟着她一起上教堂,因为礼拜之后教友会很慷慨地带我们上西餐厅。用餐之前要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丰富的一餐,阿门。我第一次吃七分熟牛排才惊觉血的美味,血的咸腥和牛肉的肉汁混在一起,吞咽之后却有一种乳香。室友说耶稣用他的血为子民赎罪,我每次看到牛排的血都好像看到耶稣的血。所以我从此祷告得更勤,谢主隆恩,希望上帝每个礼拜给我牛排吃。
十六岁以后我就不上教堂了,我患上另一个信仰。上帝是唯一的绝不容许信徒花心,我只好放弃我的七分熟牛排和上帝的恩赐。
星期五放学后,我会跟室友说我回家,我也会跟父母说我赶报告不回家。我把需要应付考试、下个星期需要交上的作业、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连同几件轻便的衣服都塞进书包里。我的心情雀跃,像远行的人,我的那些书在书包中扑通扑通地跳,我又要去见我的伊莎贝拉了。
在学校前搭十二号公车,间中经过十三个站就会抵达目的地,投币八十仙。
这是一家家庭式的小型旅馆。我每次都跟旅馆老板说,二楼最左边的房间。由于未成年,我第一次来登记还跟老板说我是来读书的,打开我的书包给老板看,都是书和作业本子。他扣押我的学生证在柜台才让我住。后来大概看我没惹出什么麻烦,也没有访客,倒是没再多问。我来到房间会把所买的泡面全摆在书桌上,书和作业丢在沙发上,衣服挂到衣橱里。换上便衣,打开窗,我的日子就要开始了。
五点半,一辆国产蓝色Proton Saga驶进这个巷子,在对面一间排屋前打左边讯号,驾驶座走下一个中年男子。
我该怎么形容他呢?我觉得我没办法。我想他都是模糊一片的,很像印象派画家的画,总是在快想到他的脸的时候湖面上一阵涟漪,或风太大将他的发梢割开他的左右脸于是分裂。我就算作梦都觉得徒劳无功,从来未曾清晰过。我只能运用联想————拼凑,抓住的往往是羽毛而不是鸟,用一千片羽毛还原一只鸟身。
他是高的。他是白皙的。他的头发微卷。他的额头偏高有美人尖。他的眼角略往下垂显得有点忧郁。他的鼻梁偏左。他的嘴唇长期处于用尺画出来的一条直线。他的耳朵是招风耳。他的牙缝间有黄色痕迹,他有抽烟。他的脖子在喉结的地方有一颗黑痣。喜欢穿蓝色的衣服,阳光下的、雨天的、夜半的海洋,各种蓝。我记得他的每一个局部,梦中都会特写他的某一点,尤其手指。他有细长的手指,没有一丝皱纹或厚茧,指甲永远干净。
他第一次用他像女人的手碰我的身体,是在体育课中,他教我们如何跳高。我是因为他我才喜欢跳高的,我喜欢在他面前将杆子越设越高,我会用我的长腿跨过去,跨过去的瞬间看他一下。他有没有看见,我的长腿。美人鱼典当了她美妙的声音,不就为了一双长腿。不过他说跳高不应该是这样的,他的手在我的背上划过停在腰处,你应该在杆子前回身,像空中飞人一样跳起来往后倾,用你的腰撑着,身体直挺。
(老师,如果我一直跳错你会不会一直教我?)
我专注看他,他的黑痣动了一下。
他并不是一个大众情人型的老师,起码我没听见身边的女生谁暗恋他,她们热衷议论另一个年轻的男老师。我的体育老师对于她们来说都太老了。从他转校过来我们学校之后,我刻意加入班上热爱议论是非的团体,旁敲侧击他的消息。
我拿到他的地址,好像阿里巴巴拿到通关密码,一点一点偷渡老师的生活。
我知道老师星期五学校的课外活动结束后,五点半到家,七点半丢垃圾,九点抽烟。星期六早上七点老师会出门跑步,老师的家后面有一个公园,他都在那里一圈一圈地跑,八点之前返家。下午客厅的电视荧幕有光,老师应该在看电视。晚上七点半老师出来丢垃圾,而后抽了一根烟再进家门。星期天早上十点老师一个人出门,中午之前都还没回来,遗憾的是我需要退房了,所以只能守到这里。观察后我也发现,老师和太太鲜少同时出入,我想他们是貌合神离的。
我升上大学之前,除了期末假以外,三年内的每一个周末都在伊莎贝拉旅馆度过。我平时省吃俭用只为了付旅馆的住宿费。我在这里的日子把无数文学经典都读过了,甚至难解的数学题也可以一一破解,尤其喜欢看着入夜后教堂顶端发亮的十字架写我的少女日记。我从来不曾打扰过住在对面的老师,与我长期对望的只有那一间像盒子一样的房子,终究未把秘密打开。
那一所房子如今即躺在面前,似乎什么都没变。现在是星期日早上九点,不晓得老师会不会像以前的他在十点钟走出家门?我关窗拉上窗帘。
在Pudu街道晃荡一夜而未睡的我在伊莎贝拉旅馆睡至傍晚,起身下楼到附近商店买吃的,猝不及防在街角转身之际遇见故人。我没料到相遇这么容易。那些分裂的五官重新组织在一起,原来老师长这样。老师和父亲长得很像,父亲和男友长得很像,男友和哥哥长得很像,哥哥和老师也长得很像。他们都一样。擦身而过,我什么都没有说,好像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他在芸芸众生中走过。我没有停下来,我继续行走。
十六岁的秘密守到我的三十岁,是时候把瓶口打开,蚂蚁走出来,走在少女的皮肤之上————
女孩的手指又细又长,指甲很干净,她将食指和中指试探性地放进她的私密,用两根手指去挑动,继续钻入再深入,总是忍不住开口唤自己的名字。终于完成高潮,抽出手指竟沾着血。耶稣用他的血为子民赎罪,母亲在血中诞下孩子,女孩在血中长成女人,她可以自己完成她自己。
旅馆中留下的青春是属于那个少女的,对手是谁并不紧要。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最初或最后。
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去选一件婚纱吧,我要散开来的裙摆,转圈的时候盛放一朵花,感觉孤芳自赏,感觉很圆满。









fecddf19-ef76-4434-8507-e74d7784da4b0ccbf16e-a852-4818-8eb5-5a675835b2e5.jpg)
403a8220-f10a-4dde-a467-e4451853e7c3cd1755be-02af-4d31-ac0f-1f896a000765.jpg)
7a0947f3-cf5d-46c2-b077-0e21c7b97f162fad18c7-7a5a-40a1-975f-35c041fd0ca8.jpg)
c3c689d0-e3dd-4455-84d6-18ff96c0439f183f5f88-b397-43b1-b9bc-fed917a5b493.jpg)
692940bf-f699-4886-99a0-d51294b0c5a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