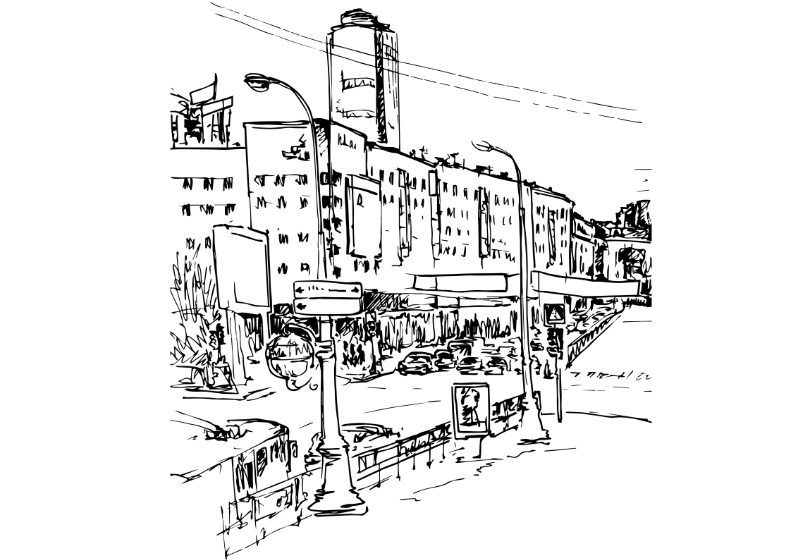
我点头,“从某一个时候开始,我封闭了自己,全心全意想要对这个世界隐藏起自己,销声匿迹,不被任何形式的任何事物发现。”
“所以,你不再对人说自己的名字?”
“嗯。每当有人问起,我只会回答自己的小名,从来不会回答完整名字,那会让我浑身不自在,仿佛一旦名字被透漏,就会把自己身上的一切————自己的性格,想法,过去————展露无遗。名字代表着我这个人,却成了把我装进一个和外部世界阻隔开来的幽暗房间沉甸甸的枷锁。甚至到后来,连别人的名字我也会避开不提。每当母亲问起朋友的名字,我总会以一句‘你不认识的,别问了’带过,似乎把别人名字说出来会让我和携带那名字的人陷入具有某种超现实性的毒性的危险之中,这让我如坐针毡。”
她沉默不语。
“名字像是脸上一块难看的胎痣,我不得不垂下头发拼命遮掩。”我顿了顿,“与此同时,我把照顾仪容这回事也抛诸脑后。我不再注意自己的样子如何变化,头发任其茂盛,长了便修剪,不涂抹任何发胶,不梳理。反正任何会让我面对镜子的事情我都断绝了。”
她依旧沉默。
“商场里看见大面玻璃,我都会加快脚步离开;买新衣时,也只是随便套上去问家人意见;拍照后也不会去看拍的效果如何。总而言之,我不曾正面看过镜子里的自己。这种情况已经大概有十年时间吧。岁月流逝,这副容貌究竟起了什么变化,作为容貌主人的我完全不加以理会。我想,容貌和我的关系,或许就像刚诞生就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吧。对它即熟悉,却也疏离。”
“刚才在洗手间里,我看向镜子,认认真真检查自己的脸孔,发现自己的容貌已经大有转变,和印象中那一张稚气脸孔有很大的出入。现在在我脸上的这副容貌想像的要老成,甚至憔悴许多。我觉得自己就像在看着一位陌生人,一位生长在自己身上,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让其他人留下和我私下里以为的完全不一样的印象的陌生人。因为当我尝试做各种表情,镜子上反映出来的,竟不是我所期待的该有的表情。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竟有那么大的差距!难怪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任何表情和动作,都得不到预期的反应,甚至会招来反效果和各种误会。这全是内心和容貌的不协调直接导致的后果,我想。我终于明白,原来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逃避自己的人,并且因此最不了解自己的人,便是自己。”
她看着我,眼睛闪闪发亮,却又透着茫然。然后,悠悠的说,“我想,我能理解了。”
“理解什么?”
“理解那天晚上,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
“当真?”
“嗯。当真。”
我看向她的眼睛,逗留一阵,然后移开视线,没任何回应。
沉默持续了好久。
最后,她打破沉默,“帮你买了稀粥,吃吧。”我点头,打开塑料袋,把里面的便当拿出。打开盒盖,一团温热气体窜出散开,弥漫眼前。她拿起大腿上的小书,翻了几页,“这本书你看过了?”
我摇头,喝一口稀粥。她把书合起,抬起,把书脊面向我,“听说过这个作者?”
我再次摇头。
“作者是城市M的人,但城市里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存在。”她又把书打开,“我在附近的图书馆找到这本小说。内容关于这座城市一个非比寻常的故事,读起来挺精彩的。”
“小说关于停电?”
“是的,关于停电,但这停电,如我所说,非比寻常。”
“怎么说?”
“小说里,这座城市M,住着幽灵。”
“幽灵?”
她点头,“平日里人们察觉不了幽灵的存在,就算察觉到,也会很轻盈忽略掉。只有当停电,他们才会出现。幽灵本身是一种空洞至极的东西,却掌握着城市M的命运脉搏。”她看向小说其中一页,“实际说来,幽灵算是具有物理意义的实体性肉体,即使很薄弱。而且也有名字,但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你可以想像得到的文字或数据记录里。即使有,也会像被施下魔法那般凭空消失殆尽。也即,有名字等同没名字。幽灵没有脸孔,没有脸色,更没有心跳,里里外外透明无比。他们是被忽略的存在,因为你可以毫无阻碍径直穿过他们像被调得很稀很稀的果冻薄片的身体而浑然不自觉。唯有城市停电,幽灵才会成为所有人都不想靠近,让人胆战心惊,主宰所有人命运的生物体。”
我停下喝稀粥的动作。
“城市M停电的频率并不一致,间隔时间可能是三个月,一年,也有可能是五到十年。一旦停电,幽灵从原来单薄的二维的,变成硕大的三维的,有血有肉的身体,在大街小巷出现。幽灵不会对市民进行攻击,或做任何的破坏。实际上他们唯一会做的,就是集体呐喊哭泣,哭得如此撕心裂肺,仿佛带着千年的怨恨,必须倾述而尽。在失去所有光线的城市里,哀嚎一处接着一处,人心惶惶,四下里奔走逃离。当城市M再次亮起灯光,幽灵消失,重新变回那被忽略的存在。另一方面,市民也会失去停电时候的记忆。
“虽然没有停电时候的记忆,但停电的后续效应,市民却感受得明明白白。停电过后,城市里会出细微的变化,如股票的跌升,家里门牌数字,物料价格,某些重要公司的策划书不自觉更动内容,以及小镇区域的划分。一开始,市民感到讶异,以为城市M受到了诅咒。后来他们渐渐习惯了,习惯了这种不由自主的改变,这种和自身无关的宿命似的改变。随着每一次的停电,城市也一点一滴起着变化,有的变化巨大无比后果严重,有的则无关痛痒,以至于无人过问。人们唯有将其视为如地震那般的大自然现象,顺应而去,不企图反抗,继续心无旁骛的过日子。
“小说里的主角却是一个例外,他有着停电时候的记忆。”
听到这里,我抬起头,看向她。
“哦?”
“嗯。”她翻去另一页,“市民们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变化束手无策,毕竟没有人理解变化如何产生。而城市M逐渐朝崩坏的方向走去,这是普遍想法。主角因为某些原因,继续保持着停电时候的记忆,如此清醒,就像声称自己带着前世记忆而来的人们,对停电时候的一切记得详细无比,所以他知道那些变化是怎么进行的。不过,主角保持沉默,没到处宣扬,静静等待下一个停电,然后主动出击,阻止那些不该有的变化的发生。”
“的确,故事挺精彩的。”我说。
“是啊。”说完,她把书合上。
“最后主角有成功阻止城市的崩坏吗?”
她笑了笑,“我还没看完呢。等我看完,再告诉你?你还是先把稀粥吃完吧。吃完了,我们就要启程回去了。你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我们该回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了。”
是的,该回去了。回去那座我们的,没有停电的城市。
2.
女孩从来没有告诉我小说结局。
我们交往了三个月,每次问她,她只是神秘笑笑,坚决不肯透漏故事结局。后来她在一场车祸丢了性命。
葬礼上,我发现连眼泪也哭不出来。大学毕业后,我离开我们的城市,回到城市M,找到工作,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了五年。下班后,我会走在街上,像品酒般品味失去女孩的城市的干涩。到过城市里所有图书馆,寻找小说的下落,皆是徒劳无功。
五年内,城市M一切运作完好,没发生什么重大事故。
但,该来的总会来,像彗星降落般无可避免。
这一天,黄昏时分,小说寓言,终于发生。
此刻,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紫红一片的晚霞天空,好几颗星星像不小心洒落的盐粒孤零零躲在一旁。我正躺在路上,泊油路尚透着夕阳照射的温热,晚风已慢慢转凉。经过的路人纷纷低头,对我评头论足。有个男人从口袋取出手机,拨通,朝着电话慌乱说了一些话。我听到警察这个词,意识忽然像万盏灯火齐亮,倏地坐起。男人见状,朝我走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摇摇头,比了个OK的手势。他依然一脸关切站在那里,不肯走开,眼睛落在我身上游移不定,仿佛电脑屏幕上不停滑动的鼠标。
我低头,发现一片黑黝黝的深红,黏糊糊的覆盖着胸口,往下一直蔓延到大腿内侧。我把手放到深红上,触手处,是一团极度浓稠的液体。凑近鼻子,嗅嗅,头昏欲涨。是血!一大片仿佛从某个栖居在地道沟渠的怪物血管爆掉流出的血!我混身发麻,胸口一阵恶心,呼吸急促,强行压抑着反胃呕吐。
远处,某个声音正述说着什么。
你要彻底清洗自己,才会得到救赎。
缓过气来,睁开眼,我挣扎着站起来,男人惊恐地向后倒退,像是看见血泊里倒地升起的恶魔那般。软疲感从身上所有角落像龙卷风般破空而来,席卷了整个身体,我才刚站起,向前踉跄几步,差些倒下去。弯着腰,双手压着大腿,我疲惫的企图回忆停电时候的细节,发现根本是徒无功。我像栓紧螺丝那般拼命往回忆挤压,始终找不到脑海里一丝和停电有关的连接点。停电这一回事就像宇宙深处某个孤独旋转的行星,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发现自己陷入一阵荒芜,比在月球上看进一台被遗弃的太空船还要荒芜。
到底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你要彻底清洗自己,才会得到救赎。
这句话一直在脑海里重复。不,不仅在脑海里,同时也回荡在宇宙厚实而弹性的墙壁间,一刻不停息。
“你还好?”
我再次比了个OK的手势,“刚才停电了不是吗?”他点头如捣蒜。
坚持住,让自己站好,左看看右望望。街上一片冷清,举目望去,街道旁立着一间开门营业的酒吧。不顾男人继续询问,我朝酒吧走去。
推开酒吧大门走进,飘过的一阵刺骨寒风,吹动了门口悬挂的风铃。咿呀,门在身后关上。酒吧里灯光幽暗,没有任何客人,没有音乐,安静得像被埋在五千尺以下的海床的维京船。柜台有一道穿着黑色夹克的身影。好庞大的身影,仿佛是缩小版的绿巨人。我刚要呼唤,身影转过身来,细看,却不是一个人。
黑色夹克里的,是一个雪人。脸上是像刚新鲜摘下的黑莓的眼睛,双手是瘦长干瘪的树枝。他正优雅地用抹布,抹着手中一只闪闪发亮的酒杯。雪人浑身上下都是软绵绵的雪,白得清澈无比,没有一丝污迹,在酒吧昏黄的环境下像砖石那般耀眼。
“喝些什么?”雪人说。声音沉稳,有腔调,像大学讲堂里打蝴蝶结一脸正经的教授。
“抱歉,目前没办法喝些什么,只想借个洗手间让我把这一身血清洗干净。”
雪人抬起头(之前他一直低头看向酒杯),眼神(即使眼睛是黑莓做成,任谁也能判断出他眼神的含义)落在我身上那一片浓稠的血红。
“这一身血恐怕你到洗手间也清洗不完吧。”
“这我当然一清二楚,但能洗多少就多少吧,那么厚重浓郁的血在身上,总是浑身不自在。”
“不,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无论你再怎么用力用水去冲刷,也洗不掉那里的一丝一毫。
普通的水龙头水对这种血是无效的哦。”
这种血?
“是的,这种血。难道你没见过这种血吗?”
我摇头。
“这血只能用一种水冲洗,就像只能对付一种特别疾病的抗生菌那般。”雪人说,把酒杯放到柜台上,再拿起另外一只。“这种水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罕有的东西。但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却相当稀奇。”
“为何?”“因为这座城市没有下雪。”
“你是说,雪水?”
“是的,唯一能够清洗这血的,便是雪水。纯正的,毫无杂质的雪水。”
我越听越觉得不可思议。雪人的存在本身已经难以理解,如今再加上一种只能用雪水才能清洗的血。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
“那我该怎么办呢?”
雪人忽然狰狞笑了起来。“你失去了记忆对吧?关于停电的记忆。”
我点头。
他把夹克脱去,放到柜台上,身上白乎乎的雪团发出一阵阵细微无比的声音。他走出柜台,站在我面前。身上,细碎的声音依然持续着,像是风拂过森林叶片轻轻颤抖的声音。然后一记当头棒喝,我明白了。
雪人正在消融!
我抬头,望去,雪人依然笑着,但这笑,已不是狰狞的笑,而是一种释然的笑。
“来,进入我吧。”雪人说,伸展双臂,敞开胸怀。
我默默点头,向前踏一步。进入雪人正消融的身体里,感觉寒冷却舒适,像夜里打开冰箱感受从里面逃窜的冷气。身上的血开始脱落,随着雪流到地上。冰冷白皓的雪,浓稠刺鼻的血,糅合参杂在一起,成了惨白的粉红色。雪像一股原始的善意,将我包围。我闭上眼睛,双手环抱自己,一切思虑停止,时间也停止,流动的只有温润羊水般的雪水。
你要彻底清洗自己,才会得到救赎。
顷刻间,雪已完全消融,留下地板上一摊看起来毫无伤害的液体,和仿佛刚从树干脱离的树枝。身上的血迹,连带那血的气味,也一起消失殆尽。睁开眼,雪人已不在,柜台上,黑色夹克像被遗忘的凭吊物。酒吧依然静默,像观看舞台默剧的观众,不作一丝打扰。我走向柜台,把黑色夹克拿起,转身,走向大门,打开,叮铃铃,悬挂的风铃再次被吹动。街道里,蝉鸣声像损坏的电子仪器四下里错乱响亮。站在门口,我昂起头,看向繁星点点,月挂如勾的夜空。
停电时候的记忆依然空白。但内心里,有一把声音告诉我,如此明确无疑的告诉我,停电之时,城市M的某个角落,像小说里寓言说的,起了什么变化。我必须把变化找出来,予以纠正,阻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既然我已经从雪人那里得到了救赎,就必须投入到战斗里去,让救赎不至于枉然。我想,就是这样没错。
我把手伸进黑色夹克的口袋,碰触到什么,取出,是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些字。细看,原来是我的名字。我像牛仔们把自己最爱的佩抢塞进口袋那般,把纸条重新折叠,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并下定决心让它陪着我走完这接下来的所有旅程。无论好坏,所有旅程。然后,转过身,我迈开脚步,在逐渐凛冽的晚风中,朝街道尽头,缓步走去。









fecddf19-ef76-4434-8507-e74d7784da4b0ccbf16e-a852-4818-8eb5-5a675835b2e5.jpg)
403a8220-f10a-4dde-a467-e4451853e7c3cd1755be-02af-4d31-ac0f-1f896a000765.jpg)
7a0947f3-cf5d-46c2-b077-0e21c7b97f162fad18c7-7a5a-40a1-975f-35c041fd0ca8.jpg)
c3c689d0-e3dd-4455-84d6-18ff96c0439f183f5f88-b397-43b1-b9bc-fed917a5b493.jpg)
692940bf-f699-4886-99a0-d51294b0c5a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