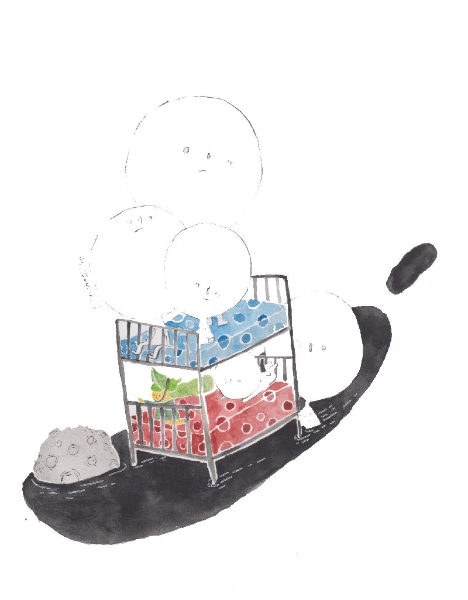
我在宿舍门外贴着一张黄色的符。因为妈妈说过到了一处陌生的居住环境,必须要贴上符以保平安。如果哪天不续住了,那张符就可以拆下了。
乌云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很快地,晾衣架上的内衣裤、其它衣物都被晾干了。我来到天台将它们回收,我的黑色短裤子和旁边的那件米色内衣纠缠住了。我小心翼翼将它们隔开。米色的内衣继续晾在晾衣架上。黑色短裤子则回到我的衣柜里安静地躺着。黑色短裤子被对折,叠得非常整齐的在衣柜里躺着。看似被保护着,没人能走近或靠近。
五人房的宿舍,最近总是特别地闷热。风扇在天花板上不停地转动,落下的却不是凉快,而是风扇三叶片上的灰尘。即使把窗全打开了,只感觉太阳的炙热。每次睡意降临,午觉要开始的时候,脖子上都会留下一大片汗。汗滴湿了枕头,枕头承载着咸咸的汗水进入梦乡,做了一个又一个的连环恶梦。记得有个晚上,坐在我对面的室友,忽然对我说道:“嘿,你知道现在是几度吗?”我停下手边的工作,摇摇头。“三十一度啊,是不是很热?最近怎么啦,真的好热啊!”她一边说话,一边把头发扎了起来。
在很早以前,我对学校宿舍非常憧憬却又非常恐惧。除了家里之外,我也曾经像候鸟迁徙一样,在几个地方逗留过。每隔一年都会转换不一样的地方,换不同的室友。待过的地方的时间都是大约半年或一年以上,每一次都是匆匆离别,谁也没有其他闲暇的时间留下什么,或被留下。这是我第一次住进大学宿舍,大学宿舍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书桌,一个双层上下铺的床,还有洗手间,还有让我们晾衣服的天台。有三扇推拉窗。推开第一扇窗,可以从宿舍里望到外面的篮球场。推开第二扇窗,微风把阳台的衣服都开始摇曳起来。推开第三扇窗,微光开始透进来。这里和我那间终日不见天日的房间有很大的不同,而我不再是一个人居住了,我是和四个人一起住。独居动物开始接近群体生活的时候,就好像怎么都不对。这房间比我的房间还要大,可是我却无法随处走动。空间过剩的我们,却始终在狭窄的裂缝里动弹不得。
上下铺的我们
从下铺往上看上铺的位置,会发现那被床褥印记的那排长方形格子。双脚总是习惯性的往上面的铁支放,与那格子越来越贴近,形成了脚板都有格子的烙印。
偶尔对面宿舍的门被打开,偶然可以看见他们是没有上下铺床的,他们把上下铺床拆开了,形成了个人的单人床。
我和我的上铺室友,上下铺的我们,却没有上下铺似的关系,形影不离。睡在下铺的我总是喜欢把脚伸长,摆放在上铺的床架上。坐在旁边的室友时不时会望向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有时候内心有个什么,好像在提醒我把这不雅的动作收回。最后双脚平躺安放在床铺上。娇小的梯子在下铺床的角落。娇小的梯子,只足以支撑室友那娇小玲珑的身子。睡在下铺的我,看不见上铺的室友,只听见上铺床发出的吱吱声。会不会有一天,这张床也无法支撑我们呢?倘若把床拆开,我们会不会都得到自由呢?脚板形成的长方形格子的烙印,在地面行走时变成了一幅两人地北天南的画。
未被隔开的书桌
在宿舍里,我们书桌的位置几乎是零距离,只要一转身就能看到彼此在做什么。我总是喜欢用堆积成山的书,放在书桌上,书有时候会挡住了坐在身旁的室友的半张脸。坐在身旁的室友毫无察觉,总是滔滔不绝地分享她的事情。在位子上的我却无所适从,不知该回应什么。有的时候是戴上耳机,那些我无法搭上的话都淹没在歌曲里。室友喜欢唱歌,总是问我她唱歌好不好听。但有的时候,我却希望在我身旁位置的空隙装上一片窗帘或一幅画,隔开我与别人的距离。室友终究无法把堆积成山的书击倒,而我继续沉浸在我设好的那副窗帘或那幅画里,无法自拔。
紧锁的浴室大门
洗手盆、厕所、浴室三个地方都被融会贯通地连串在一起。厕所的门总是要使劲全力,才能把门打开,而且还会发出有些巨大的声量。浴室的门总是关不紧,永远都透着一丝裂缝或微光,洗手盆的我们偶尔能透过微光,把所有未完整的我们都看透。但紧锁的浴室大门却巧妙地隔开了我们的距离。
洗澡时,其他三个室友都有把浴室大门关起来的习惯。紧锁的厕所和浴室的大门里偶尔会传出几句韩语歌词。有好几次,都想把门打开走进去洗手盆前清洗我的餐具,但每一次打开大门的手,都忽然畏缩了。我好像被告知浴室里有只大蟑螂,想冲进去消灭却又极度害怕,于是心里长期住了一个大蟑螂。每每都等到大门被洗好澡的室友打开,察觉浴室里空无一人的时候,我才能踏实的走进去。
室友从浴室里走出来,用毛巾把湿漉漉的头发擦干后,拿出了护发素往头发抹了一层。我依稀记得她曾问过我用什么牌子的护发素,我随便说了一个牌子。过后她又接着说,她也是第一次用护发素,不知道用着的这个牌子好不好用,她问我有什么好介绍。我耸耸肩,摇头。我拿起衣物走进浴室。挂衣钩当挂上第二件衣服时,总会一件衣服先落下。就好像我的挂钩撑起第二个人时,我们都会落下。浴室的下水道总是聚集黑发,还没人去清理。这些头发中,或许也有一些是我用了那罐护发素而掉下的头发,或许更多的是我们五个人落下的头发。是谁的头发谁也分不清。
洗完澡后,发现室友的书桌上放着一个罐子,罐子里全是一粒粒橙色的球形。
空气中弥漫着护发素的味道,我却一度闻不习惯。
我极少打扫。以前小学或中学时候,都有个值日生表,而宿舍虽然没有,可是我们都约定好每人一个月负责打扫一次。可是过了好几个月,我迟迟没有动工。看着有洁癖的室友和其他室友一起往马桶刷啊刷的,马桶抽水的声音在我耳边不断回旋,像是提醒我还有事情没完成。那天晚上,我俯在地上,捡起我位置上的头发,数不清的头发就如我无法清理的那堆垃圾一样,被摆在一旁,地上还残留着墨迹,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被语言寄托的阳台
放着晾衣架的阳台是我们聊电话的一个地标。室友的碎碎细语,像是弥补一段异地恋,在房间里的我们,仍可以听见室友语气的急促。往返房间里的室友却若无其事的继续她的游戏,我们也绝口不提。就让我们的破碎,我们的脆弱都只说给晾衣架上的衣服听,让衣服上的水分最后得以蒸发。
晚上下了很大的一场雨。衣服被淋湿了,一些不知名的昆虫也走进了房里。会飞的昆虫把陆地上的我们都吓得花容失色,大家都害怕,都不敢往昆虫的方向再走向前一步。我记得其中一只昆虫,它的翅膀少了一只,它每次都会进来我们的宿舍。我每一次都会跟它说话。最终我们随意拿了一张纸想把昆虫擒拿,却还是失败了,最终还不见它的踪影。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或许它离家出走了。
过了几天,房外发现了几只昆虫的残骸,或许其中一只是它。
清晨醒来,发现正在整理衣物的室友。
听说她要从这间房间搬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我默默地看她收拾,从书桌上的零食电脑染发剂被清理,再到衣柜里挂着的每件衣物,再到床架上每一处翻转过的痕迹,躺过的味道。她只花了大约两个小时就把一切都搬离了。诺大的行李箱却装不了我们想带走的一些熟悉的气味、熟悉的时候。又或许她根本什么也不想带走吧。
我洗好衣服后,来到天台发现晾衣架上似乎已满了,只剩下米色内衣旁边的空位。
几天前的米色内衣还在晾衣架上。
我把自己的牛仔裤和一些衣物挂在米色内衣旁边的空位,却把自己的衣物都摆放得非常靠近,反而与米色内衣隔了一段距离。一直到室友乙来到我身旁把米色内衣收走。晾在一旁的牛仔裤和那些衣物之间多了许多的空位。
可是怎么感觉有些孤独。
我看见宿舍外面的大门依旧贴着一张黄色的符,我轻轻把符拆了下来。
所有的避忌,所有的间隔都在这一瞬间消除了。而我也该搬迁了。在搬迁之前,还是先为自己准备好一张单人床,然后持续独居吧。









fecddf19-ef76-4434-8507-e74d7784da4b0ccbf16e-a852-4818-8eb5-5a675835b2e5.jpg)
403a8220-f10a-4dde-a467-e4451853e7c3cd1755be-02af-4d31-ac0f-1f896a000765.jpg)
7a0947f3-cf5d-46c2-b077-0e21c7b97f162fad18c7-7a5a-40a1-975f-35c041fd0ca8.jpg)
c3c689d0-e3dd-4455-84d6-18ff96c0439f183f5f88-b397-43b1-b9bc-fed917a5b493.jpg)
692940bf-f699-4886-99a0-d51294b0c5a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