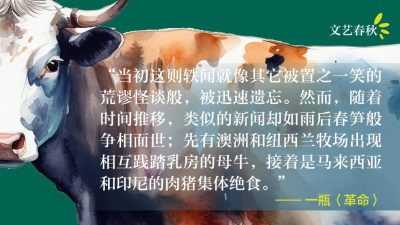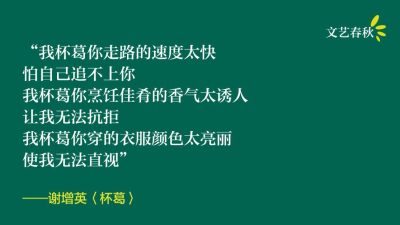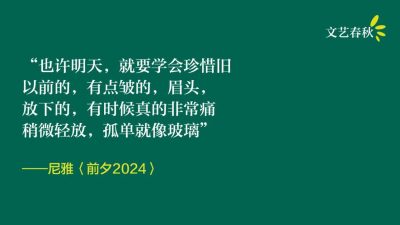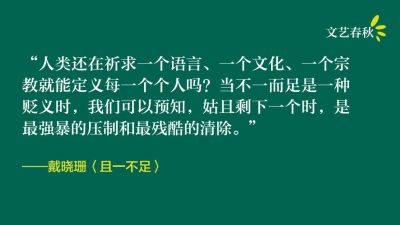星期天的阳光躲在窗帘后偷窥,不时露出一丝丝的气息供房内尚未关上的空调把玩,带着灰尘来回萦绕在睡意未醒的桌子上。数支干涸的酒瓶与深黑色空杯立在桌上的一角,等着窗帘被拉开以后的暴晒。
ADVERTISEMENT
早上八点半。手机预设的闹钟已经被关掉了好几次。我从空调喷出的冷空气中缓缓坐起,身体沉重地像被车子往反方向拖着,被床褥牢牢吸附。我打开了房内厕所的黄灯,各类洗刷用品仍旧各司其职地待在被安排好的位置,镜子前我的头发混乱得像是前卫的艺人,我举起我的右手,它还是无法转动,无法扭开那该死的水龙头。
我的手。在盥洗盆前的镜子端看,臃肿得像是个猪蹄但没有发紫。我在昨晚临睡前便已经上网搜索了一番,据说只要没有发紫便不是骨折,只是筋脉受伤,冷敷热包一段日子即可痊愈。我回到家时已经是午夜一点,没有办法不相信网络医生。
“你的手怎样了?”想是厕所的黄灯惊醒了太太,我向靠在厕所门前的她展示我那猪蹄。
她叹了一声,说:“我请半天假陪你去看医生吧。”
我轻轻地说了声好,她便挺着大肚子转身回到床上去补眠。当时的我再度把注意力投放在那无法动弹的猪蹄上,想着《变形记》里那位起床发现自己变成甲虫的主角,我则成了猪。
“这是爸爸最后一次去踢球咯,之后便好好陪你和妈妈。”前一晚出门前,我抚着太太的肚子说。
太太其实并不太喜欢我踢球,她说这项运动危险性高,现在她有了孩子,亟需要人照顾,万一我受伤了她该怎么办。
我总是笑她杞人忧天,但我深知她的担忧不无道理。我踢球的场所并非草地,而是硬邦邦的石灰地,英国留学归来的队友总和球场老板说应该学学英国,铺上软草皮,减低球员跌倒后受重伤的几率,奈何老板每次都笑说成本高,收了钱后便拿着一瓶啤酒躲进冷气房。
太太从不明白足球有何魅力,一群男人追着一粒皮球狂奔让这项运动看起来相当愚蠢,足球员各式各样的伤病新闻也促使她把足球标签为高危自残的运动。速度与激情,碰撞与火花,这是足球给我的刺激,是在现代钢骨水泥商业城市里对血液的野性呼唤。于是乎,即便下班后身体如何疲惫,我肯定不会放飞机爽约,每天都抱着当球场英雄的心态踏入体育馆。
于是乎造就了如今站在镜前的自己,肿痛的右手像周星驰在《漫画威龙》里练电角神拳时一样肥大。这也让我想起偶尔上云顶高原赌博的经历,当输剩最后一片筹码,告诉自己输完就算的那一刻,总会奇迹般的赌赢,甚至回本。然后人性的贪婪不会让你收手回家,而是想起运气终于回来,继续输下去,也输得更多。正因为我想着这是最后一次踢球,所以输掉了手腕。
早晨的医院总是显得格外冰冷,虽然等候处的人气旺盛,但都没有笑容,人群愁云惨雾般穿梭在号码的报告声里。太太始终请了半天假,陪我到医院就诊,这样的画面与我眼见所见何其相似——头发雪白的老夫老妻相互扶着或走或坐,徘徊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我的手如今无法开车,太太并没有像我想像中的大发雷霆,反倒是一直关注我的痛楚和不适。
“有没有预约的骨科医生?”医院柜台服务人员问道。
“没有,任何医生都可以。”
服务人员瞄了太太的肚子一眼,递来一张分娩传单,说:“要好好养伤,以后才能抱baby。”
我们跟随指示,照完X光片后便到专科医生候诊室等待。在那里,我看见除了自己以外各种备受折磨的肉体,原来除我以外,还有许多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因不同事故而受伤害而被带到医院。我们像一艘艘不同支流的船,导向同一个河口。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各自的桅杆和帆布破损不一,而且河水混浊且苦,没有一丝喜悦的味道。坐在这一群悲痛的肉体中,我忽然觉得自己肿胀的右手并不算什么,因为有好几个人全身上下除了一只脚,全都臃肿红痛且无法动弹,看起来就像是从鬼门关爬回来的模样。
这让我重新检视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轮到我面见医生时,我这辈子首次努力注视着X光透视片上那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右手,那些银白色的骨头与其接驳处,在我体内共存了好几十年,但这却是我们的初遇。恍如隔世,我努力从医生口中回想着与右手的前世今生,却没有丝毫头绪。
“这里。你的手腕处有明显裂痕。”
印度籍医生努力地指向手腕骨处,英文里偶尔夹杂着粤语与华语,不知是怕我听不懂还是医治华人多年学会的的技能。
“其实我看到很多裂痕。”我对医生说,他和太太同时笑了出来。
医生改用拇指和食指测量比划,尝试告诉我裂痕不长,大概只有二厘米,而且骨头没有碎裂,休息一段时日就会自动复原。
“最快两个月你的手腕骨便会自我接驳修补。”我的眼睛没有离开过那照亮着X光片的特制框架,因为我知道我将无法看见自己的手一段时日。
护士随后领我到石膏房,准备“打石膏”。我对打石膏这回事充满好奇,想着到底是怎样把混合水泥涂在手上,甚至故作轻松地和太太说笑,缓和气氛。只见护士捧来一小盆热水,同时备好剪刀、手术刀、貌似纱布的石膏卷以及一大捆棉卷。医生戴好手套进来,再次握着我的手腕扭动,确保伤势没有比想像中严重后,便以棉卷从手掌开始包到手肘,将石膏卷浸泡在热水后,赶紧沿着棉花包扎起来。不消五分钟,纱布竟然如五行山被贴上留字真言后绵密坚固了起来。
我如今才知道打石膏用的不是水泥,而是貌似纱布的石膏卷;也才开始要知道,手的缺席会让自己怀疑自己。
想是太太昨晚使用水龙头时锁得太紧,我用左手转了好几回都无法扭开。我喊了老婆几声,想是还在梦中没有听见,我逼不得已举起打了石膏的右手,想尝试用仍然突出的手指扭扭看。我还是处在认为自己伤势并没有医生口中严重的状况,他说要两个月,我偏认为两个星期应该就能拆石膏,但我立刻发现除了能把右手举起来以外,我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动作。
我硬来,一阵刺痛如雷击般忽然自手腕处传遍全身,痛叫声把太太惊醒。她跑到浴室来查看,说:“开水龙头是向右边转啊。”我像是醍醐灌顶般醒悟,同时内心一股沮丧感油然而生,原来右手不能使用时,我连扭开水龙头的方向都搞不清楚。我突然被迫从一个右撇子变成左撇子。
太太如常出门工作,留我一人在家休养,出门前还帮我穿上了吊臂带。太太离开后,我穿着内裤走到镜子前观看自己的模样,看着自己好不容易削掉的脂肪很快便会因着受伤而重新找上自己。肉身的颓坏竟然可以无来由地从看不见的死角袭来,毫无预警,且摧毁掉我这几个月来辛苦给予它的锻炼。现在并不是思考身材的时候,我尝试告诉自己,先回归到现实层面才比较实际,例如我该怎么以相对不熟练且无力的左手为自己准备午餐、洗澡等等。
我拒绝外卖,拒绝等太太回来帮忙我洗澡,但每一次的剧痛皆让我不得不让步。于是乎,我受伤在家休养的首日,被逼订麦当劳外卖当午餐。洗澡是比食物更难解决的事,皆因包着石膏的右手丝毫不得沾水,因此必须以塑料袋包裹隔水,才能进入浴室。
我拿了去年买电脑时留下的特大塑料袋,靠嘴巴和左手的笨拙配合,咬牙切齿般把石膏右手包起来。莲蓬头发射出来的水仿佛毒液,我必须在狭小的浴室空间内,模仿《骇客任务》里尼欧闪避子弹那样穿梭,只是我笨拙许多。在整整两个月的休养期里,我的浴室洗澡剂总是停在双肩,没有更进一步,活动自如的左手无法回折搓洗自己,也不能尽情地搓洗右手,两条手臂毫无反抗地被细菌霸占,那段期间我甚至觉得,马桶里的细菌也比我手臂上的可爱干净。
然而,我至少能够看见自己的左手,而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它并没有我想像般污秽,依旧是白白净净的;但我同时也成了自己身体的偷窥狂,眼睛无法控制地不断望向石膏细缝里的右手境况。那里潮湿粘稠,如史前黑洞般神秘与不可探索,只允许拿着手电筒在外照射观望,入内禁止。
太太的肚子越来越大,我的石膏无法如愿在两个月后拆除。医生告知必须多观察一个月的消息时,我恼恨自己并不天天叫外卖,反而在习惯石膏包裹的感觉后,动锅弄盘,做起一些简单的蒸食或汤食。会不会是我用石膏坚硬处支撑厨房活动,所以造成恢复放缓延迟?太太没有责怪我,但我生气自己的矛盾,我一方面不想成为废人,一方面又想着尽快复原。然而我却频频从别人的眼珠子里看出,我是个废人的倒影。只要我走到多人的地方,一定会有热心的孩子或路人前来帮我开门,好像我那健全的左手也跟着废了一样。我挤出笑容婉拒每一次自动送上的协助,那是尴尬与无奈的时刻,对方往往也会挤出同样的笑容,拒绝善意与善意被拒绝都同样难受却又无可奈何。
半个月后的复诊,我抱着忐忑的心情再次回到医院。检查后,医生笑嘻嘻地告诉我,右手可以重见天日了,嘱我到石膏房,很快护士便运来了一托子的剪刀锯子螺丝起子。医生操着他那印度腔很重的英语说:“等下会有点痒,还有就是,不要怕。”说完便一手锯子一手剪刀,锯割起石膏来。石膏上的粉末点点散开,渐渐出现一条细缝,进而蜕变成裂痕,一旦裂痕形成,医生便拾起螺丝起子,利用杠杆原理从内一撬,石膏便断成两半,我的手也掉在了大腿上。我看了右手良久,尝试提起,无力且无感,瘦得如在画册看见的非洲饥民四肢般,仿佛自己装了义肢。我明明是手腕骨裂,如今却连累整条前臂退化成一支竹签。
我没有立刻洗澡,下意识地去闻那被包整整两个半月的右前臂,竟然没有想像中的恶臭,只有淡淡的汗酸味。我不断地擦拭搓摩,原本以为可以攫获很多污垢,但也出奇地干净。尔后我步入冲凉房,按下沐浴露,事隔多日后首次清洗右前臂,这种感觉很奇妙,因为受伤期间我迫切希望可以清洗,如今却没有太多的感觉,兴许是肌肉萎缩后感官刺激也随着减退,它宛如一个外来部件。这支右前臂是我的,伤后却又变得好像不是我的。
回到日常,没有路人像之前般对我谦让或施予援手,我戴着护手时,顶多有小孩指着它说很酷,因为很像能发射砲弹的钢铁侠手套。医生要我多用右手,让细胞肌肉活化,笑着说这样以后才能抱即将出世的婴孩;我不时用康复中的右手提购物袋,如果不是我表示提不起,太太也没有意识到我的手还没完全康复。
镜子前我回想起臃肿的右手,那时无法扭开的水龙头如今是否扭得开?我举起竹签右手狠狠抓住水龙头,根本无法使力,于是我决定双手并用。自来水奔涌而出,右手腕传来一声“喀喇”,我叫了一声痛,门外的太太应该没有听见。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