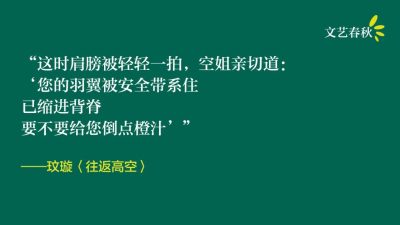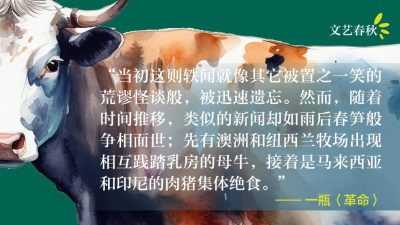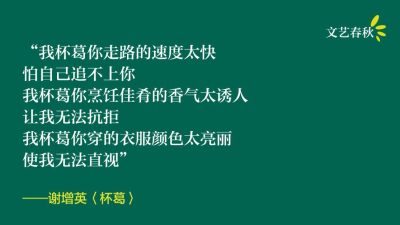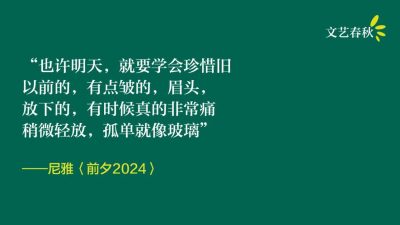天气变热的后果超乎想像,绝对不是安装冷气或减少出门就可以独善其身。那年4月,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躁,早晚犹如置身在蒸气房中,驱之不散的湿热充斥着鼻腔气管,让人坐立不安,让人缺氧。那个4月,大部分时间我伏案在空气不流通的小房间里赶论文——游客入住乔治市古迹酒店的意图。
ADVERTISEMENT
说实在,我不关心乔治市的古迹酒店,以及游客入住古迹酒店的意图。我不认为事情那么复杂,是因为口耳相传还是能力所及,是酒店位置好还是房间装饰别致,听起来左右都像在鸡蛋里挑骨头。事实是,大部分古迹酒店的客房都与普通酒店没有两样,充其量房内多一张古董椅子,价位高昂些的可能就多一架泛黄的老旧浴缸,而我居然要为此撰写一篇至少100页的文章,天花乱坠地绕一圈地球回到原点。无论如何,我的个人立场不阻碍我站在老城的街头巷尾,头顶着大太阳厚着脸皮要求游客填写问卷。没有站在街头抛头露面的日子,我窝在自己的小房间,孜孜矻矻地吞咽其他论文学说,找寻可以支撑理论的论点。这通常是一整天的事,虽然谈不上废寝忘食,但察觉时间时经常也已是半夜三更。
随着论文截稿日期逼近眉睫,呼吸困难与胃胀风的老毛病卷土重来。凌晨一点半,我站在盥洗台前刷牙,像脱水的鱼大口大口深呼吸。入夜后虽然没有白天闷热,却也不凉快,外头的树如蜡像静止,仿佛有无形的罩子罩在上空,滴水不漏。我清着舌苔,捎到敏感处胃酸伴随胃气哗啦哗啦嗝出来。夜晚的社区除了大楼对面的室内巴刹还有人在打麻将,通常非常安静,连周围流连的野狗也鲜少叫吠。
漱完口,客厅的电视画影还在流动,电视机前的妹妹已经沉入梦乡。她的身躯陷在陈年的横条藤椅上,弯成一个弧,疲惫的脸上泛着浅浅油光。午夜新闻播着卡巴星车祸片断,行动党党员神色凝重——这绝对是党以至国家沉重的损失,画面上的人物说。
我将电视关掉,转身看见妹妹额头上的汗,细而密集。她头顶上的吊扇拼了命在转,已然是速度的最大极限。将灯熄掉之前,妹妹下意识举起手,在手臂上抓了两下。长指甲与肌肤摩擦发出刷刷两声,夜里显得特别响亮,随即手臂上留下了两道浅色的红。
灯熄灭后,世界只剩黑暗。
它们畏光。
人类因为没有在黑暗中看见的能力,所以没有及早发现它们。包括心思细腻的母亲,都没发现它们留下的蛛丝马迹,那些圆圆的小黑点,完好地融入周遭背景,象是岁月在床边墙角留下的痕迹,在真身揭示之前毫不显眼。
那一阵子,岛上笼罩在一片失去的悲恸氛围中,参加追思会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各族群和各年龄层。先跨过我的尸体!卡巴星对伊刑法坚定的立场让人印象深刻,那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巨人,立成一堵高耸的坚硬的墙,将世俗国的框架稳住。许多人舍不得那敢怒敢言的真性情,在政坛上尤其难得;更多人恐惧,在没有卡巴星后,伊刑法的提案会如西伯利亚冻土底下的炭疽菌,等待时机刚好,悄然苏醒。
它的苏醒、布局与繁衍,完全在我们可能的想像范围外。当家人开始发现有异物入侵居家环境,影响日常生活时,感染程度已扩散如癌症末期,失去控制。天气的炎热让人难以忍受,蚊虫在妹妹全身上下留下张扬的咬痕,母亲则一天到晚精神不济。
“妈你是不是睡不好?”
“没有啊……”母亲伸手擦拭眼角的泪,一脸疲态,“只是眼睛不知怎的一直在流泪。”
妹妹以为自己火气大惹蚊虫叮咬,大喝罗汉果青草茶降火;母亲则认为天气热眼睛过敏,猛滴眼药水。直到一天下午,母亲罕见地大声唤我,是一种近乎毛骨悚然的求助声。
我盯着母亲床上的竹席很久。
母亲每晚都睡在竹席上,这习惯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竹席由一小块一小块3×2公分的竹板连接起来,在炎热的赤道铺在床上睡特别凉快。自从母亲睡坏了若干年前她从大陆扛回来的那张竹席后,就一直念叨着买新的。只是竹席并非必需品,镇上不容易找,好不容易找到,如获至宝。“还是最后一张”,母亲为她的战利品喜滋滋。
我蹲在床边,盯着床上的竹席。蓦地,一只黑色的只有几毫米的虫从竹块这一端爬出来,快速钻入竹块那一端。流着汗的背脊瞬间凉了,寒意延伸到耳后,冻结脑袋运转的能力。我转过头,正好对上母亲的视线,两人相觑半晌,二话不说,七手八脚将竹席卷起来,连拖带拉将竹席扛到大楼垃圾堆。丝毫不留恋。
母亲事后用消毒药水前前后后擦拭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将床被单都洗过,枕头抱枕都曝晒过。我们绝口不提虫子的事。5月下旬我提交了论文的最终版本,等待教授做最后一次反馈。长期在外的弟弟回家过生日,我们还帮他庆生。蓝卡巴星誓言捍卫他父亲的政治立场,誓死抵抗伊刑法,在补选中用狂风扫落叶的姿态大胜。妹妹身上的咬痕渐渐消退,母亲的眼泪也不流了,一切仿佛回到从前,那一个下午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
一个早上,妹妹惺忪着眼,抓着手上新鲜的五分一角大小红包,万念俱灰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它们还在。
万念俱灰。许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事人还来不及理解就成了定局,仿佛你只是个局外人,是第三者,无关紧要的群众。你以为自己生长在世俗国,突然一天她成了回教国;你以为土地上执行的是世俗法,突然一天她说要执行伊刑法。这些念头一直都在,它们只是隐藏起来,随着遏制条件松垮复活;就像它们携家带眷搬进来,大剌剌掠过我们的眼底,没有询问过我们,喧宾夺主。
怎么办?母亲问,哭丧着脸。
床虱二字刺痛我的神经,我弹跳起身上网爬文——“床虱是一种体型扁平椭圆,呈赭红色,吸人血为生的寄生虫。它们没有翅膀,既不能飞,也不能跳,通常潜伏在人们睡觉的区域附近……检查床铺或枕头,它们会留下黑色小点,那是它们的排泄物……”
母亲不停地抓头。她头皮发痒,那些小黑点嵌在她床头的地板上,嵌在墙角边,嵌入瞳孔里,我用指甲用力抠,非常难除去。那不是岁月的痕迹,是床虱走过必留下的大便,吃饱喝足的铁证。我们粗心至此。
“床虱进行创伤式受精,既雄虫不管雌虫的感受,用自己如利剑般的生殖器官强行插入雌虫身体。它们在隐蔽的场所交配,将卵产在墙壁、床板、家具等缝隙中。雌虫每个繁殖季节产卵二百多个,一年繁殖三代或三代以上。耐饥,吸血后即躲藏不出,成虫不得血食可耐饥一年以上,幼虫得不到血食可活30天以上……”我看着那些家具摆设,它们可潜藏的范围太广,我们战败的机率太大。
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该考虑搬家。
我突然发现,世界上的生命组织超乎所认知的庞大与复杂,多种生物交错生存在同一个空间,不只鸟在天空飞,不只鱼在水里游,这群生物和你占用同一个空间,比如蟑螂出没厨房的频率和你出没的次数一样多,比如白蚁吃掉了房子的骨架,比如螨虫爬满了床爬上你的脸,而你对它们的认知如此匮乏,甚至对它们的存在浑然不知。这种浑然不知,正如我就站在你面前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是现实与想像的落差,是人与人或人与事认知上的黑洞,直到东马的邻居文莱突然宣布通过伊刑法,众人才棒头大喝。
我们丢弃了床褥,多余的家具,跑遍了镇上大小超市尝试了不同的杀虫剂。我们分工合作检查房内各个肉眼所及的缝隙,出动强力手电筒照明,细针探入罅隙中钩扰一动不动的赭红色身体,它们圆滚着肚子打禅,在缺少日照的卧室建构理想的天堂。
墙上到处是它们被压扁的尸体,血却是来自于我们。血迹是一笔一笔加上去的,像血债血还的账,要一笔一笔算清。一天一天过去,每一次喷药过后,蓝色的房门被紧紧地关起来,如潘多拉的小盒子,里头发酵着另一个咬牙切齿的世界。数小时后,我们一家总动员清算业绩,每回都有来自各生命阶段的鲜活个体曝露嘴脸,象征源源不绝的生命力。它们还在,而且非常顽强。我们甚至用批土将所有缝隙填满,缝隙无处不在,石灰与木板连接的地方、裂开的墙角、落漆的墙壁,电灯罩底下、电线管背后……雪白的墙如补破衫般糊上东一块西一块的批土,却总有我们错漏或超出我们所及的地方。我们几乎疯了。
半夜热醒,客厅仍然灯火光明,藤椅空荡荡的。妹妹趴在桌上不敢睡,她被折磨得最惨,一脸的惶恐憔悴。对街麻将声依旧,除了我们一家,没有人知道那些外生物盘踞于此,每天交配产卵繁殖后代,蓄势待发毁灭人类。世界如常运转。世界如常运转?发生那么大件事,世界怎么可以如常运转!我想起《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中,最让我动容的篇幅。没有人因为你怎样了就怎样,没有谁不可以失去。除非床虱搬到你家。
人就是沧海一粟。
我看着装订好的论文,朱红色的厚皮上烫上我金色的名字,以及金色的“游客入住乔治市古迹酒店的意图”。所以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的求职面谈中,面谈的人要问同一句话——所以呢?而我支支吾吾,答不出来。
准备论文口试那几天,除虫公司的人终于出现在家门口。他们只有一个电话的距离,承认无计可施却需要极大勇气。在这之前,我以为他们的制服至少要像抓鬼团队或化学测漏员那样,戴个氧气罩或防毒面具,将鬼怪都吸到背后的钢制长筒里。尽管外形并不惹人注目,他们的到来还是引起同楼层一两户邻居的注意,毕竟我们是户挨着户地生活着。
除虫公司来了三次,前两次相隔两天,最后一次相隔一个星期。他们三人成一队,每人一桶药水,一支喷嘴,将屋子里各房间角落家具褥垫都仔细喷上一回。开始作业前,他们戴上口罩、手套和穿上白色袜子,“以防粘上,白色袜子增加看见的机会”。每次作业结束,他们将外面的衣物除下,装到大塑料袋内封死。
我对这份工作充满好奇,他们是否有洞悉另一个微观世界的能力?就像道士驱惊,问米婆附灵。你怎么不怕被感染?我问其中一人。
什么不怕!对方反射性地脱口,却一副欲言又止,“带过一次回家……家里的地上铺的是地板,它们躲在地板下,喷药根本喷不到,搞到全家活动范围就只剩各自的床。那时每张床架四个脚都浸泡在水杯里防止床虱爬上来,床架上的床垫则用塑料袋套死,不让它们爬出来。”
后来呢?我问。
“如果不是房子刚买,应该会搬家。”他大叹一口气,“后来就掀开地板啊,花了一大笔钱。”他心有余悸,捉鬼反被鬼附身,毕生难忘。
三次治疗结束后,日子算是回到了常轨上。论文口试结束后,我们替沾血的墙重新上漆。没有人建议将凹凸不平的墙磨平,大家都担心床虱冬眠式假死的本事,一不小心又复活。
天气依旧炎热,据报上说是自1975年以来最炎热的一年,单是这个月的高温就已经破了好几次历史纪录。我们尽量少出门,同时商议是不是应该装冷气了。伊斯兰党很快在国会提呈私人法案,寻求在吉兰丹州落实伊刑法,引来各路挞伐,也为后来的民联解体埋下伏笔。
周末,弟弟如往常般打电话回家。他说起新加坡的天气和大马一样糟,而且房里突然多了好多蚊子,每天醒来都发现手臂有新咬痕,全身都在痒。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