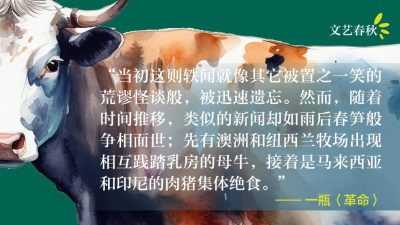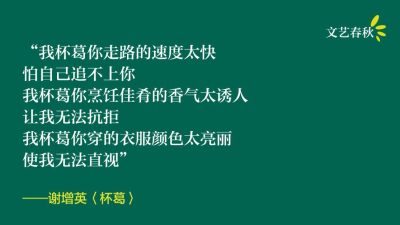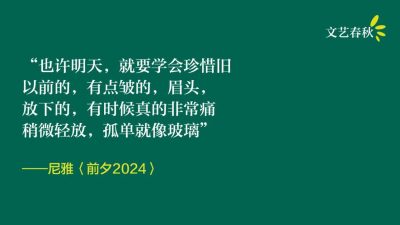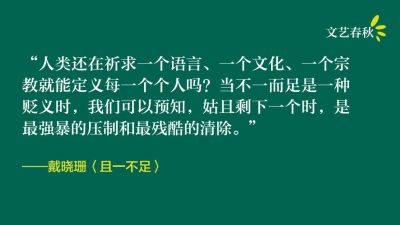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但从未想过要成为作家。由于50、60、70年代的台湾都处于克难时期,写作很辛苦,收入又不高,因此,只想大学毕业后多赚钱孝顺父母,所以我修读的都是行政管理和商业课程。
后来,我去了马来西亚定居,不久,家里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故,想工作担起奉养父母的责任;然而,台湾的文凭不受当地政府承认,于是在1986年,我去美国读研究院。那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刚发生了震撼当地政商界的“新泛电事件”,造成两国股市史无前例暂停交易三天,余波震荡,进而引发了使无数平民百姓受害的合作社风暴,最后演变成一场马来西亚华人的经济浩劫。出于激愤,促使我及时捕捉住这场重大的社会事件,以此为背景,写就《沙城》。意喻当时华人的经济堡垒其实是建立在沙滩上,根基并不稳,所以一个大浪打来就崩塌了!
ADVERTISEMENT
1987年9月,《沙城》不仅在当时销量最大的华文报章《南洋商报》连载,翌年3月,马来西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将其摄制成华巫双语的长篇连续剧热播,由我撰写的主题曲〈浮华烟云〉又获得马来西亚第一届娱协十大最佳歌词奖,因而产生了颇为轰动的社会效应,并受到马华文艺界的关注,我就这样被邀请进入了文坛。同年4月,《沙城》被马来西亚十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又因此书被带进中国,让我能独得机缘,分别受到中国暨南大学和南京大学邀请,成为中马两国还未开放民间自由往来前,第一位被政府批准进入中国访问的“文化使者”,为时一个月(自1990年4月10日至1990年5月9日)。
这趟刻骨铭心的旅程带给我的感动和感恸,又促使我写下了《戴小华中国行》。之后,通过旅游、访问、讲学、会议等不同形式,我来往世界各地,于是,又写下了一系列的游记散文:《深情看世界》《闯进灵异世界》《永结无情游》等。随后的作品以及2017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忽如归》和2019年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因为有情——戴小华散文精选集》,都是因为某个人物、某个地方或某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才让我有了创作的冲动。
所以,我创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才写,而是我的情感受到了某种强烈的撞击和敲打,让我不能不写,似乎不写出来,身心就无法得到安顿。诚如巴金所言:“我之所以写作,不是我有才情,而是我有感情。”
因而我的创作观,其实都会被所看过的书,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及政治局势所影响,这些影响也都快速地浓缩在我过去的创作实践中。
或许我创作的题材都是自己关心也是当地民众关注的事情,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在90年代初主办了几届让读者票选当地最受欢迎的十大华文作家榜,我都能高票当选。即便如此,我的内心还是有着困惑,心虚和不自信。因为我非常清楚,受欢迎未必就代表我的作品是好的,是优秀的。
我曾读过一些文学创作的论述,有人认为,虽然文学要和现实生活相结合,它必须和民众产生共鸣。但也有人认为,文学必须是纯而又纯,静而又静的,纯粹得像新鲜的空气,平静得像老子的哲学,这样的文学才是崇高的,永恒的。然而,对于此种文学境界,我虽行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虽然,我的有些作品能获得奖项;有些作品被选入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华文科教材内;有些作品被选入游记词典和选集中,然而,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还是经常有着不安和困惑。
因为,我的生命历程受到马、中、台三度情间和中华、基督教、伊斯兰、印度四种文化的影响。这些自然会显现在我的创作中。所以《忽如归》就是源于我灵魂深处的、生命本质的、思想精神的创作。我试图在创作中缝合被撕裂的家庭亲情与失去家园的疼痛记忆,以构成人的个体生命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书写。我有如剥洋葱般一层层去揭开历史真相,并在剥开的同时,也在一针针地“缝合”,来努力弭平伤口,同时,自己也在弥合伤痛的过程中得到了反思、疗效,甚至是救赎。
不过,创作过程中,身分认同及是否被认同仍然困惑着我。于是,写写停停,近十几年来,一直在搏斗着。
直到我读了邓敏灵写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以及中国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先生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我才有所顿悟,豁然开朗。
现在,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两个真实的故事。
其一:2016年在加拿大文坛引起轰动的华裔作家邓敏灵。她的著作《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一举摘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吉勒奖两大桂冠,并获同年布克奖最终提名,引起国际广泛瞩目。
邓敏灵出生在温哥华,父母是从中国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华裔。由于她特殊的身分变化,《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中主人公玛丽的思绪经常会随着母亲的故事,飘向中国和马来西亚,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苦苦寻觅着自己的归宿。
尽管中加文化的冲突令她产生身分的困惑和文化的彷徨以及文化精神的错位,但也使得她的作品体现出一种超然混杂的身分想像。《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遂成为一部超国界,属于离散写作范畴的小说。它跨越太平洋,在中国、马来西亚与加拿大的历史与现在之间穿梭,记载了一段难忘的历史,个体生命如同滚滚洪流中的浪花,随着国家命运的巨涛起伏跌宕。
邓敏灵的获奖反映了加拿大文学绚丽多彩的“马赛克”图案,形成了鲜明的无国界和超民族写作特征。它让文学单纯的只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人的命运,是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学。这也使加拿大文学成为21世纪超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文学的发源地之一。
其二:常书鸿先生在法国留学时,经常与一群年轻的艺术家探讨和争论同样的创作观问题。那时的他,非常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因此,那一段时期,他千百遍地在罗浮宫和其他美术馆巡礼,对许多西方名家的绘画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相信这些才是世界美术的正宗、人类艺术的源泉。
直到有一天,他在塞纳河畔散步,无意中在一个旧书摊发现了《敦煌石窟图录》,刹那间,他就被里面300幅敦煌壁画和雕塑的图片震撼住了!
他觉得书中那种道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完全可以和拜占庭基督教壁画相媲美。其狂野的画风,甚至比西方现代派还要奔放,而它的人物又刻划得那样生动细腻。然而,让他更为惊讶的是,这些竟都是1500年前一些不知名的民间画工所创造的作品!
同时,这次的意外发现也令他悟出人生和社会生活中所有场合都通用的重要启示。虽然我们无需受制于既有的艺术理论,却不该忽视艺术的精髓其实是升华于民众的心灵。
像敦煌的画工,他们根本不理会世俗的想法,只是用自己整个心和灵魂去创作,去表达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对生活的真实感情,因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即使经历千百年的风雨,仍然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其影响经久不衰。
过去,常书鸿一直抱持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想法;看了敦煌的壁画和雕塑之后,他被这些画工的创作态度深深感动了,他认为这群人才配称为真正的艺术家。自此之后,他不再将自己局限于固有的艺术理论里,封闭在狭窄的象牙塔内。他认为,文学艺术家的天职,应是真诚地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奉献给民众。
邓敏灵和常书鸿的亲身体悟,启发了我。自此以后,我不再患得患失。只要每个作家写他最擅长的,各展所长,读者也选择他最感兴趣的各取所需,那就会是一个非常开阔和多采多姿的文学世界。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