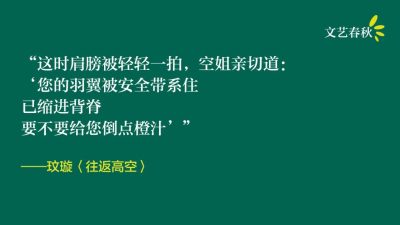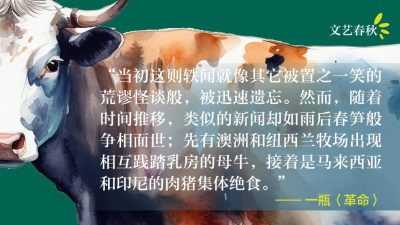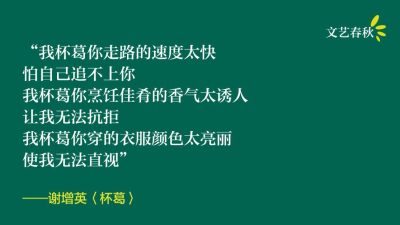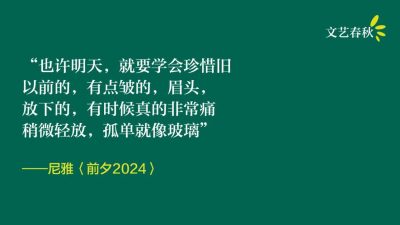那一夜,满月过后的农历十九,意姑从岛上的医院回来,在抵达家门那刻,所有人都要转身背向,目光回避。
ADVERTISEMENT
隔天,我去她的房间取照片,照片被放大洗印后将摆放在灵柩前。
在她房里的原木书架第二格,有一本已被世人遗弃的四角号码索引辞典,在辞典左侧,塞着一个红蓝边的航空信封。我打开信封,抖出几张一寸照片。有一张黑白的,短发,一片向右倾斜的厚浏海,使得左侧的头发稀疏些,露出半个兜风耳。她的脸颊两侧丰润,嘴唇轮廓分明,下颏一道浅浅的美人沟,好清秀的一张脸。她身穿中学的校服,可以清楚看到校徽和学号,是亭亭玉立的少女样,望向镜头的眼眸十分敏锐,目光如炬。
匆忙中,我仍禁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和她默然对视了一下,仿佛在怪责她遽然离世。在那一刻,想到有些话,说或不说都已枉然。
在她离世后,几次进去她的房间呆着,试图捡拾她遗留的蛛丝马迹。她的房间约莫100平方呎,在方寸之地想像海阔天高,那究竟是怎样的?也许更宽裕,也许更匮乏。
我曾紧闭着双眸,坐在她坐过的高脚凳,模拟她想像的样子,假装搜索她搜索过的版图,感觉犹若深夜的泅泳,阒黑而不着边际,后来已猜不透的她的心思,大概都潜匿在她心底那块不透光的角落,仿佛还没来得及探测海洋的深度,海洋却更深沉了。
早年,曾经有人带意姑去算过命,八字摊开来,批说她的前世是叱咤战场的将军,今世身体的残障是为前世的杀戮赎罪偿还。倘若真的有轮回因果之说,意姑会否相信她的前世是来报应今世的呢?
而事实是,她自幼患上肌肉萎缩症,右脚尤其乏力,行步时一瘸一拐的,全依赖左脚支撑。医生当年断定她活不过25岁,仿佛会推算人的命运似的。
家里有两张她专属的高脚凳,一张是沐浴时专用,要从她的房间移去浴室,沐浴完毕后搬出来晾干,再摆回房里;另一张平时摆放在祖先神台侧边的,用膳时要移过饭桌来,看电视时要移过客厅去,晚间诵经时要移过菩萨神台前。
因意姑无法如常人一般屈膝蹲下,父亲在洗手间安装扶手,还让木匠特制一个残障专用的高脚马桶。她出门需要陪伴,上下轿车需要扶持。依据神明的嘱咐,所有清明和丧礼的祭拜品都严禁食用,似乎怕引来晦气,她倒是吃了不少营养补充剂和中药补品。
兴许是父亲刻意的安排,她那些特殊的日常料理成了我过去生活的另一个重心,那时我还不到10岁。
我自幼便要学会帮她掌控炉火煎药,三碗水慢慢熬成八分碗,像提炼仙丹似的,喝了便可长生不死。煎药的过程中,隔着沾湿的手巾抓药煲的圆柄,把药倒入陶瓷碗来回一两次检查。煎好了药,轻敲她的房门,监督她坐在房里的板床上端着徐徐服下。
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仿若在静待菩萨显灵、奇迹遽现。
我常听她述说在田舍的往事。她说蓝湛的天宇很辽阔,白兔、小羊和大鱼柔软得宛如白絮又似雪。在锌板屋前、池塘边和椰树下,她贪恹地大口呼吸着自由的风,眼眸常常不由自主地觑视不远处的玩伴,羡慕他们赤脚在田里踩泥巴,那是她不被允许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领域。
也许她从未想过,这世间还有抵达不到的地方,后来的路途艰难得俨如我未曾抵达她心房一般。
几年前,曾回去田舍巡视老残板屋,昂望同一片蓝天,徘徊在她逗留过的土地上,仿佛瞥见她在田边凝神眺望的孤单身影。霍然想起多年前的那张照片,照片中那看来特别醒目的浏海。想到她那片右倾的浏海和她伫立时一贯左倾的姿势,想到两个反方向相互拉扯之间的错觉,也许让她的背脊看来挺直些。
我想,她若能在过去生命中遭遇的两极找到平衡点,双脚踮在这尖点上,平稳地坚持着,活着的意义也许就不一样了。可那跛立的姿势恍若破解不了的宿命,宛若屋边那棵歪斜摇摇欲坠的椰树,终究是要倾倒的。
直到后来,她的步履愈是蹒跚,终于要使用U字型的扶手架。她步行时夹带“哒哒哒哒”的声响,像似镣铐铁链拖行的声音,又好像谁用力敲打舌尖在申诉。有几次我在睡梦中被吵醒,在清晨万籁寂静的时刻,那缓慢的、走远又走近的声音格外响亮;双眼未曾睁开,隔着门板,便猜到她夜里睡不好又起了个早。可是那行路时有规律的节奏,仿若她的前世在军队操练中的步调,似乎太过用心,听起来总觉得有点诡异。
她的右小腿在年少时动过一次手术,也许是后来致命的痛击。那道瘦长乌黑的伤疤,像一段蜿蜒曲折的幽林小径,仿佛离不开命中注定的崎岖。
几十年旋踵即逝,那旧患伤疤开始溃烂,总是结痂不成而长期需要清洗换药。帮她清洗伤口时,熟练地用钳子夹着沾了消毒药水的纱布,先抹去残留的分泌物,换好药再重新贴上一块手板大的纱布。当纱布染成晚霞的绛红时,黑夜不动声色地靠拢,天空越来越晦暗。
由于行动的不便,意姑几乎不外出,她的生活大致上只能在那局促的房间里进行。从房间的百叶窗望出去,可以看见父亲栽种的番石榴树,番石榴树很争气,常结满果子,宛如她曾经期待收获的人生。她眼底的彷徨透露出挂念的心事,常常使我不忍直视,窗外那遥不可及的蓝天,终究存在于房间之外,那些她用尽心思豢养的宠物溜达到更遥远的云端去了。
曾几何时,白兔和小羊被野狼吞噬,天色转成死灰,沮丧一点一点咀嚼她。有一次和她在房间里对话,她说活着像在虚延岁月,她的心事俨如白昼和黑夜层层叠叠,渐渐堆叠成一座山,我已然无力攀爬。
身体残障的事实几乎把她啃噬消化,她的懦弱换来我无心的藐视,挪步离开她的房间那刻,我装着若无其事,没能把她的心事一并带走,用自以为最聪明的方式轻轻搪塞跳过,到后来目睹她重重地摔下,我惶恐而早已无从懊悔。
她房里的摆设固定,几十年来纹丝不动。出殡那天,几个亲戚在她房里翻箱倒柜地大肆搜索,我忍不住叮嘱两句,似乎试图保留什么案发现场的证据,深怕弄丢了重要的线索,模糊了日后探索的方向。尔后,他们带走几本集邮册,那是她生前最宝贝的珍藏,汇集她的修养、态度和能耐,至于那些他们带不走的,却都是我一生的搜集。
仔细回想她在世的最后几年,觉得她更祈望独处时光,独处没什么不好。那时候我已在异乡工作,逢假期回家三两天,匆忙中和她话也说不多。有一次反手叩她的房门,等了好一会儿,门终于被半拉开,露出半张脸,她不耐烦地回应着,显然心情不好,见她浮躁的空拳使力敲击左边头壳,申诉说近来头痛得厉害;我没来得及反应,门砰然又关上了。
于是在她的房间之外,在距离渐渐地拉开之后,我们都住进各自的洞窟里。
这些年,有些心底的质疑是我一直不愿触碰的。我鲜少再进入她住过的房间,一个人拖曳着记忆中的迷惘踽踽独行,似乎也走远了。她房里的摆设已被更换,记忆已不是原来的样貌;高脚凳被保留下来,摆在父亲的房间里,用来堆放旧剪报,用尘埃来上锁原封不动的记忆。
我想起那本四角号码索引辞典,想留作念想,于是跟父亲讨了回来。翻开辞典内页,页页之间隐约感受到她指缝间的温度,原来关于注音符号和四声、单字和复词的词性,早已正确明晰地编列表明,愕然想起以前,关于四角号码索引辞典的应用,她大略指导过我的,只是那时我尚年幼而未曾认真记住。
直到最近,在整理家里的旧书架时,意外翻阅她少女时的留言,写的是太白〈行路难〉中的名句。而关于破浪启航,她似乎早已准备就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反复读着,酸了鼻子,酸得心里一直颤抖。记得她离世那年,已经有50岁了,医生当年的言之凿凿,终究沦为荒谬的迷信。
原来,她一直是很努力的。
快18年了,仿佛索居幽穴多年后找到出口,我终于决心把多年来愧疚的刺痛逐一调整安顿,把过去积淀并转换成富余为我导航前进。
不久前,梦里迂回,在人潮往来的夜市遇见意姑。她拉着我频频四顾而寻寻觅觅些什么的,绕了好多圈呢。醒来,记得她方才跑得飞快的,脚竟然不瘸了。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