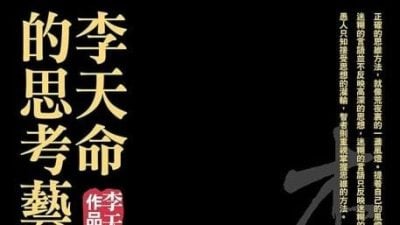【读家投稿】伍木 / 流军小说中的现实主义



流军在《跋》中沉痛地写道:“边佳兰原是鱼米之乡。战前欣欣向荣,村民安居乐业。那次逃难之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村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次的逃难是边佳兰村民心中永远的痛。屡次重读记下的文字就心情沉重,心酸泪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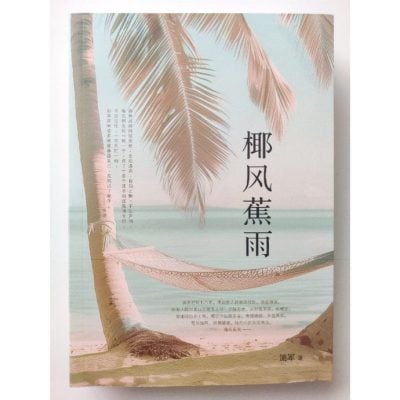
ADVERTISEMENT
1940年生于马来亚柔佛州边佳兰的新华作家流军,在1985年的《热带文艺》创刊号中有一篇《我怎样写起小说来——兼谈〈浊流〉的创作》。他在文中阐明自己的胶工出身:“我出生在马来亚南端的一个小乡村里。父母靠割胶为生,由于家穷,我九岁才上学。当时的学校是全日制的。每天早上,我都得帮母亲割胶,到十点多钟才能到学校。那时已经上了两节课。因此,我的功课往往跟不上。”
新马华人家庭的命运与橡胶树捆绑在一起的事实,跃然纸上。除了胶工外,流军还当过杂货店店员、代课老师、工场书记、船厂经理、商人,丰富的人生历练加上博闻强记和文笔流利,让他在书写小说时能够得心应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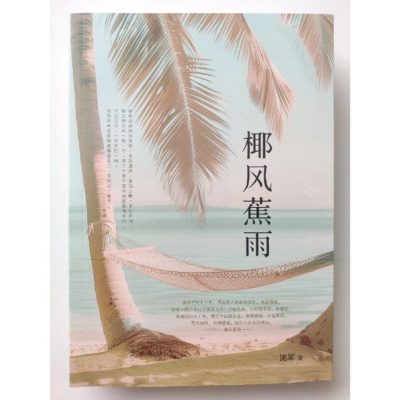
多次改写《海螺》和《丁香》
1997年8月,流军写好30万言长篇小说《海螺》,刚好这时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小说版编辑陈和锦向他邀稿,但由于《海螺》篇幅太长,在陈和锦的建议下,流军改以《海螺》女主角丁香的故事为主体,写成传记式小说《丁香》,1997年11月连载于《南洋商报》,并收录于201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丁香》。
第一稿的《海螺》在2001年完成修改工程,2002年由北京文联出版社出版。十多年后,流军应台湾秀威资讯之邀,从2018年开始为《海螺》进行瘦身手术,历两年半完成删减手术。2021年11月,繁体字版的《海螺》在台湾面世。
之后,流军对《丁香》的内容进行补充和修改,为配合英译本的篇名TropicalTale,《丁香》的标题改为《椰风蕉雨》,并以此为主题篇,收录在刚出版的小说集《椰风蕉雨》中。
这就是流军三写《海螺》与二写《丁香》(《椰风蕉雨》)的全经过。对于台湾版的《海螺》和新书中的《椰风蕉雨》,流军是比较满意的。
《椰风蕉雨》是以百年前柔佛州南部的万和镇为背景:“万和镇位于柔佛州极南端,人口两千来户,一半住在老巫河口,以捕鱼为生,其余的散居于老巫河中上游,以务农和采割甘密维持生计。此外有百多个刚过番的新客在森林里砍树开荒。他们来自中国乡下,没钱付船费被卖到卢家庄当猪崽。”
在流军的笔下,丁香是万和镇风情万种但水性扬花的女人,曾与几个男人相好。镇上的人说她克夫伤财,然而,万和镇首富卢水雄却看上了她。卢水雄纳丁香为妾后,隔年柔佛苏丹王赐予拿督头衔,苏丹后收丁香为干女儿,并把老巫河中游东岸上百依格的土地当礼物送给她。届时卢水雄40岁出头,膝下犹虚,丁香嫁给他后生了双胞胎男儿。
故事情节虚实相生是流军小说的一大特点。2024年8月,流军告诉我,小说《椰风蕉雨》中有六成的内容真实,四成虚构。女主角的原型是来自中国福建乡下的两位妙龄女郎,他把穿插发生于中国和马来亚的故事定格在柔佛州,并把丁香化身为娘惹,使其形象更为本土化。由于丁香是柔佛苏丹后的干女儿,即便卢水雄一开始就识破她红杏出墙,两个孩子不是他的后代,也只能忍气吞声。
在父权为主的百年前马来亚社会,丁香的出现,无疑是向父权挑战的一大女性形象。
小说的灵感来自破船和海螺
在新版《海螺》后记中,流军交代了他当初书写《海螺》的缘起,这篇缘起后来整理成《从饱含沧桑的破船到〈海螺〉》一文,发表在2022年12月19日《联合早报·阅读》。他在此文中说:“故乡老家前面百米外就是老巫河口。河口东边有片红树林。林里有艘破船龙骨。船壳腐朽不堪,桅杆埋在泥里,末梢露出泥面。骨架邋遢却挺拔刚劲。高约五米,长约三十米,下半部布满螺壳,上半部长满青苔。”
“为什么红树林里会有破船?”这个困扰流军许久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有一次,他路过泉州,顺便到文物展览馆参观。展馆外有一艘破船龙骨,是之前出土的郑和下西洋的大宝船。这艘破船与他故乡红树林里的破船颇为相似,流军方才意识到,故乡那艘破船可能也是郑和下西洋时因触礁沉没而被大浪冲到边佳兰老巫河口的。此时,流军萌发为故乡那艘破船写小说的念头。
“破船”这个物象不只出现在《海螺》,也出现在小说《椰风蕉雨》中。流军把幼年发现破船的经历,套用在中国南来的猪崽汪海螺的身上。汪海螺在赚够钱赎身离开卢家庄后,一天,扬帆到老巫河口游逛,穿过红树林,发现河湾里有艘大船斜躺在沙滩上。原来是艘被人遗弃的破船,汪海螺拣起卵石敲敲船身,船身坚实牢靠;爬上船舷敲敲甲板,甲板牢固平稳。他寻思拆掉桅杆,把船身扶正,钉个框架,盖上亚答,围上板墙,有门有窗,好歹是个家。几天后破船上的房子搭好了,由于破船长满螺壳,汪海螺取名为“海螺屋”。
当初《海螺》的稿件改好了,流军遇到取书名的问题。后来,他家里的几个海螺给了他灵感。他在《从》中透露,那些螺壳是他孩提时从老家门前的红树林里捡回来的。螺壳可当号角,吹起来声音很响亮,钻几个洞眼可当螺笛。螺笛声委婉动听,教人陶醉。《海螺》中也有螺笛,那是猪崽罗海彪过番时从乡下带来的,想念家人时、苦闷时、开心或愤恨时,都可吹螺笛抒情。既然螺笛声是小说的主旋律,流军便以《海螺》作为书名。
把破船改建成可遮风挡雨的海螺屋,把海螺制作成可吹奏抒发思乡之情、发送暗号、传递凄凉爱意等哀怨乐声的螺笛,这些从“破”到“立”的建构,正是流军小说中现实主义的来源和基础。
除了《海螺》外,小说《椰风蕉雨》中也有螺笛的影子,那是男主角汪海螺抒发思乡之情的工具:“离家已经八年多,想起家人就牵肠挂肚,彻夜难眠。然而人隔万重山又能怎么样?万般无奈,他只好吸旱烟,吸过烟后吹螺笛。他吸一阵吹一阵。旱烟吸出乡土味,螺笛吹出故乡音。青烟缭绕,乡音哀怨,愁丝如网,悱恻缠绵,他的心在沥沥淌血。他哭了,脸上爬满泪珠。他边哭边吹,边吹边哭。哭声抽搭,笛声哽咽。笛声飘过万和镇,镇上的人听了黯然神伤;笛声飘过森林,唤起开荒猪崽重重的乡愁。”
螺笛也是汪海螺向情人丁香发送暗号的工具,螺笛声“有时雄壮有力,卟嗡卟嗡,像凯旋的军号,穿云裂石,震得天花板簌簌作响”。苏丹后去世后,丁香的后台倒了,卢水雄对于汪、丁二人的奸情不再容忍,把丁香关在小瓦屋内。汪海螺无法继续与丁香幽会,他从远方传来的螺笛声变成传递凄凉爱意的声音:“笛声时而凄切哀怨,时而悱恻缠绵。心有灵犀,她知道汪海螺为她牵肠挂肚,魂牵梦萦。”这是丁香听到螺笛声后的心理陈述。
抗日和反殖民是新马文学创作的母题
《椰风蕉雨》书中的其他小说,例如《不归路》《魂兮归来》,与马华小说家陈政欣小说《武吉镇轶事》之《暗流涌动》和《武吉镇上36小时》等同属抗日、反殖民小说。
《逃荒——日军入侵前夕逃难实录》更像是一篇小说化的散文。流军在《跋》中沉痛地写道:“边佳兰原是鱼米之乡。战前欣欣向荣,村民安居乐业。那次逃难之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村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次的逃难是边佳兰村民心中永远的痛。屡次重读记下的文字就心情沉重,心酸泪垂。”
我联想到文莱作家刘华源的散文《和平终于来了——日军占领文莱60周年回顾》,此文是回顾文莱百姓在日本投降后,从避难区回返原乡的真实过程。无论是在日军来犯前,百姓集体逃难,还是在日本投降后,百姓集体回归,日本军国主义者带给东南亚人民的苦难都是巨大而难以想象的。
流军的《狼烟》与陈政欣小说《武吉镇轶事》之《武吉阴魅》,新华作家张曦娜的小说《边城2009》《云氏海鲜馆》等篇章,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上述篇章让我更加确信,即使那个可歌可泣的年代已远去,抗日与反殖民恒是新马华文文学创作的母题。
流军今年2月初连载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的小说《玉王传奇》,起因于十多年前他应北京作家协会之邀,到云南省采风21天,一行人在走滇缅公路时,在腾冲待了两天。腾冲是玉器中心,加工厂有好几间,玉料来自缅甸,一个玉商给他们讲述玉王的故事。刚好流军也有一位黑道朋友曾在那里走私玉,机缘巧合之下,他写成此小说。
总的来说,流军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至少有三个特点。首先,在流军的小说题材内容中,有一半是来自真实的经验或体会,另一半则是自己想象力的创造。文学的最大魅力,莫过于虚实相生的完美结合。
其次,流军人生阅历丰富,认识三教九流的人物,例如马共干部、云南省走私玉的人。单就马泰边境和平村,他便数次走访。这些广大的人脉资源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的小说书写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素材。
还有,流军的小说主要在于反映光怪陆离的人生百态,且他善于在小说中融入熟悉的物事,例如破船和海螺,这为他的小说生色不少,也提升了阅读旨趣。
相关文章: 流军/玉王传奇(上) 流军/玉王传奇(中) 流军/玉王传奇(下)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