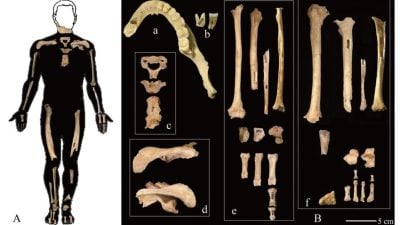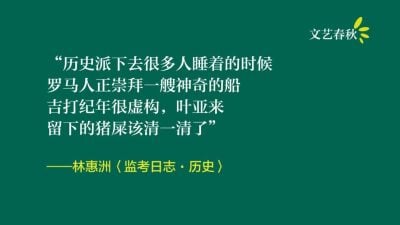陈洁颖/空巢



这一天,水清住了九十余年的屋子迎来了四五位稀客。
早晨,他比平常早一些醒来,双眼瞪着黑暗许久。待他终于下床,窗外依旧黝幽。同过去九十余年一样,洗漱完后,天就会从边缘开始点亮。他拖着瘦削的腿骨到餐桌旁,从层层叠叠的肉罐头中拔出其中一个,放到餐盘上。平日里,客厅风扇的嗡囔和电视内容就是水清一整天的同伴;每隔一段时间,喜欢向他求书的年轻人会带些漂亮包装上门,同他叹杯茶。日子也就这样草草过了。
ADVERTISEMENT
实际上他跟待会登门拜访的蓝教授并不相熟。蓝教授上学的时候,他已退位。那时他的腿脚还不需要倚靠拐杖,闲来就是等人带他走出房子那道大门。他屋子各个角落都被人头塞满,无人不尊崇他的思想,而他的退休讲师身分更是为他的名声增添不少吸引力。后来朋友几个秃了肥了驼了老了,再后来全没了。满天下的桃李也不是出国,就是有了更重要的生命议程。妻去世后,整栋房屋仿佛也一同下葬了。油漆斑驳、脱落,高耸的杂草吞噬了草地甚至水管;路过的邻居从来没见过那几扇黑漆漆的窗户打开的模样,大门外偶尔出现的三两只麻雀,在飞跃的时候才给这死寂的建筑带来一点生气。
自从近一年前走道上的书堆随微尘轰然倒塌,外籍钟点工经常有意无意指示他处理了这些满屋子都是的尘封旧物;许多时候,他直接用手指指向那些贴壁高筑直冲天花板的迷宫,告诉他,他实在收拾不了这些可能滋养着许多成年老虫的可怕温床。这些肥瘦不一的书本,只留下一行狭长的过道供人穿过。毫不夸张地说,这栋屋子是书的巨坟。诚然水清厚重眼镜背后耷拉的双目和瘦弱颤抖的臂已经很难支撑他拿起书来,可不论送卖他都觉得可惜。思来想去,他大腿一拍,想出了最好的方法:捐赠给大学图书馆。除了这里,还有什么地方更有资格收下一系列拥有作者亲签,甚至由作者本人留存的珍贵藏书?
于是他认识了蓝教授。
电视屏幕照亮客厅。他名字的发音久违地刺透空气,穿越屋内久不透气所产生的怪味,传到铁栅门这头。他初初忘了被呼唤的感受,不知道那是在召他。名字后叠着前飞来,一声比一声大,这才传到了他的耳里。他眯眼一看,外头迷迷蒙蒙站着五个人影,四女一男。
待蓝教授的学生们将带来的空箱装满,已近中午。期间,水清调小电视声音,贪婪地收听屋里的人声。水清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位置,径直拄着拐杖坐在沙发边,一边同蓝教授说话,一边掀起眼皮,透过厚重的眼镜朝这被书的迷宫包围的四人看去。他忽然想起,人在海外的孙应该同她们差不多岁数。
蓝教授的满头黑发只夹了些许白丝,不臃肿也不瘦薄如纸片。看学生们支起身,水清哎哎几声,让大家留下来一同吃饭。学生们都将视线聚焦在教授脸上。教授摆手,且扶了扶眼镜。
他们就这么走了。水清的生活也终于回到正轨。他重新调回电视的声量,瘫坐沙发上,双眼复又失焦。
水清做了一个梦。梦没有开头,画面从闯入他住所,掠取藏书的五个人开始。离开后,他们到附近的餐馆用餐。教授对桌子高谈阔论,好像桌子才是他那愿意抽空为学术圈献力的学生们。这或许是他常年在讲台前养成的一个习惯,每一句话都默认是说给所有在场的人听的,对着哪里说、对方有没有听进去,其实没差。
他说起一位不幸的大学者。他当年声望震慑四海,在时代的重压下仍不懈坚持研究的重大使命,写出一本本著作。然而千禧年伴随跨时代的革命宣言从天而降,撞出一个历史的鸿沟,并立足其上;几乎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巨物吸引目光,遗忘了巨物身后的他的年代,再来是他的著作,再来是他。不把旧事物抛下就不能前行。旧事物也识趣地走了,例如他的朋友与妻。他依旧等不来死亡的召唤,静静停留在90年如一日的住所里。
每个人的眼里只有可怜。水清别过脸,他后半生见惯这种脸色,让他生起厌恶来。他摁紧眼皮再张开,眼里只剩蓝教授一个人,瘫在无人的客厅沙发上。他解开衬衫的所有纽扣,让微微拱起的乳与腹露出,并随着呼吸上下晃动。他作为父亲的时候,经常裸着上身在家走动,瘦削的短裤,近乎全裸。最开始孩子会拉上窗帘,后来没人这么做了。衬衫之下,他藏着绵软的一层薄肉,反观水清,身上每个角落都已干瘪收缩,如同过了花期萎靡的菊。蓝教授的家具摆设与他家稍稍不同,格局窄多了,还没有楼梯通往其余层间。所有的房门都紧紧关着,看不透后面的情形;所有的灯都别开眼,昏暗一片。
梦陷入了寂静。画面停留在蓝教授与他对面电视上定格的脸。作为一个羸弱的独居老人,水清的精神本就不太好,尤其今天家里还来了不少稀客,让他废了好多力气在招呼人和思考如何招呼人上。毫无动静的蓝教授让他的眼皮开始沉闷起来。在水清差点打盹的时候,一个气泡从蓝教授耳边吹出来,把他惊醒了。透过那层透明的薄膜,水清不得不看透蓝教授,这与他非亲非故的陌生人。
困在自己世界里的蓝教授依旧解析不了妻女的背影。在一个平常天,他顶着衬衫与20片刺肉的甲,翻遍宽敞的家也找不到指甲剪,才终于明白她们早已离去,或者应该说,出走。迟来的宁静包裹了他。他屡次尝试驯服这与文学形影不离的陌生情感、摇至临终的篮。也许没办法克服孤独,正是他窝在母校执教的原因,亦或这房子其余人离开的原因。他四处拨打电话号码,毫无方向地寻找她们的去向,却又是失败。他的人生,也许只有混上讲师这件事是成功的。寂寞侵蚀了他,在内心他缩成在市场迷路的孩子哭着大喊妈妈,却不敢表现出来。总体上,社会容许任何一个年龄段的男子保持少年的态度让他们四处寻找下一个新母亲,她通常以妻子的身分出现在他身边;不过对于任何最普通的男性,这条规定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一旦不小心抖出自己对寻求母亲的渴望,就会被轻视。他人轻飘飘的眼神实在是构成不了任何杀伤力,可是几乎没有男人可以与之对抗。
柜子上的书本都早已落了灰,许久不动。他曾经依仗那些书本以逃离现实,但结婚之后,他不再需要以它们为借口了。逃避现实变成他在家中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孩子出生后——否则哪里来的钱维持所有家庭成员的吃喝玩乐?他可以在办公室待到八九点才慢悠悠地离开校园,等待桌上冷掉的饭菜和依旧一尘不染的桌椅迎接他回家。重要而有用的书,都会被挪到校内的办公室里,成为他的分身。对学术问题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就被抛在家中,自生自灭。然后不知什么时候,不知为了什么,她们一声不吭,打算永远走出他的生活。她们走的时候明明一本书都没带走,公寓房却突然无限宽大。他甚至没办法辨识她们究竟带走了什么、带走了多少。他的瞳孔聚焦在电视边框与白墙之间。那里之前填得满满当当,看不出身后的壁是什么颜色。现在物品空去,电视周围变得简洁起来,他没办法不去猜测之前放在那里的究竟是什么,却也毫无思绪。
蓝教授回到餐桌边,听学生们前俯后仰在笑,笑得东倒西歪。他不记得她们那时笑着什么,只知道一度她们说起找对象的事来。他看着与孩子相仿的面孔,脱口而出:“结婚还是好的,有个伴。”
餐桌冷了下来。没有任何眼正正对上他。蓝教授没来由地一阵心虚,仿佛学生们已看透他的内心,唾弃一介教授在人生上如何一塌糊涂。他的背轻轻弯了如变形的月。他又想起今天的林老师——水清睁大的眼皱了眉头——像蜗居在不再跳动的心脏里,空洞的心。无数房室只有层层叠叠的书籍越积越高。浮尘落到封面上,形成斑点,和墙上霉斑一模一样着。偶有陌生人闯入他的心房,在房室间跃动;稍慢的则从高高低低的泛黄书堆中认出他全名。他们带来迟到的鼓掌让他暂时回到过往,却不能复活这萎靡中的死肉。这里再也不会有鲜活与生命。他的名声随着人的出走一点一点死去。有些人说,人一生会死去两次:首先是肉体的死亡,永远闭上那双睁开了将近一世纪的眼;再来是社会上彻彻底底的死亡,被仍然记得他的人遗忘、抛弃。林老师的情况却相反。他是先死在大众心里,再等待肉体赶上死亡的进度。可惜,他的肉体蜗居在其中一个心室里,半聋的耳对其余心室传来的任何声音不闻不问,不论内容是好是坏。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他了!因此灵魂迟迟等不来肉体死亡的音讯。
水清不得不怨起蓝教授来。他没想到,这个看似受人敬仰的后生竟如此歹毒!他左右摇晃挣扎,想逃离现下,可包裹他的气泡非常牢固,没办法一戳就破。他五指并拢,拳头爬满青筋,把透明的墙顶出一个又一个突起。拳头所及之处越挪越高,水清浮了起来。在他足底,蓝教授萎缩成一个渺小的点,和每天瓷砖上来来往往的蝼蚁没什么区别。蓝教授这个时候已经低下头来,十指牢牢钳住手机。他手里骤然升起的音量就连水清都听得见,自己却闭上双眼深深呼出一口气,仿佛正坐在昏暗凉快的厅中聆听即将开场的演奏会,让跳动的音节填满自己空虚的身。水清仍在上升,连音乐都被卷走,耳边只有风声唰唰。黑暗向他袭来,待褪去后,慢慢化成轮廓模糊的巨大方形箱子,里头正发光。他眨眼,把游移的轮廓定住。
那是正在播放新闻的电视。上方,风扇和多年一样,带着一层灰尘转规律的圈,嗡嗡声替钟报时。
摆脱这白日噩梦后,还没吃上午餐前,水清已经把梦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毕竟谁会记住每天零碎又荒谬离奇的梦?水清继续回到一模一样的每天:起床——吃饭——看电视——和人谈话(如有)——吃饭——看电视——吃饭——入睡。蓝教授曾为了搬运书本再上门几次,学生们的脸大都并不固定。不过那仅仅是他九十余年人生中的小小插曲,连内心的涟漪都掀不起。至于他近期是否终于死了好与他的辉煌时代会合并给这篇文落下一个好句点,我仍未打听到。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