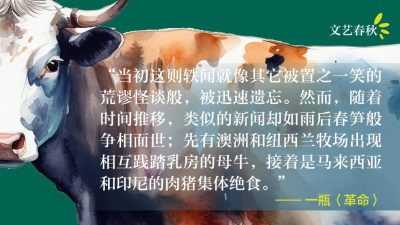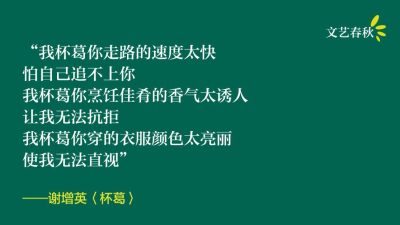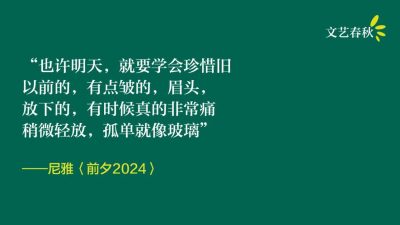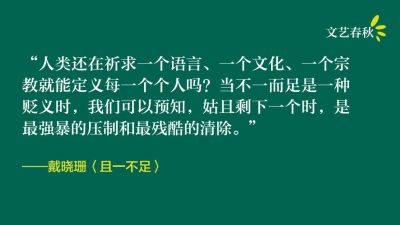渐渐地,阿胖的那段旧事成了大家再不愿触及的,好不容易结痂的疮疤。以后,就算彼此对谈,也只能绕着那一圈隐匿不见的孤岛驰走。至于,阿胖霸据,踏足,穿梭,轻蹭过的那些,属于它的舞台,都像是彼此结了未名的暗契,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隐入花丛草木间,它们自然融成,不露痕迹,仿佛那些曾经附着其上的,阿胖的气息,都只是一场幻觉大梦。变成一种,属于我们的自以为是。
其实,那会不会只是,阿胖给我们这群痴顽之人开了一个天知道有多大的玩笑,收回曾施予我们的一切,以惩罚我们不意间碰触的,未察的,什么?
ADVERTISEMENT
关于阿胖还在的那段日子。在我那飘忽、断续、甚至扭曲跳接的记忆中,阿胖应该早在我未搬来之前,就已在此生活了很长的时间。说不上有多少年,据阿胖的“管家”——2楼先生(我们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姑且称之)摊开那缓慢得像陈年大肠的回忆,阿胖应是9年前来到我们这座楼层。刚来的时候,阿胖的白腹仍然紧实有致,“吊肚”,你知道吧?2楼先生就此打住,他相信这种低频的古老词汇是会不慎打断这场对话节奏的。嗯,我知道,就是没有小腹的意思对吧?我无法想像“吊肚”的阿胖。
在脑中,我将初见阿胖的身影抽出来,一帧颜色依旧鲜明的相片,白腹。嗯,4年前的阿胖,身形似乎瘦些,小腹却已微微鼓胀;我动用了一些臆想的修图工具,刷了刷阿胖的白腹,那局部像泄气的气囊,逐渐缩小,待到一个满意的弧度,才挪开笔刷。想像中9年前的阿胖,是那样的——紧实的白腹,毛色鲜亮的橘背,稳实却举重若轻的四肢,虎头虎脑,还有那睥睨一切的倨傲。“阿胖!看过来!”“咔擦!”橘背白腹迅速流光,像走急的旋转寿司阵中,一道透明澄亮的生鱼寿司。2楼先生出示真正的4R相片,画面中的阿胖(不,不应该称作阿“胖”),身影矫捷,是相机无法捕捉的极速,遂成了一抹亮澄的流动,但依然像寿司。不知怎么的,无论是我初见的阿胖,最后一眼的阿胖,甚至相片中9年前初来乍到的阿胖,都令我想起与食欲有关的一切。
阿胖明明吃不了多少。
那时,阿胖身前总有一个小瓦钵,里头是七分满的猫粮,另外三分已经稳妥地在彼时已初具规模的小腹中,酝酿,与等待出路了吧。像人一样,过于干涩的饭,总是难以下咽,必需浇上一些菜汁,才吃得粒粒皆香。大概也是这个原因,那七分未入口的猫粮,才因此静置许久。阿胖并不着急,它审视来人,时而瞇眼吐纳,时而霍霍扫视。直到我母将盛满水的碟子,轻轻地放在小瓦钵旁,阿胖才弓起身子,慵懒地低头舔一舔碟子里的水。阿胖舔水的动作总是那么优雅,前胸那一片V字的白,像是有教养的小孩在进餐时系的白色方巾。后来,阿胖不愿舔碟子里的水,转而待我母每回在水喉底下洗手的时候,跳上台边,伸缩它那像乌鱼子的舌头,舔弄盛水的掌心。阿胖是喜欢混有手汗的咸涩的水,还是作为一种宣示主从的秘仪,就不得而知了。
阿胖的“玩伴”可不止我们一家,除了2楼先生是其最大的“管家”(提供温暖的榻居、脆口的猫粮还有那足可誉为动物界亚曼尼的高价项圈),在这寓所中,近乎大半的女性都愿为阿胖巧言令色。像4楼那高挑瘦削的印度太太,18楼那昼伏夜出的值班护士还有那班散居各楼层狂暴的屁孩;他们面对阿胖,就像是捧在手心上一颗不欲人见的宝石,对其呢喃低语,极尽谄媚地讨好。多数时候,阿胖总是抖擞银白的猫须,轻掀那沉重眉睑(阿胖毕竟年纪不小了),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这时候,女人与小孩们就像是受到电击一般,逗弄的声音逐渐拔尖,开始摩挲阿胖圆滚滚的头,力道大了,阿胖就会别过头。目光及处,是一群鸽子,它们迟钝而笨重,伸头缩脑地啄食;那一瞬间,阿胖眼中闪过一丝迟疑,继而回头,迎面向那些摄像头亮光,有些沉敛地定住,像是刚盘算好一桩物事,就再也不计较地笑对镜头,还有这些扰人如搓手苍蝇般的绮语。
关于阿胖还在的那段日子。曾经的那一个夜里,阿胖无预警地闯入家中,我忘了阿胖好几次也干过这般明目张胆的事,几乎所有与它有关系的人家,都曾遭阿胖造访。这次轮到我家,阿胖迈着像虎的步伐,从我趋前抱住的手中硬生生钻过,迅速地进行它风一般的巡礼。怔住的我,看着阿胖像阅兵的司令,一间间地驻足、迟疑、前进,所有过程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就在它准备跳上我床榻的那一瞬,终于被我大力地扯了下来。我想,应该从没有人如此对待阿胖。阿胖愣怔,继而反抗抓狂,四肢实实地抓住地面,奈何那是刚抹过的瓷砖地,阿胖只能不住地被我抱走。抱在手中的阿胖,小腹像一团巨大的麻糬,四肢绷紧,急欲表达它的愤怒。阿胖被我放在门外,一瞬间,它似乎又想返身闯入,我便放低语气,“不可以这样哦,阿胖。”稠腻却不给余地的劝降。
没等阿胖反应,我就关上厚重的木门。门后只传来阿胖爪子刮在木头上的声音,还有几声甜腻的软语。那时的我,突然觉得阿胖像是突然转性,变得如此黏人。像是,较之我们对它的喜欢,更为浓烈的求爱。
不得其门而入的阿胖,后来足足与我家冷战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明着有两家人叫唤它,它却死也不愿走向我这边。后来,是在另一个雨夜里,看见阿胖不动地栖坐在楼座大厅的云石椅下。阿胖是在演哪一出戏?我疑惑。阿胖平时不老是攀上攀下,还可以搭升降梯,到处去串门子么?我缓缓走向石雕阿胖,蹲在它的身旁,遵循社交辞令注明的:“谈判时,尽量与对方平行对话,过高的俯视是种藐视,将会严重动摇对方的心理,进而影响谈判结果。”“喂,阿胖”我小心翼翼地开了口,阿胖依然不动。“阿胖喂,还好么?”我换了一种像那些女人小孩般的,更为浓稠,还夹带着稚气的声调,刻意延缓字与字之间的距离。这时候,阿胖突然眨了一下眼睛,银白的猫须动了动,打呵欠般的嘴型中,涌出一种之前未曾听过的,更为低沉的“喵呜”。像是一种“有事么?”老爷爷般乖张的语调,我仍不敢伸手抚摸它,又开始转成正常的语调,“那你算原谅我了哦?”阿胖无语,只别过头,看着顺屋簷掉落的水珠碎成花。
作为人的独断与蛮横,我那时就认为,这算是与阿胖言归于好了。就是,从那之后的几天,阿胖失踪了,不来大厅晃荡,不去花圃逗弄禽类,也不会突然出现在升降梯的角落,视若无人地走出。这一切,像是被切断的电流,那之前的一切变得无法驳接。我甚至怀疑那一雨夜的真实,阿胖是否真的出现在大厅,是否真的回应过我。楼座里那几个固定的,阿胖的“玩伴”开始焦急地寻找,我们先是在楼层罅隙里,电机房、储藏室,还有那最可能也最令人不敢去搜寻的垃圾场。
没有。什么都没有。
阿胖的“玩伴”们和我,开始推理起阿胖的踪迹。有人认为阿胖不会走出我们这座楼座,“我从未见它走出我们这栋楼座,你们看见么?那里的石墩,最远的一次,阿胖到了那里,就调头回来了。”那时,2楼先生正拖着沉重僵硬的身躯,走向大厅。“问过了那边的管理处,都说没看见。”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对着我们。2楼先生虽说是阿胖的“管家”,却从不认为阿胖是它的私有物,他总是说:“阿胖怕寂寞,你们能多陪它真是太好了。”想无可想,谁都想不到,一个怕寂寞的阿胖会突然消失不见。“出走?它都已经住在这里这么多年了。”忘了是谁,嘟哝了这么一句。
关于阿胖消失后的那段日子。升降梯边的寻物启示开始剥落,见到剥下的一角,就会用力地推平它。“MISSING”——正在进行式,我想像,阿胖是否真的正在消失?像黑洞中间,那纺锤状的细管,阿胖是不是正在里边,顺流逆流?我不敢想像,怕寂寞的阿胖长劫轮转的身影。于是,我愿是那,忘了是谁说的,“出走”。“RUNAWAY”,不是更潇洒些,任性些,更符合阿胖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么?尽管它总是抵挡不了人们的软言相诱。也许阿胖就像孟若笔下的那些女人,突尔在生命的某一道光景中,照见了另一个不曾见过的自己。然后发觉之前那些安逸稳妥的一切,却是会让体内的一些什么,渐渐调萎,先是最外的那层,侵入愈深,就得掐住最里内的,窝于心房之后的那点,多年来一直守护的什么?什么?就这样被濡湿、浇熄。
最近,阿胖的“玩伴”们又开始怀疑起,那些最近大量侵入社区的外劳,他们说外劳嗜吃猫肉,阿胖没准已成为他们腹中的养分。这时候,我发现原本对阿胖纯粹的念想,逐渐质变为攻讦的器具,仿佛要将那些柔软的触角,变为一双双利刃,随时面敌。既慈悲又残忍啊。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