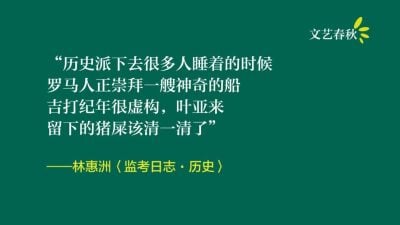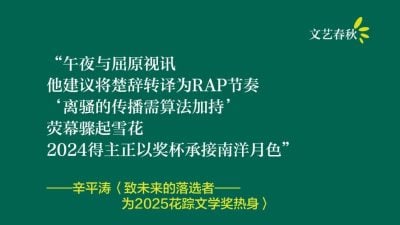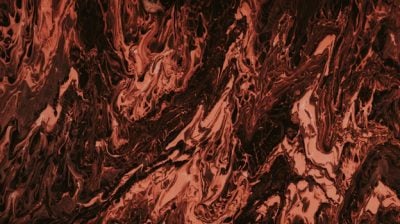方肯/装死的人不穿鞋(上)




ADVERTISEMENT
我的邻居黑先生已有一周没有出现。黑先生是一名律师,他的眼皮总是半关,每天早晨就顶着凌乱的头发在阳台晒衣。衣服比较喜欢待在阳台,可以吹风,可以见见日光,还可以看着白云做白日梦。衣服摆脱了人腐朽的味道,找回清爽。
这个国的人都已经死去。他们一醒来就死去,一睡着就活过来。如果醒时发现自己活着,他们就把自己杀掉。
这个国的一切都在腐坏。云是黑色,雨是灰色,人的身体里坏成一团,一张嘴就是恶臭,字迹如爪痕划进心脏,多看一眼都会痛。
我从自己的阳台爬到黑先生的阳台。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常这样偷溜到他家里去,看他的电视,躺他的沙发,到他的书房,翻看他索然无味的文件和笔记,没有一丝温度。但是律师的书房散发着一种魅力,我总相信里面藏着令人讶异的秘密。他海蓝色的办公椅很欢迎我,泡绵椅垫和我相处融洽。虽然桌上层层叠叠的文件夹催促我出去,但我可以对它们视而不见,反正我从不懂它们。
我对他的书房仍抱有期待,希望总有一天可以看到黑先生柔软的踪迹,纵然他每个醒来的脚印都已经死去。
我拉开阳台的玻璃门,进入客厅,那屋里已失去他的味道。客厅和饭厅比平日整洁,杂志、报纸都不在沙发上蹓跶。杯子靠着杯子,筷子和汤匙划清界线,地板上有我完整的影子。
在不开灯的屋里,我依然能轻快地走到他的书房。没有什么能阻碍我,可越是靠近,一股刺鼻的味道越是强烈。我一打开书房的门,味道猛然从房里逃出来,撞上我的嘴巴和鼻子,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窗敞开,窗边的窗帘望着月光,随风飘动。月光站在书桌上,纸张都在发亮。
那书桌旁的大水桶是如何进来的呢?里头灌满水泥,臃肿得动不了。它见到我时有点不知所措,想躲起来却找不到地方可钻。它只能杵在原地和我对望。
桌上曾敌视我的文件夹都不在了,书架上多了几个空格。我没有时间和我友好的办公椅寒暄,便走到屋里各处寻找黑先生,包括他的房间。他的屋子前所未有的空洞,好像他不曾住在这里。
我把我在门上的指纹都擦掉,然后从阳台爬回自己的阳台。
打电话报警,报的是气味,和人无关。死去的人不对异状有所反应。我是装死的人,语气也像死了那样僵硬,低温。
几分钟后,警察来到黑先生的家。他们撬开门后,在门口拉开了红白胶带。有人拍照,有人检查屋中每个没离开的东西。他们盘问了我,我说是我报警,什么也不知道。我不能说我知道,死去的人什么都不会知道,也不可以知道。
屋里的壁虎和蚂蚁却一定知道。那壁虎一家也常在黑先生不在家时,大肆乱窜,它们不破坏任何东西,只在墙角、桌底、洗槽边留下粪便,炫耀自己的版图。蚂蚁偶尔找到黑先生掉落的食物碎粒,就领着整个家族的小兵把食物搬走。我常看到那弯弯曲曲的蚂蚁队伍,真想捻断这条蚂蚁项链,但我牢记着死去的人不留下痕迹,不许破坏这屋里的任何东西。
警察没有发现壁虎和蚂蚁,否则它们能提供有用的线索。
臃肿的水桶在房里呼唤警察,警察已准备好搬运器具,他们像约定好的朋友,一见面就结伴走了。我以为先认识水桶的是我。
第二天早上,住在对面的邻居说警察找到黑先生了。他在水桶里。
黑先生给自己灌了水泥。警察说。
我们回到自己的屋里,半天没有出来。谁都知道黑先生是发现了自己还活着,把自己杀了。
丧礼在当天晚上。调查顺利完结,没有疑点。我和几个邻居去治丧处,但丧礼上没有黑先生,只有黑先生在一张照片里微笑,从远方回来的妹妹,以及两排哀伤的白菊花。人和花一样沉默。
黑先生的妹妹眼睛里有一点泪。那是死去的人短暂活着的迹象。她看着我,我看着她。黑先生的客厅有一张合照,黑先生和妹妹站在山上拍照,风抚开他们额间的发,也拨开他们咧嘴大笑的嘴。我不知道让他们笑的是风,还是互相揽着肩头的手,但两人笑瞇的双眼很一致。那时候他们必然是活着,那种笑容只有活人才会有。
我看她看得很心虚,她好像认得我,她是否在照片里曾看见我凝视她?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我太渴望见到活人的样子,提醒我:我还活着。
“黑先生”入土后,我周身不舒服,我已不能再到他的家,拜访我熟悉的电视、沙发,还有那张海蓝色的办公椅。它们为黑先生服丧中,心情大概不好,谁也不想被打扰,只想任尘埃层层将自己覆盖,直到下一个住户把它们抛弃。
第四天,我家的门铃响了几声。它忘了自己还有声音,自己把自己吓醒。我以为是警察,或许有了新线索,或想起遗漏的问题。
我打开门,见黑先生的妹妹身着一身白色风衣,化成一只风尘仆仆的天鹅站在我的门口。她已退去丧礼上的黑色套装,和头上那个灰色束带扎的小发髻。
她背着像白色羽翼的背包,走进我的屋里,观察了环境,问我能不能让她进来。我竟然不敢拒绝她,那都是黑先生的关系。
她用了客房的浴室,洗了澡,然后向我要吹风机。吹风机见着她,很卖力地呼出热空气。她的眼睛也是半关,和黑先生一样,常挂着通宵未眠的疲累。
失去亲人之后,身体里的精神凋零,飘在空中游荡,不会落地。有些人飘很久,有些人很快坠落,被泥土吃进去,一段时日后再长出新芽。黑先生的妹妹很轻,在我面前飘来飘去。她观赏了我的桌椅、花瓶、吊灯,最后安坐在我墨绿色的沙发上。确定她不再移动后,我才坐在她旁边的椅子。
我望着她,想不到要说什么。她弯下身,从我的沙发下拿出一双鞋。
我直盯着那双白色的布鞋,如远航而来终于靠岸的白船,我深怕它随时漂走,眼珠在惊恐中僵滞。
我掀开掩盖沙发底部的布,难以计算的各色布鞋塞满了我的沙发底下。
我从不知道它们躲在我的沙发底下。
既然我能爬到黑先生的屋里,别人也能爬进我的屋里。
黑先生的家里没有秘密,书房里也没有秘密,秘密都住在我的沙发底下。
鞋是邪恶。从我们出生以来,这个国就告诉我们:鞋是邪恶。
“赤脚不能抵达的地方,就是不该去的地方。”
“这个国已铺上安全而舒适的道路,因此鞋子是多余的物品。”
“人之所以陷入错误,是因为走得太远。”
为了不犯错,人们不穿鞋。没有人想承担犯错的后果。秩序若是被扰乱,谁也活不成。
我曾有那么一次割破脚底,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那天,我看见云化成鹰,先是在我的屋顶上盘旋,然后忽高忽低地飞,邀请我跟随它而去。
我从屋里奔跑出来,仰着头,朝鹰急速飞去的方向追去。我只注意着那鹰,忽略地面,毫无自觉跑了多远,或是跑了多久。直到我感觉脚板疼痛,才看见双脚沾满了血。
双脚正站在遍布尖石的地上。大树浮出苍老而粗壮的根。在阴湿的丛林里,腐坏的血腥味正肆意闯进我的鼻腔里。我听到味道在狂笑,并且舔舐我脚下的血。
我那时多想穿上鞋子,离开那个地方,继续寻找令我着迷的鹰。
当我走到医院的时候,我的双脚已停止流血,地上没有我的血迹。
没有人知道我曾到过什么地方,但我被割破的双脚是犯错的证据。
人们一直问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见过谁,我照实回答我去追了一只云化成的鹰。
没有人相信我。
我被留在在医院里几个星期,脚下的伤口早已完全愈合。为了脱离困局,我只能以谎言来证明我的诚实。
我说我梦游了,梦见云化成的鹰,遇见遍布星星的丛林,屈腿的大树,以及闻到四周弥漫花蜜的香气。
他们信了,就让我走。
自那天起,我知道我不能醒来。
黑先生无论醒来或睡着都感受到自己的呼吸,那活着的血液在体内激烈地流淌,可以听到浓稠的愤怒在沸腾,也可以听到哀伤敲在心脏的撞击声。我和黑先生都是装死的人。
我继续装死,黑先生却要让所有人知道他活着,并且呼唤所有死去的人活过来。
死去的人死去太久,已遗忘死去的原因,以及惧怕活着的原因。人们不能追问原因,知道太多的人会把自己杀掉。
“把鞋子送给所有人,只要他们可以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们就会活过来。”
黑先生的妹妹将布鞋塞进她的白色背包,直到不能再塞入任何一双鞋为止,但那些布鞋只是我沙发底下的一小部分而已。
黑先生的妹妹背起她的背包,自己打开我家的门,像展开了白色的翅膀,扑棱扑棱飞走了。
第十四天,黑先生妹妹赤裸的身体在海上浮起。她把自己杀了,报章如是报导。
一个正试图唤醒全世界的人,把自己杀了。
我望着她曾坐在客厅吹头发的一角,像只天鹅整理自己的羽毛,退去了灰与尘,洗发水的味道随着吹风机向周遭四散。
如今,她不带走一根羽毛,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从沙发底下拿出一双适合我的布鞋,是黎明初醒的灰蓝色。我把布鞋套在我的双脚上。那是我第一次穿上鞋子。
我在客厅穿着鞋子走路。脚底和地板隔着一层薄垫,发出暧昧的细语声。它们初次相遇,对谈如此投机,像久别重逢的老友。我聆听着它们,在客厅来回踱步,直到夜晚降临,直到客厅的暗让我看不见自己的双脚。
这么一走,我不想只在客厅里走了。(待续)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