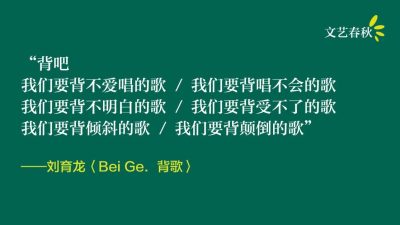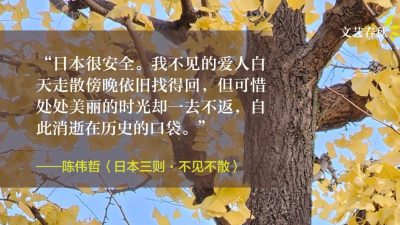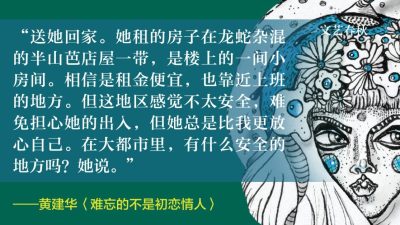我知道我是谁,但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叶国辉的房间已经待了一个晚上。我很饿,肠胃被空气填满,饥饿的虫子在里面狂叫。很吵,像我的心情那么吵,但我不能踏出叶国辉的房间一步。
ADVERTISEMENT
我曾几次悄悄打开门,门外是饭厅,六人椭圆形饭桌是寂静的,没有人坐在那里,也没有人经过,但是我听得见从客厅传来的欢歌笑语。没有人认识我,我只认识叶国辉一个人,我走不出叶国辉的房间。
我真后悔答应叶国辉来参加他的生日会。
来这里吃吃喝喝,认识几个新朋友,唱了生日歌吃了蛋糕就走,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周末的夜晚很郁闷,电视机坏了,网络欠费被切了,太多理由逼迫我要答应叶国辉的邀约。
好吧,我承认我对叶国辉有好感,否则5辆卡车也没法把我拖出去。认识叶国辉只有几个星期,他常光顾我兼职的便利店。本来他会买瓶可乐或者一包Mister Potato的薯片,最后他什么都没买,只是来等我下班,然后送我回家。
那天,他问我要不要去他在家办的生日会,我当下拒绝,因为我没钱买礼物。临时改口答应了他,他没有问我原因,这是他的优点。好吧,我承认我对叶国辉有好感。我想知道他家在哪里,房子长什么样子,有什么收藏癖好,当然也幻想跟他共度他的生日,留下一个美好回忆。
现在,我就在他的房间里,有一整个晚上看个够。他的房间没有一本书,连杂志都没有,只有一整墙的音乐CD。房里没有一张椅子,我坐在地上重复听着陶喆的《爱很简单》至少5万次,腰椎快变成S形。不要问我关于屁股的事,我已经感觉不到它。
叶国辉忽然敲门,不等我回应就推门进来。
“你好吗?”他问。
“好啊。”我轻快地回答。
“我很快再过来,再等一等。”他说。
我微笑看着他:“去忙吧,我听歌听得很好。”他就出去了。
好?好个屁!
我要将CD掷向房门,把房门磕出一个大凹洞。叶国辉的枕头躺在床上笑我,外头气氛这么欢乐,你被抛弃在这里发闷气。我要捏死那两个枕头,把它们撕成碎片,然后丢进马桶里。我不会让它们被轻易地冲走,我要它们被塞在马桶的排水管中,永不见天日。
整面墙的CD都在笑我,你可以马上离开这个房子,走啊,快走啊。它们刺痛我的自尊心,我要把它们全扫到地上,踩在它们脆弱而虚伪的塑料盒子上,听它们被折断时候的哀号,央求我的原谅。
我忍天花板上的那盏灯也很久了,打从我一进来它就一直瞪着我,不断增强它的亮度,试图要照瞎我的眼睛,多么造作的白色。我要让CD都瞄准那可恶的灯,把它丢个稀巴烂。
叶国辉又回来了。他看见我还坐在地上,抱着双膝听歌,看起来很专注。我发现他颈上的深红色印记,像夜幕的星星,那是之前没有的。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忍不住偷瞄那些印记,虽然难以置信,却还是确定那些都是吻痕,绝不可能是敏感或捏出来的。每个大小不一,充满了强烈的攻击性,仿佛血色的文字,怒吼着占有权。
叶国辉若无其事,或许当我有视力障碍;又或许他是被迫来展示给我看的,脸上有细微的无奈和低沉。
他说:“再等一等,就吃蛋糕了。”
我说了一声谢谢,他又出去了。
谢什么?谢个屁!
我到底来这里是为了做什么?
不知道我妈此刻在做什么。我离开家的时候,她还在睡觉。我不知道她昨晚喝到几点。昨天我下班回到家后,她还没有回来。半夜我醒来喝水时,她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喝酒,灯也没开,像平常那样把我吓个半死,像平常那样自言自语,泪流满面。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电视屏幕破了,裂痕像蜘蛛网的图案其实很美丽,电视柜上的玻璃酒瓶碎片反射晨光,我喜欢这种暴力的优美。我才想起昨天好像听见几声巨响,但我实在太累了,没法起身查看。
我很想打电话给我爸,跟他要买电视机的钱。我们家很需要电视机,因为我妈没看电视会变得神经质,妄想我会抛弃她去找我爸,甚至有谋杀她的意图。
我妈两个月前和我爸大吵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从前,他每个星期从新加坡回来,虽然我并没有表现得很高兴,但是至少他总会带一些什么回来,吃的用的,像按摩椅﹑空气过滤机、气炸锅之类看似不错又不太需要的电器。还有日本进口的大苹果﹑韩国进口的大葡萄﹑生鲜鳕鱼等,味道都不算坏。
我和我爸的关系也不算坏,比和我妈好,虽然他真正的家庭在新加坡,国籍是新加坡,而我们只是他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停靠站。那都无所谓。他们已经把我生出来,也养了这么多年,吃好住好,我没什么要计较。
直到两个月前,我妈生气我爸仍然不跟他新加坡那一头承认我们的存在。
我爸很无辜地说:“都这么多年了,说来有什么用?”
我妈吼道:“我要堂堂正正做张太太,做小的也没有关系,好过什么都不是!”
我爸说:“不要无理取闹,一把年纪了谁理会你是谁的太太,你不就是阿婷的妈。”
我妈更生气了,指着我爸的头大骂:“你别想再糊弄我,我现在活得很清醒,你这个不要脸的男人。”
我爸听到“不要脸”就火大,声音也大起来:“你说谁不要脸?你才不要脸。”
他们“你不要脸”、“谁不要脸”的闹了一会儿后,我妈把我爸推出家门,顺道把他的鞋子正中丢到他的额头,然后哗地关上门。我听到我爸在门外痛得大叫,而我的邻居们也一定都听到了。
那天起,我就没有见过我爸。我几次想打电话给他,因为他已经两个月没有给我们家用了。但是,我妈说如果我打电话给我爸,她会把我也赶出去。我妈完全没有找钱的打算,还开始喝酒。要知道,酒不是便宜的东西,而我们根本没有本钱借酒消愁。
最后,我只好到便利店兼职,在两母女饿死前挣点钱,或许可以多活一阵子。
上班第二天下起了雨,叶国辉在店里逛了很久。我怀疑他想偷东西。店长说小偷不分年龄或外表,有些人偷窃纯粹就是贪图刺激和成就感。
雨停后,叶国辉拿着一瓶可乐来付钱。我一眼也没看他,只希望他快点离开,我要打电话给我妈,告诉她我今天忘了带钥匙,千万别把门锁了,也千万别三更半夜才回家,明天一早我得做课堂报告,而我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准备。
叶国辉很利落地付了钱,就走出便利店。一周后,他再度上门,同样买了一瓶可乐。接着是两三天后,他又来到店里,买了一包Mister Potato薯片。他到店里光顾的次数越来越频密,直到有一天,他问我:“现在几点钟了?”
我回问他:“你的手机不能显示时间吗?”
他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这只是我想跟你说话的借口。”
我从没有想过让叶国辉送我回家。那天上班后,肚子就闹脾气,把我肚里所有的神经线全绑在一起,不断拉扯﹑扭动﹑撑开又缩紧。一个经痛可以毁掉我所有意志,我变得软弱且毫无主张。叶国辉正好出现了,温和地提议送我回家。一向没和我多说两句的同事,见我脸色苍白也马上附和,很有义气似的帮我值班,但我觉得他是怕我在店里痛到往生。
自那天起,叶国辉都会来便利店接我回家。后来,我和叶国辉会到附近喝杯茶,或吃片印度煎饼才回家。我们谈了很多,说起他早餐时听的歌﹑刚才在路上差点撞上一只狗,诸如此类的生活琐事,从他嘴里说出来好像很有趣。我说我今天上学上班都差点迟到,但是放学下班都很准时,还有对于猪原来都是双眼皮而感到很惊讶。每回谈及家庭,我就打住。叶国辉从不问我为什么,总是保持谈话通畅的距离,令我说了第一句,会想再说第二句。
有一段时间,他整个星期都没现身,我的夜晚静得像半夜停止放送节目的电视机,只剩下无声的杂讯,细碎的黑白色盲目地飘来飘去,似乎很规律,又似乎很紊乱。跟着我的白天也变得安静,上课的思绪是单向道,走出去就不会回来。几天后,仿佛叶国辉不曾出现,我回归原来的轨道,才知道习惯是一场惊悚剧,像落入荒岛而不知所措,失去抵抗孤单的能力。
再见啦,叶国辉,我一边走路去上班,一边看着踩在柏油路上的双脚说,心里顿时觉得很自由,没有等待和期望,这才是我原有习惯的人生。(待续)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