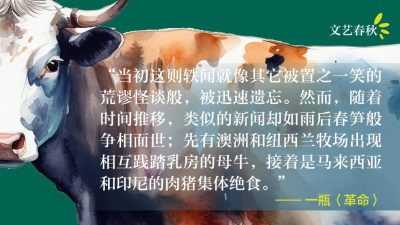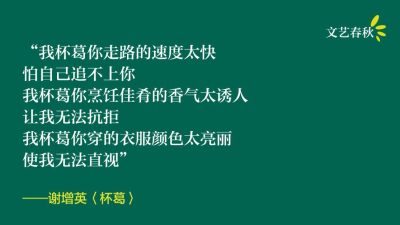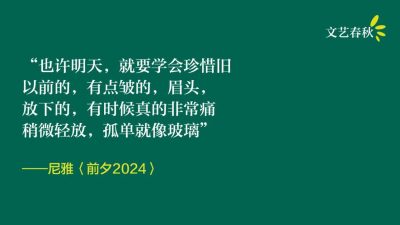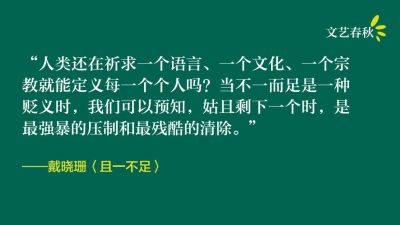ADVERTISEMENT
a.
来到安平,总让我想起马六甲。
在那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开始如鲸觬冲破了千波万浪,横跨了大西洋、印度洋、越过了马六甲海峡,直上南中国海,到了台湾和日本等国,贸易风带出了一片辽阔的海图,让西方探索的眼睛开始发现了东方神秘世界的故事。那海潮和风浪卷起的狂飙,几乎吞没了整个东方世界的传统,使得东方世界的故事被扩展成了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版图。
所以当马六甲王朝在公元一五一一年被葡萄牙的舰队冲刷过海岸,并被砲弹轰炸出了一个历史的大缺口时,末代苏丹携家带眷往南逃亡而去,流落到南方之南的一座民丹岛(Bentan island)上,百年王朝遂亡于海上雄狮的吞噬之口,同时马六甲也成了开启一条东方香料航道最早的驻站。圣地亚哥城堡、圣保罗教堂也开始在马六甲小山上建筑起来,这几座以一块块石头建筑起来的葡萄牙殖民史诗,伫立在马六甲的山上,如垂天之云,俯视着那片古老的土地和海岸,并在城堡上面,竖起了西方的第一面旗帜,在西南季候风中狂狂然的招展。
而那时的安平,却还没有历史和文字的记载,只能凭借想像,想像在那天荒地野,麋鹿奔跃;黑水乱涛,倭寇横行的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广漠天地;想像那被称为大员的岛土之上,有西拉雅族的社群聚落散布在四周,他们以猎鹿耕地维生,是如何追逐着日昇日落过活。那时,葡萄牙人还未出现,还未看到海洋婆娑的美丽之岛,而不由自主地高喊出福尔摩沙这名称来;荷兰人也尚未到来,历史正以最原始的面貌,呈现出了安平的一片荒芜。天地在此交际,水气澎湃,只有简陋草寮间的一排排骷髅悬在寮亭上,有时被风吹得轻轻晃动,或彼此互相磕出喀喀喀的声音来。
那是个不记年岁,交易以结绳方式做记录的年代。聚落中常以苦草酿酒,竹筒盛饭,闻乐而舞,长歌不辍的年代。那是个鹿蹄千百,在平原草丛中奔若雨声过境,野地蔓草正等待开拓,而文字尚未踏入大员,历史仍被放在风中歌唱的年代啊。
直到万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陈第因追随沈有容将军追击海寇而渡海到了台湾,并且随着深入岛屿,以更确实的笔调,记录下了眼中所见的〈东番记〉,自此大员以上的岛屿,以及一直以来没有历岁书契的西拉雅族之日与月,遂有了历史文字黎明的天光。而彼时,马六甲已被葡萄牙殖民近于百年,圣地亚哥坚固的城堡,也开始在风雨中露出沧桑的痕迹了。
不久,荷兰的海上舰队却悄悄地穿过时间大雾,航向了遥远的东方。当一六一九年荷兰攻下了印尼爪哇岛上的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于巴达维亚做为据点,展开了扩大远东海上版图和殖民的计划。一六二四年,荷兰人从澎湖撤退下来,如西方之鲸,侵占了当时衰敝明朝王权所不管的“大员”,并在此建起了第一座欧式城寨“奥伦治城”(Orange),并于一六二七年改名为“热兰遮城”(Zeelandia),以及在台江内海对岸,大动砖土,兴建起“普罗民遮城”来,所有荷兰官员都住在这两个“王城”内,与城外的居民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热兰遮市镇也开始开发了几条街,如南边的新街、宽街、北街和窄街等,台湾的第一街在此延伸,形成了井字型状,护着千家万户和各国住民,并在此写下了一页具有国际化特色的城市史。
在另一个东西季候风交会的地方,一六四一年的砲声却惊破了马六甲圣地亚哥城堡的夜梦,进而将统治马六甲一百三十年的葡萄牙从马六甲海峡赶出去,结束了葡萄牙语穿行于马来街道的故事,并开始了另一段一百八十三年以荷兰语写成殖民史的章节,也建起了一座面对着马六甲河的荷兰总督府(红屋)。这座府邸,可以说是已成了这段历史的重要注脚。
这期间,大员和马六甲海岸都可见到各国船舶云聚,通商海岸流运着各种香料、丝绸、茶叶、香烟、糖、瓷器、香水、鸦片等贸易品,且随着季候风北下和南上,航经马六甲海峡,浪涛响彻舷边,昼夜流转,将大员和马六甲的航道连接成了一条东南亚最明亮的水线,激溅出了十七世纪初璀璨的浪花。海盗的船只也在海雾中时常出没,风雨天光,共谱了一曲海上探险的交响曲,直到——
直到一六六一年中,大明招讨大将军郑成功以传奇的身姿,率领两万多人,从柯罗湾,以鲸虹的气势,拨开大水沧沧的经纬,划开迅速的水浪,穿过鹿耳门,到台江内海,展开了鼎鼎磅礴的血战。所有沉睡的鱼龙那时都被惊醒,风云流布,在那挥舞的剑尖上,战鼓擂动出一曲勇猛的战歌,千帆擎起,一一列队成了史书里不得不书写的一片壮阔。
而围城九月,终于逼出了荷兰在台最后一任大员长揆一(Frederick Coyett)的和平协约书,从此之后,遂开启了明郑时期的“安平”,“大员”的名称也随着历史一起遁退,化作了史书中的一个名词。此后,“安平”成了明郑立于台湾史诗上一个“反清复明”的最后抗争基地,直到郑克塽在一六八三年八月跪举降书迎接清水师提督施琅入台,明郑所建立二十二年的延平王国,终于消亡于水雾之中了。
我翻阅着历史,历史却如波浪拍碎了我的思绪,然后退远成了潮退后的沙岸,静静的将文字海岸线串联起来,成为想像无法抵达的边界。堡垒的残迹,剥落的红砖,都爬满了岁月的枯藤,抬眼遥望,却难以望穿那四百年的历史景象啊。而人如潮水,去去不回,繁华胜景都逝如泡沫;古楼烟尘,也带出了古老故事里的苍凉,我似乎听到历史想说些什么,讷讷的,欲言又止,最后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来到马六甲,却总让我想起了安平。
b.
我最初到安平时,那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与当时的女友匆匆来去,记忆中就只站在那攀着苍劲古榕树根的热兰遮外城南壁遗迹下拍照,但照片曝光,只见城墙剥脱而露出了枣红色的砖块,呈现出了一种古老苍凉的美,人影却在光亮刺眼的空白处显得有点模糊不清。我常常企图从照片中的景物,去搜索往昔走过安平的足迹,但记忆却挖掘不出过往的印象,最后只能颓然叹息不已。
后来某次旅行至马六甲,从马六甲河沿岸走到了荷兰广场,看着这一带红色古老建筑屋,都是荷兰人遗留下来的四百年古迹,仍然完好地矗立于马六甲河岸前,总督官邸已成了博物馆,基督教堂仍然高悬着十字架,发出清亮的钟声,敲落了古老岁月的悠悠光尘,在那晴朗的天空下回荡;不远处的圣芳济天主教堂上,鸽子飞起又落下,啄食着游客丢落的面包屑,时间却喧哗地从游客的脚步间溜过。当我随着游客的身影拾阶踏上圣保罗山上,目触着已成断垣残壁,裸露出枣红砖块的墙面,以及已成了摆放荷兰名人碑块墓园的圣保罗教堂时,让我突然想起了安平古堡,想起了夏天里一树林蝉叫的嘶喊,想起巷子寂寂的古老时光,闲散地在几个老人围聚的谈话中,慢慢走远。
从马六甲到安平,千山万水,沧海遥隔,但这两地的一些些故事,却都曾经走过了四百年的岁月平原与丘陵,走成了些许相似,却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景。而荷兰人留下的古迹,都凝固成了历史的石碑,在马六甲仍有一些被保存得相当完好,但绝大部分却已烟消云散;而在安平,遗迹多已不复再见,只剩下几面残缺的城墙与断壁,在老树枯根的缠绕中,见证了历史窸窣有声行经几个世纪的过往,里头曾有过无数政治的动荡与生命的呐喊,敲打石砖,却再也找不回四百年前荷兰话的语音了。(待续)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