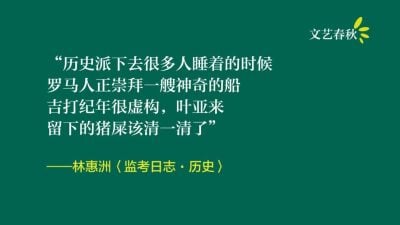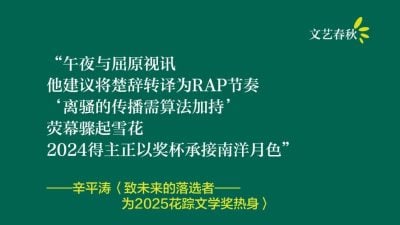榴梿季/金睿瑜(峇六拜)



榴梿季,街道随处可见移动式棚子搭建的榴梿档口。每当家人随性购买榴梿回家,家中必然掀起一场“吃/不吃”榴梿的风波。然而,生者的饮食习惯仅仅是风波的后话,长辈一般嘱咐我们先把开好的榴梿摆在祖先牌位前,待祖先享用,后人才可以吃,似乎忘了询问祖先吃不吃榴梿。
“榴梿出,纱笼脱。”小时候,每当外公家的红毛丹树开始结出浅绿色的果子,外婆便会教我念这句俚语。长大以后,我才意识这个现象有些诡异,因为平日只说福建话的外婆,居然用标准华语念俚语。我来不及问她从哪里学,为何要这么说,她便撒手人寰了。
ADVERTISEMENT
外婆死后,我以为她从此和榴梿脱离关系。岂料,外婆却给表哥托梦,要求他买榴梿拜她。人死后,还会想念生前喜欢吃的食物吗?妈妈和我协助表哥把装盒的榴梿分配给神明与祖先的时候,在场的家人随即讨论起这个话题。
根据我对外婆的了解,她对榴梿已经到了不挑品种的热爱程度,不论山榴梿、D932、林凤娇、红虾、黑刺、猫山王,甚至任何我叫不上来的品种,她全盘买单。动骨科手术前,外婆三不五时就买榴梿回来,她的孩子们总是叫嚷,哎哟,又买榴梿啊,以隐喻的句式劝阻她买榴梿。外婆从来不顾孩子反对,就在地上铺几张旧报纸,随意点名孙辈帮她开榴梿,然后一口盐水一口榴梿,咕噜咕噜地把果肉吃下腹,适才那些劝阻她吃榴梿的孩子也纷纷围在她身边相互分食。
当时表弟表妹尚未出生,我仍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因此,外婆或妈妈那辈的家人总会往我嘴里塞榴梿。若吃到甜口榴梿,我会恨不得多吃几个;要是咬到苦味榴梿,我便会像小狗一样吐出舌头,随即逃离分食现场,仿佛这样就能散一散苦味。
买榴梿祭拜太公太嫲
无关爱与不爱,我对榴梿全然无感,吃不吃榴梿则取决于我的心情。妈妈那家的长辈总说,马来西亚人一定要会吃榴梿。听见这句话,我便锁紧眉头,露出“儿”字,以一张表情解释心里复杂的情绪。当大人误以为我不喜欢榴梿的味道,要我捏住鼻子吃榴梿的时候,又有另一把声音说,她的阿公阿嫲(爷爷奶奶)是唐山来的,不吃也不奇怪。我不足5岁,可以听懂大人的对话,却无从解读深层含义。在我看来,这句话简直是我的救命稻草,说出这句话之后,在场的家人便不再逼迫我吃榴梿,不懂如何反应的我总算可以离开混杂的场面。呼,好险。
从前不晓得怎么介绍父亲的家族,妈妈总是提醒我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是中国人。某日,我忽然意识到同学的祖先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不同。念了中文系,我才明白爷爷奶奶准确而言是第一代移民,两人分别于1947年和1959年抵达槟岛,在这里开枝散叶,这个情况是近代移民史中相对少见的案例。
其实,我不太清楚爷爷奶奶移民的细节,包括他们如何适应当地生活。然而,我能从爷爷奶奶的衣着分辨他们与外公外婆的差异,尤其奶奶与外婆,她们更能象征两个地方的女性群体。奶奶总是穿黑裤长衫;外婆更爱围纱笼,两人说着同源的福建话,但是惠安腔与南洋腔将她们分置于两方。当我苦恼于奶奶和外婆的身分,我却在她们身上找到共同点——爱吃榴梿。
相较于外婆豪放潇洒的吃法,奶奶总是抿一小口、一小口地把榴梿吃完,表现得非常含蓄。看着奶奶的穿着,我忽然联想到外婆教我的俚语,可是奶奶没穿纱笼。外婆去世前半年,奶奶先走了。她的忌日落在农历六月,但是祭拜奶奶之前,我必须先于农历四月和五月祭拜太嫲太公。
太嫲、太公和奶奶的忌日分配得相当平均,一个月祭拜一位先人。这几个月份普遍遇上榴梿季,姑姑们也会买榴梿拜祖先。太公太嫲吃榴梿吗?祭拜太公的时候,妈妈忽然问我这个问题,我征了一征。犹如外公家的灵魂拷问,这场对答置换了提问者和答题人,我不知怎么回答。姑姑随即开口解惑,阿嫲很喜欢吃榴梿的,然后凑到我的身边小声地说,可是你爸不喜欢。
看向一桌的祭品,我开始想像先人吃榴梿的样子。爸爸与祖先齐名,是祭祖仪式的受邀成员,不知他看到榴梿会有什么反应,和我一样不知所措,还是索性逃跑?突然,我悟出另一个新道理,爱吃榴梿的妈妈养出不爱吃榴梿的孩子,奶奶和爸爸如此,妈妈和我亦然。外婆的七个孩子都爱吃榴梿,偏偏到了我这代,只剩下姐姐是榴梿狂粉。
对于榴梿,我既不像长辈般痴迷,也不像部分的同辈看见榴梿就逃跑。我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供桌上的榴梿,反复揣测,为什么他们会吃榴梿呢?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