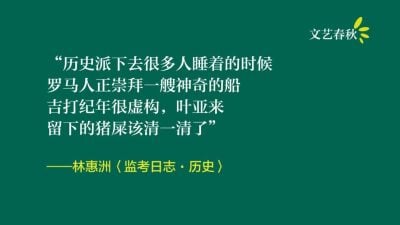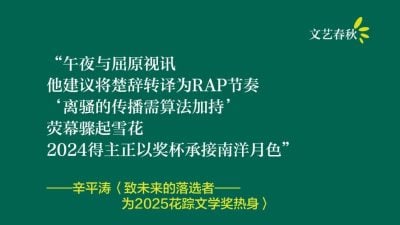郭于珂/木偶惊魂记



冠病肆虐的那几年,我经常感觉自己在做着同一个噩梦,或是活在某个没有出口的地狱里。
我见过崩溃的医护人员,因氧气筒不足而必须在病人的生死间做选择;我听过殡葬业者讲述死者“排队”一周才能火化的故事;还亲眼见证重症病患被透明的隔离罩覆盖,宛如一条死鱼,等待被病毒吞噬;更夸张的是,我最常视讯的人不是亲友,而是病毒专家。几乎三天两头就得连线,像追剧一样掌握变种病毒的最新发展。
ADVERTISEMENT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你可能只会担心自己会否确诊,但记者的日常工作却像在撰写连载的惊悚小说,因为病毒如同鬼魂,肉眼看不见,它却无所不在。在那段日子里,我和同事的精神状态都非常糟糕,每天一觉醒来就得迎接新的悲剧。
2022年尾,我终于因过度压力丢下电视台记者的工作。本以为能逃离“医学领域”,结果更离谱:对象从白袍医生换成了热带雨林里的原住民巫师。
起初,我只是为了协助本地电视台拍摄民俗节目,才开始寻找那些濒临失传的传统疗法;没想到一来二去,竟阴差阳错地成了我的硕士论文题目。
不过,想找到愿意上电视的巫师也不容易,因为许多原住民社群都有一个共同禁忌,即治病仪式必须在全黑中进行、不允许外人参与,以及禁止拍摄和录音。
触犯禁忌会有什么后果?轻则相机故障或录到怪声,重则灵魂走失、巫师身亡。可想而知,我全都撞上了。
这几年,我时不时会一个人跑进深山野林,在没有讯号的黑夜里聆听巫师吟唱咒语和燃烧甘文烟(kemenyan),连结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
我看过病人被灵体附身,突然嚎啕大哭,也碰过被祖灵半途中断的治疗仪式,“警告”巫师若执意继续,现场所有人的灵魂都会回不来。
当然,要说最惊心动魄的经历,莫过于我与嘉户族(Jah Hut)治病用的木偶——sepili 的那次邂逅。

灵魂被偷恐致病 需靠木偶收服“恶灵”
嘉户族相信,一个人拥有7个ruay(灵魂/精神),只要其中一个被恶灵bès偷走,那人便会生病。为了赎回病人的ruay,巫师会透过灵伴的协助鉴定“凶手”,再交代族人雕刻特定的木偶收服恶灵,因此每个sepili的造型就是bès的模样。它们的形态各异:有的似人,有的如兽,还有的手持兵器,面貌诡谲莫测。
为了应对这些无所不在的恶灵,嘉户族长辈会将每一个bès的故事和形象,透过口传的方式交给后人,因此每个男孩从小就得学会雕刻这些木偶。

巫师告诉我,他们的木偶有几百种样子,而每一个都能对应特定的“症状”。例如,若病人感到头痛,那干扰他的恶灵有可能是Bès Rungkup Tajam Kepala;失眠的话,则怀疑是Bès Yak Yung TT Galax搞的鬼。
这些恶灵的名字听起来像外星语,但在嘉户族人心里,它们就像城市人听到“癌症”或“新型病毒”一样,会头皮发麻。当然,嘉户族的巫师并不会在每一次治病仪式中都动用木偶,而是会根据病情轻重,决定要进行到哪一个阶段。

一般上,第一阶段的治疗被称为Muruk,即巫师会咀嚼黄姜,并将嚼碎的粉末涂在病人身上;第二阶段叫Tepung Alin,巫师会在病人身上搓揉一个面粉团,收服恶灵。若病人的情况太过棘手,则需要进入第三阶段Trekben,而巫师会把木偶放置在病人后颈,一边默念咒语,一边“抽走”恶灵。

最后,巫师会利用Salak叶制作的“武器”拍打它们,再命令助理火速将所有的木偶丢到无人会涉足的丛林里头,且丢的时候不能回头,要不然这些恶灵会盯上你,把你变成新的猎物。
作为一名好奇心旺盛的人,我当然回头了,还触犯了其他禁忌,结果接连遇上一堆难以解释的怪事。
偷把木偶带回家 厄运衰事接踵而来
| 普通会员 | VIP |
VVIP | |
|---|---|---|---|
| 星洲网平台内容 | |||
| 星洲公开活动 | |||
| 礼品/优惠 | |||
| 会员文 | |||
| VIP文 | |||
| 特邀活动/特级优惠 | |||
| 电子报(全国11份地方版) | |||
| 报纸 | |||
首先,在拍摄Trekben仪式的过程中,摄影机突然出状况——电池莫名其妙掉落,导致过去整整一个小时的连拍画面全都化为乌有。幸好,这个仪式会进行两个晚上,所以我们还能在第二晚重拍。
后来,我们又拍摄了一位嘉户族男子制作Bès Pintu Katak(门蛙恶灵)的雕像。据说它常栖息在森林里的小溪边,那里布满碎石,还会渗出红色的液体。
但之后用 AI 语音转录访问内容时,我却发现,在雕刻师摩擦这尊恶灵屁股、为其抛光的片段里,竟被识别出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你要怎样让我活过来?”
更可怕的事,发生在我把木偶带回家之后。为了方便摄制团队好好拍下那场仪式中使用的8个木偶,我们请嘉户族的朋友重新雕刻了一组“道具”。
虽然他们再三叮嘱,拍摄一结束,就得折断这些木偶并丢弃在偏远之地。但天真的我以为,没收服过恶灵的木偶是安全的,便将它们当作纪念品留下。
结果,这些木偶跟我回家的那一天起,我便饱受失眠之苦,甚至感觉脑电波好像故障一样,一直能听到奇怪的声音,整个人的磁场也毫不对劲。
我当然害怕自己被标签为迷信之人,所以在那些无法入睡的夜里,我总是不愿去思考它们之间的关联。
然而,每次只要我试图为这些木偶辩护,寻找留下它们的可能,我就会遭遇不幸,像是确诊新冠病毒、家里遭到爆窃、耳朵莫名发炎或眼睛冒出不明异物等等。
就这样折腾了好几个月,我收到了最震惊的消息——嘉户族的巫师过世了。
原住民巫师过世 宛如一座图书馆被烧毁
在原住民的世界里,人们常说:“当一个巫师死去,就像一座图书馆被烧毁一样。”过去的我不曾真正体会这句话的重量,直到听见巫师的死讯,仿佛看见那些古老的咒语与祖先的智慧化作落叶,在雨林里缓缓焚成灰烬。
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巫师,我紧紧握着他的双手,深深鞠了一躬,心里盼着来日还能再会。直到事后才惊觉,那原来是一场告别仪式。
虽然他本来已经抱病在身,但我心中仍不免涌起一股沉重的罪恶感,是否因为自己无知地触犯了禁忌,才让他的死亡来得更快?

那一晚,我再次彻夜难眠,脑海里浮现的全是巫师血红的牙龈——那个被槟榔染出的笑容,鲜艳得像在展示他嚼碎恶灵Bès的证据。
可真正让我心慌的,是忽然意识到:若巫师已死,那谁来帮我收服恶灵?让我辗转反侧的会是Bès Yak Yung TT Galax吗?我当然没有答案。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