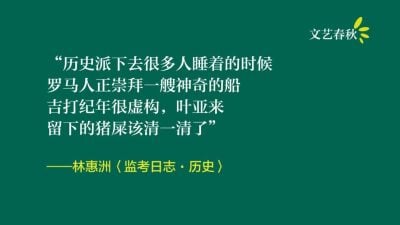卓振辉/新村,新村——如皮屑般细细碎碎的东西(上)




《卷蜘蛛网的牙签》出版后,大家似乎将我和新村绑定起来了。诗人郑羽伦有段时间卯起劲做YouTuber,介绍《卷》时称其读出了书中浓浓的乡土气息。坦白说大出我意料之外。彼时没好意思说出口(毕竟人家愿意不计酬劳在油管介绍你的书),但内心想法是:《卷》固然有背景设置在新村的小说,但也有设置在怡保旧街场、茨厂街、新山等地的故事。况且我写的,说到底也只是属于自己的故事。
换言之,不得不坦诚自己没有要写“新村故事”的意识。要是有人向我邀稿说希望写写“新村故事”,恐怕我会三思而后拒,拒绝的拒。以当时的我而言——如今亦然——最不希望的就是被贴上任何标签。就跟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拒绝被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或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拒绝其小说被贴上单纯侦探小说的标签,或骆以军拒绝其小说被贴上私小说的标签一样道理。又或者……肯定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此处不一一列举。眼下想不起来,主要是。
ADVERTISEMENT
不过,任凭作者如何咬紧牙关拒绝标签,读者的感受毕竟最为直观。于是思来想去,花了相当长时间独自消化这神启般的资讯。最终接受事实,如公堂上法官庄严肃穆地拍板定案,敲下结论:新村活在我身体里,新村也自然而然活在我笔下。就是这么回事。
一旦承认,反而像从胸口抖落一块千斤重的石头似的,石头掉落一面湖里,被温柔且黏糊糊的湖水包围。
当然,不是说从此认定自己为新村作者、非写新村故事不可。从前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会是。而是说——我尽量精准——某种无以名状的新村气息(或曰精神)总会竭尽所能透过我的笔触洒落字里行间。像入冬地区的一面湖(又是湖?),湖面结冰了,冰层之下的石头游来晃去想方设法找到冰层的裂缝并且一跃而出。简而言之即如此。至于石头为何游来晃去而非沉入湖底一沉到底,这暂且不管。
换言之,一个成年人在新村待一天、一星期或一个月,对其世界观不会产生如地壳摇晃似的动摇。要是待个一、两年,也只会在其意识之玻璃球染上一层略微异色的薄层。在新村成长,就是另一回事了。
有段时光我迷上大陆剧《去有风的地方》。女主到云南一处偏僻度假村休养3个月,各种迷人的机缘巧合之下对人生的意义重新思考,并且与当地一位有志青年堕入爱河(就电视剧而言,不堕入爱河是不行的),最终在当地开张酒店,为振兴当地旅游业贡献一份微薄之力。设定着实迷人,但剧毕竟是剧。大多人对偏乡之地抱持无聊单调、甚至适合退休养生之类的想法。一望无际的稻田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是心旷神怡的景色。身处城市而决定回乡发展的,自然不乏其人,但比例上恐怕属于少数。My FM电台曾做过类似话题的听众来电环节,印象中有回乡之后风生水起的回答,但大多听众提供类似答案:在城市落脚多年,生活方方面面已然成型,况且谁能保证回乡之后能确保眼下的高薪?
不过说到底,剧是剧,现实是现实。云南是云南,新村是新村。无法平行搬运。
况且,我扯远了。
和身为新村过客的身分不同,要是你从小在新村长大,呼吸新村空气、脚踏新村土地、和新村人交流是是非非沟通人情世故、感受过新村早晨宁静致远的清澈(不仅是有高楼大厦和没有高楼大厦的天空之差别,而是更深层次、几乎精神性的差别)、领教过新村夜里可怖的寂静(对胆子稍小者而言,入夜后从新村街头徒步至街尾是巨大挑战,主要是心理方面的挑战),十多二十年下来,新村魂气早已悄悄充盈你整个人。从头到尾,由里至外。大至人生观世界观,小至神经细胞上的电信号及神经末梢的化学分泌物,新村统统把控。一回头你发现,所谓自己无非是某垂垂老矣的新村之神在闪晃着灯光火影、神秘兮兮的冶炼室用新村泥巴加上新村的金木水火土揉捏而成,并且往嘴巴里吹进一口新村气而活过来(多少有些异样)的生物。至于新村之子是否按照新村之神的模样构造—— 只好另求高人指点一二。
而我土生土长的新村乃新邦波赖(Simpang Pulai),怡保一处小地方。你或许听说过,或许没有。
虽常自称新邦波赖人,我向来不知如何同外地人介绍新邦波赖。一来是个小地方,二来无甚特色,三来我是名副其实的路痴,对地名、路名及地方名之类的永远搞不清楚。
一度怀疑是当代年轻人的通病,毕竟成长于所谓GPS时代,但细究起来GPS时代到来之前我已活脱脱活成这副模样。因此,和GPS之有或没有无关,我天生担当不起只要动口就能让人脑海里生成一副路线图,并且准确带领对方到达目的地的那种角色。坦白说,考到执照初期,家里对我驾车出门是心怀忧虑的。看脸色就懂。一脸此君会不会又迷路、白白浪费车油、无法准时回家吃饭的神色。
更有段时光我特别固执,拒绝和现代科技扯上太多关系。年轻人有种种固执实属正常,但彼时拒绝当代科技的年轻人相当少见,如今恐怕更少,近于稀缺物种。不用GPS,而是坚持脚踏实地地认路,结果迷路迷得乱七八糟,只好认命。当时有种朴素世界观被彻底瓦解的悲哀。如今看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更盛一些。
当然,即便摸透了GPS的操作方式,对于介绍新邦波赖方面也没什么帮助。只好旁敲侧击。如今说起新邦波赖,我会说新村入口位于金马伦山脚路口左近,入口处旁边有座国民型小学,唤培英华小。而人们脑海中将浮现画面,并且将画面与画面拼接起来,接着眼睛睁圆大腿一拍嘴巴啊啊啊地说,是的是的,他大概知道彼处何处了。这,各位,就是家乡附近有个地标性旅游景点的好处。
自不待言,世上的人林林总总、社会林林总总,新村也同样林林总总。全马四百多个新村,有的发展持续兴旺、也有的长期停滞不前。新邦波赖属于后者,幸或不幸,难说。位于金马伦山脚路口左近,并未为新邦波赖带来实质影响。当中恐怕有更深层的地缘因素,私以为。新邦波赖往北是Gopeng(由新村扩展而成的城镇)、往南是怡保市区,恰好卡在一个中间的、尴尬的位置。有点像以色列,一边是欧洲诸国,一边是俄罗斯,两头不到岸,两边都成为不了。30年前到新邦波赖和30年后到新邦波赖,不会有物是人非之感。基础设施自然有所改善,但气质上始终如一。
换言之,和所谓“故乡历经时代洗练”类型的写作者不同,我(或同类写作者)面对的是30年如一日、不动如山、如往深海抛锚般沉甸甸的生活场景。这对我(或同类写作者)而言,恐怕是写作者养成的决定性因素。幸或不幸,难说。
◎
可想而知,年轻人纷纷出走。近年来,临近地段被某发展商(说来是深耕多年、远近驰名的发展商)相中,大量投资开辟成新型住宅区。
所谓新型,即除了住房(以对传统新村人而言价格不菲的房价起跳),也包括学校、医院、公园等等设施。说不定未来会建超级市场或大型游乐场。经济能力稍好的华人逐步逐步地迁移过去,新邦波赖也逐步逐步地成为老人村。跟一人人体代谢逐渐凋亡,而另一人刚诞生到世上生机勃勃活力充沛没两样。当然,也有新血注入新村——外劳们。在城市,外劳越来越多实属正常(至于为何实属正常追究起来只会横生枝节,不追究也罢),但城市毕竟体量大,外劳的增多不会在短期内引起视觉上的强大冲击。(12月2日续)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