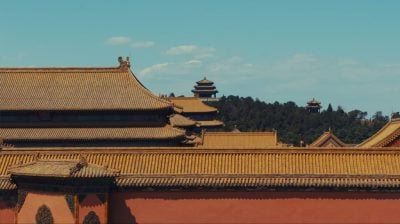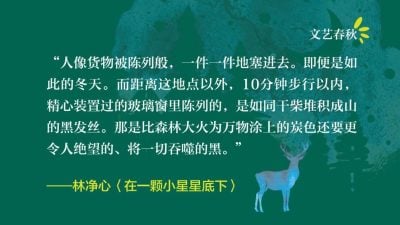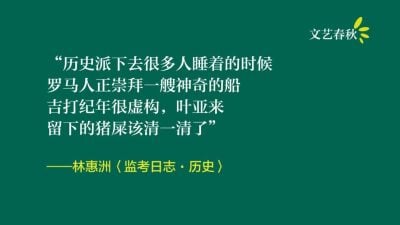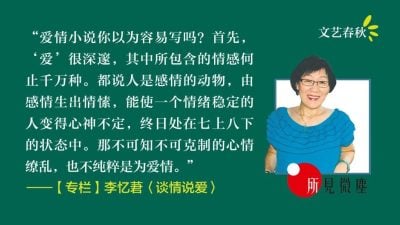【爱华文】你说啥?/林展邦(蒲种)



怎样才算不爱华文?
我真正遇见一个不爱华文的人是上学期的事,由于她和我仍有联系,姑且称为J,容我先带入一点她学习华文的始末,并由此说回我自己。新年期间刚听过〈你说蛇〉,以为会是现代流行曲风,谁知除了背景乐节拍和这几年新年歌的经典桥段:舞到一半必有饶舌,〈蛇〉整体上走传统路线,没有电音,没有太过嘈杂的人声。熟悉的新年旋律让我想起华文学会、一日营现场等等的热闹画面,会员、营员就像一个村的家人,而我的主要目的是把脱队的J拉回去。
ADVERTISEMENT
【起源】
J当然不会对着我问“你说啥”,或者评价〈蛇〉究竟有没有电音。从各方面看,她和一般女同学没有差别,不矮也不太高,扎起全级泛滥好几年的不长不短的马尾,笑声像鹅,她应该不知道那是比喻修辞手法。我在她身上初次意识到自己不适用长句对话,这样只会换来她以另一种类似“你说啥”的形式向我确认刚说过什么,有时我得即刻思考一个英文词。
她自嘲地称自己为Banana,虽然真正的香蕉人要西化更多,而她还能与同样在中四报考华文的我们以华文沟通。我们坐在午后三点闷热的舱室,阳光自西面操场毫无保留地照到课桌上。华文班课时一向长气,我相信这不是授课老师的问题,而是J解读课文的速率实在需要时间。有一堂〈醉翁亭记〉,开头好几大段的景物描写就让她卡在原地。
忘了是不是第一堂华文课,老师把我推到这样一位女生面前,善意地希望我能搭把手。作为J的前座,仅仅转个身的工夫,我想我确实有该尽的责任,理所当然幻想将她的分数拉过及格线。
【结局】
我参与红蜻蜓出版社的征文活动,得以为J带来最新一期《读一点》。等到大段空节取出,翻到长篇小说,我的初步想法是一页页教她认识更多词汇,否则以J的情况,只是写两三段不含注音的作文也实在困难。华文课漫长的四节,唯有老师们心照不宣创造的课间可以让授课老师询问进度,以大家平均水平推进的时候,就不得不暂时忽略J。
J犹疑着开口,读完一整句“什么,什么和什么”后停下,望向虚空,我迫切用更多英文词汇完整她脑中的想像。那是龙族的故事,管理员倾力呵护,只为几个脆弱的个体存续。J手中捧着的华文课本也和快要解体成一堆部首和笔画的易碎物没什么两样,她需要一个能重构零件的帮手。
对J而言,这只是一个缓慢下落,终将触底的过程。初升高,她错过弃考华文的日期,似懂非懂的点头成为她面对华文老师的保护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进退中尝试了解她的学习背景和家庭环境。J的确透露很多:在家人口操英文的环境下长大,虽然就读华小,华文成绩也曾经过得去,却面临小升初仅针对华文的适应不良。于是J任由华文科分数跌到及格线以下,老师的过度反应、亲人的逼迫,我们屡见不鲜的弃考原因组合在一起。
母亲对扶持J的计划既想支持又抱有忧虑。其一,J的华文水平倒退实在厉害,其二,年终考临近,我没有足够时间摸索一条辅导J的路。母亲果真一语成谶,我只能在考试前一晚结合个人经验和恩师提点,连夜敲出三四页浓缩笔记,建议J专答试卷一的应用文,试卷二的概述、韵文,即我认为还可能存在套路的地方。余下的一点乐观萦绕在梦境边缘:如果她兑现承诺打印笔记,再利用考前最后半小时读过一遍,一切应该水到渠成。我即便不完全承认她的能力,也理应相信我自己。
无法替代的文化内核
我却是没想到J会临场“罢工”。星期五作为年终考第一天笔试,只考华文等几个选修科,开考时间早,我们不必面对午后毒辣的太阳。但太阳尚未升起的时候,J弱弱地问了一句:“反正我明年不考了……可以不读吗?”
我把“你说啥?!”憋回,换成“你确定?”,问号末尾她点了头。我收起笔记,发现一场考试竟能把艰难经营的链条拉得那么远。事后想到最贴切的形容:J的成长曲线如蛇一般迂回曲折,最后头尾断开,〈你说蛇〉歌词中描绘的“我家最热闹”忽然显得不怎么有人气——我们常说学华文、报考华文的学生就是一个大家庭,而从华小与国际学校的分水岭开始,一次又一次洗礼和筛分,历经磨练的被公认更成熟,完好无损的朝另一个赛道疾驰而去。受伤的蛇无力化龙,剥落的鳞片里,一个体无完肤的弃子居于中央,无数个鳞片里有无数个弃子。
J的最后一舞明显高于她的平均表现,但我不能确定自己有无起到作用。龙年的尾巴带来最后一点好运,不止她,所有同学的分数都偏高,老师说这次题目简单得多。成绩发回那天,我抽出空档瞄到她两张卷子的平均分,不知该感到惋惜还是安慰。
【结局以后】
读理科却更像文科生的我,养成生活中处处皆是艺术成像的错觉,失败是跌落谷底,成功是敲开天堂之门。从古至今的文人都带有一点超脱世俗的疯癫,就是因为感受到文字之美,却难以共享的缘故吧。J主动缴械是一次宏观和微观上的完败:宏观上,对华文教育如此;微观上,对我本身亦然。
J的例子让我思考,除了中国的庞大市场和传承中华民族命脉这类对新一代几近免疫的说法以外,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学华文、报考华文、爱华文?答案或许还有一个。
蛇会为了进一步成长蜕皮,底下的新皮再逐渐长成蛇原本的样子,代表我们坚忍的文化内核,而新事物是外界一层层套上的涂层,即便能待一段时间也无法替代原有底色。追求涂层而舍弃皮的蛇,就像失去脸谱,在其他生物眼中便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
另一次空节,我把〈赵子龙长坂坡救幼主〉简化成“这人死了,然后那人也死了”的快节奏短文,哪怕只换来J迸出几声鹅叫——这是借代修辞手法,我也愿意在进退中尝试。J需要的是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推力、足够优秀的人。
“你说啥”的故事不太有正能量,但胜在真实,且离身处华文教育中心的我们足够近。蛇年来到,不是龙,却有龙的影子,我借这份得来不易的喜气,希望不再听到“你说啥”,而是热闹的〈你说蛇〉。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