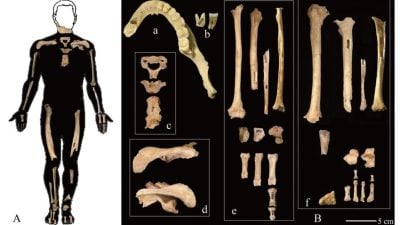雨林听爵——西必洛爵士音乐节/王晋恒(双溪大年)



“让我们彻夜狂欢,直到西必洛的人猿赶我们回家!”长得有点像本地作家许友彬,面色红润的主办人振臂一呼,宣告西必洛爵士音乐节(Sepilok Jazz Festival)正式开幕。不知道百年以前,人称“爵士第一人”的Buddy Bolden是否可以预见,这个以非洲音乐为DNA,糅合拉格泰姆(Ragtime)、压音和蓝调,意图与白人华尔兹分庭抗礼的乐种,竟然抵达世界另一端的婆罗洲雨林。
乐评人菲利普·拉金形容爵士乐为“20世纪上半叶对所有国家、所有有头有脑的人平等地开口的不可思议的暗语”。然而,时间过于久远,我难以想像爵士乐在美国遍地生花,最后在全球蔚为大观的历史进程。当广告板昭示作为雨林研究中心的西必洛即将搭起舞台,迎接几组来自不同区域的爵士乐团,我首先好奇的,更多是野性、自然、莽苍的雨林,究竟要如何与走过舞厅、酒吧、剧院,变化多端的爵士乐产生联觉效应。
ADVERTISEMENT
山打根原本就是一个很爵士的城市,始终维持一贯随性,慢半拍的调性。音乐节的检票过程稍有疏漏,队伍越排越长,却不见有人抱怨。检票员临时想出解决方案,问题最终都会很神奇的,迎刃而解。会场内的椅子不成齐整行列,主办方默许听众拉着椅子径自围成小圈圈,几群人就这样分布会场四周。大家随心而为,维持着不必言宣的秩序。
暖场表演环节,年轻面孔轮流上台,经主持人介绍,方知他们不过中学生,虽然业余,却展现颇高的音乐素养。
始于黑人音乐的爵士强调重复,主持人邀请每个乐团派出代表,临时凑合成一个“爵士小乐队”(combo),萨克斯风、吉他、键盘、贝斯轮流来一次即兴(improvisation)。学生们先是稍显犹豫,却也能随机应变,渐入佳境。
突然明白为何音乐节售卖“2日通票”,因为强调现场感,享乐就在此时的爵士乐,没有一场表演是重复的,每个细微的变奏都是那场表演殊异的印记。接下来两个小时,一场又一场无懈可击的爵士演奏中,我第一次听懂村上春树所形容的“非得聆听现场演奏不可”、“需要观众以肉眼观察每个音符的浮动”、“切身感受他呼吸节奏后,才听得出价值的、内省式的”这种音乐。
【沙巴入阵曲】
MBTI大行其道的时代,如果要为沙巴人的性格划出一个粗浅印象,我想大概会是ESFP——外向、热情、务实、灵活。一首〈Tinggi-Tinggi Gunung Kinabalu〉前奏一响,听众席的沙巴人就像上了发条,开始鼓噪,呼朋唤友:“走啦,一起上啦!”
舞台前方的空地成为公共舞池,谁想上去跳舞都无任欢迎。卡达山舞者身穿全黑传统服装,领口的亮片反射璀璨光芒,双臂延展,手掌跟着节奏向上拨动,仿若一只一只自由的黑鸟。据说这个舞团曾获某个国际舞蹈艺术奖,常常远赴欧洲与各地舞者交流。
爵士音乐包容性极高
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越道地的,越国际——贴近草根的文化,很多时候反而要上到国际舞台才能回过头被本地人看见。刚抵山打根,总是抱怨这里是文化沙漠,相比起游客较多,更加繁荣的亚庇,山打根较难见到文化表演。然而,这个卧虎藏龙的山打根舞团向我证明,人只有在一个地方久待,才有资格稍作评论。
众人在相同的律动中起舞,从小听到大,近乎“第二州歌”的〈Tinggi-Tinggi Gunung Kinabalu〉是沙巴人心心相印的媒介。这个地方活成了马来西亚(甚至是整个大同世界)该有的样子——每个族群都保留其独有身分与特色,与世界交朋友时就尽情挥洒,同时欢迎每个人加入,谁都是其中一分子。多元即是这块土地最强的软实力。那个当下,我竟然鼻头一酸,眼泛泪光。
紧随传统舞之后上台的是沙巴本土乐团LeLucky。牛仔外套,内衬黑色背心的双主唱要求观众站起来随音乐起舞。给我摇摆,其余免谈!曾在林佚的文章中读到,有些旧时的中国学者批评跟随爵士乐起舞的风气——“就像神经质的痉挛”——这评价虽偏激,放在眼下的纵情与尽兴,倒也挺说明情况。
LeLucky为配合主题而改编的歌加入大量blues note却不让人感到一丝忧郁,间中还大玩起爵士的“调动与回应”(call and response),时而用口技模仿唐老鸭演绎怪诞滑音,时而指挥听众应和演唱。知了高频且持续的鸣叫成为背景伴奏,观众席偶然闯入稀奇的蝴蝶与蟋蟀,恰似一首爵士乐当中,那个美丽的错音。现场感染力极强,整座雨林为之舞动。
【来自槟城的匠人爵士】
LeLucky的恣意癫狂之后,我为下一组表演捏把冷汗。来自槟城的爵士乐团Tonal Alchemy开场即冷场,主唱不及LeLucky双主唱幽默,键盘手兼团长更严厉要求技术组不要喷干冰,场面一度尴尬。
然而,就在乐手彼此使了眼色,表演正式开始之后,我见证了这组乐团如何仅凭高超的音乐技术,没有一丝紊乱的紧密配合,逐渐炒热现场冷淡的气氛。音色剽悍的女主唱、节奏迅猛打法灵活的鼓手、最重要的还有方才训斥技术组的白发团长,他的指尖飞快起舞,切分音、减和弦、八度跳跃,以及种种语言无法穷尽的技法,简直就是一场落在雨林的七色雨,滴在观众空白的心灵画布,至终完成一幅印象派大作。
It’s all about Jazz.
相对于LeLucky流行意味较浓的表演,Tonal Alchemy每一首歌都有jazzy touch,早已深入人心的歌曲来到他们手中,都会被爵士这个乐种收服,以致听众遗忘了原曲的风格。他们的表演没有狂欢舞池,走的是不同的表演路径与表现手法,引领听众抵达同样陶醉忘我之境。我们在二四拍掐指、点头,节奏不断加速,像一阵越刮越紧的风,热烈得令人惊讶。听众席上难掩激情,过瘾的欢呼声此起彼落,让我想到Eric Clapton在MTV Unplugged演奏〈Layla〉即兴时,因为颗粒分明的弹奏,那一声被收音器收录到音轨里的,观众情难自禁的“Whoo!”。
这组乐团就像那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传统匠人,熟知规则,打破规则,不追求明星排场,只想退一步专心演奏,所以获得全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standing ovation。
【和鸣与相融】
酒杯降临。夜色中
唯一清醒的纸镇
——陈子谦〈夜歌——给Fabien Wong〉
音乐节的酒水畅饮,可以喝的举杯互敬,微醺听爵士;不能喝的则尊重对方,心中修行不会因此动摇。所以才说,这里活成了马来西亚该有的样子。或许也可以换句话说,马来西亚人民的相处,也应该多一点jazzy touch。就像爵士乐的精髓“多重节奏”(polyrhythm)——不同声部不同节奏,皆在同一首歌中起伏变化。
著名爵士乐手Gerald Clayton说过:“许多事物都有内部联系,即使他们表面上各自存在。”爵士音乐因其极高的包容性,成为一个随着时间而丰富起来的乐种,落地拉丁,即衍生出bossa nova 、cha-cha、mambo……
那一个舞池中,有专为看人猿远道而来的阿根廷与哥伦比亚人。是次西必洛爵士音乐节成为他们旅途的惊喜变奏。于是澳大利亚人声合唱团SOULCUTZ不知事先安排,抑或是即席插入,为他们呈献了拉丁风情的〈Sway〉:“When marimba rhythms 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高个子洋汉发现自己已成全场焦点,所以哪怕四肢不协调,还是使出毕生所学的有限舞技,用力扭动,身体越扭越弯,整个后背几乎要触地。
毫不害臊的高个子开了个头,抛出的砖引来更多的玉,更多人接着加入其中。白衣白帽白裤子的主唱风度翩翩走向席间,邀请身着高贵礼服的女士上来共舞。女士先是一阵婉拒,最后还是应允,一旦上台,无论男女都要忘情投入。影子凌乱,一夜狂欢。
进而想起爵士是曾经打破种族区隔现象的混血音乐。Nina Simone说过:“爵士是白人对黑人音乐的用语。我说我的音乐是黑人古典音乐。”剖开爵士乐的内核,自然无法对那一段沉痛的历史视而不见,那原是丧葬之曲,刻录着多少贫穷、不公与生命挣扎的记忆。然而,虽然时代多变,有一种爵士精神却是亘古不变的,那即是她的有容乃大,对爱、对自由、对热忱、对理想、对美好世界的普世追求。
适逢九月天,SOULCUTZ 选唱了Earth, Wind & Fire的〈September〉作为结尾——
Hey, hey, hey
Ba-dee-ya, say, do you remember?
Ba-dee-ya, dancin’ in September
Ba-dee-ya, never was a cloudy day
Yes, I will remember.
记得那一夜人猿与我共舞。
记得那一夜雨林的迷醉与癫狂。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