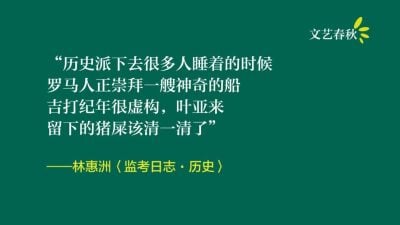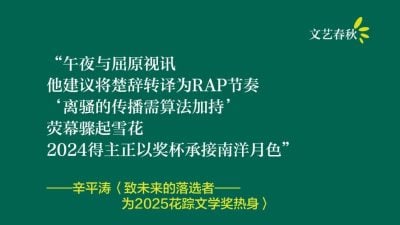阿嫲的沙漏岁月/林俐俐(万津)



举家迁往新居后,有六七个年头,我与阿嫲同房,她睡单人床,我睡地板。阿嫲起初手拄一根拐杖,行动自如,自己的事都鲜少假手于人,包括整理床铺、清洁痰桶、洗刷沐浴、用餐……直到后来跌倒骨折,康复后改用四脚拐杖,她才日渐需要依赖家人。而生命倒数的后期,阿嫲的精神状况让生命的旋律完全变了调。长寿的阿嫲活到93岁,忆起阿嫲人生最后的阶段,总有几个历历在目的场景萦绕脑海,挥之不去。
难忘那个天地变色的夜晚。
ADVERTISEMENT
客厅里,大人在闲聊,小孩嬉闹着。愉悦的氛围中,默不作声的阿嫲从沙发爬起,拄着四脚拐杖慢慢踱往后厅。突然,她停下脚步,喊了一声:“唛乱啦!”周遭的嘈杂声戛然而止,众人视线聚焦阿嫲。我走到阿嫲跟前想安抚她,怎知她睁大眼睛望着我,愕然道:“你……你的脸怎么会这样?鼻子做什么那么长?”听到阿嫲这么说,我们都大吃一惊。
那一刻开始,阿嫲仿佛在人生的轨道上岔开了另一条不归路,自此回不到正途。我们的日常亦犹如在波浪中颠簸的小船,再也平静不了。阿嫲生活在幻觉与现实之中,精神状况时好时坏。白天,我们不敢让她独处,家人外出工作或处理事情时,总有一人留下看顾她。
“蚂蚁”一度困扰着失智的阿嫲。“做么痰桶那么多蚂蚁?”阿嫲一面念叨,一面拿布把痰桶盖抹了又抹。无形的蚂蚁爬满她如厕的地方,擦拭了这儿,又爬到了那边,令她烦恼不已。跟她说没有蚂蚁是没用的,她只会怪嗔旁人否定她明明看见的东西,唯有配合着她用手随处扫一扫,敷衍着说蚂蚁没了,都扫掉了。
睡房的窗户挂着红黄翠绿花草图案的布帘。阿嫲仰卧在床上,指着眼前的一片“草地”,喜滋滋地跟我分享:“看,好多鸡啊!”她仿佛回到当年饲养家禽的时光。公鸡总在天蒙蒙亮时喔喔啼;毛绒绒圆萌可爱的小黄鸡唧唧叫着紧随在母鸡身后。阿嫲浑浊的眼珠荡漾着柔和的微光,松垮的嘴角勾起美丽的弧度。
有时候,阿嫲显得精神奕奕,她独个儿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与空气中的街坊聊得很起劲,时而发出笑声。我最怕阿嫲和她记忆中的冤家吵起架来。她瞪大眼睛,声嘶力竭地与眼前的对手争辩着,骂着。若家人前去劝解,她就激动地向来者投诉对方的不是。偶尔,她的虚拟世界发生了重大事故,令她焦虑无比,甚至急哭了,催我们迅速去处理她应付不了的事。或许那是阿嫲苦难岁月的影射吧——饭店里永远忙不完的活儿;火爆丈夫和倔强内弟没完没了的龃龉;两个大家庭三代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摩擦;还有两个儿子英年早逝的锥心之痛。失智,似乎没让她淡忘了这些,反将过去压抑在心底的委屈、怨气与悲恸都倾泻出来。火山口喷发的滚滚浓烟、炽热火焰与岩浆,谁阻止得了呢?
忍不住对阿嫲大吼
不知何时,阿嫲的四脚拐杖已换成了轮椅;有时,她自己推,更多的时候,家人帮忙推。再后来,她渐渐分不清白天夜晚,时间对她来说已没有任何意义。一天晚上,我在阿嫲的喃喃自语中,用两块小毛巾捂耳迷糊入睡。半夜,疲惫的灵魂被撞击声惊醒。昏暗中,只见轮椅在狭隘的空间挣扎着,轮椅上的人奋力趋前,试图打开上锁的房门。我起身捻亮了白炽灯,揉着沉重的眼皮,问阿嫲要去哪儿。
阿嫲神情紧张,语气急促地说道:“他们在后尾等我了,我要出去!”我没好气地把轮椅推回床边,说外面没人,叫她去睡觉。安顿好她,熄灯躺下没多久,耳边又闻声响。阿嫲又起床爬上了轮椅,转动着轮子要出去赴约。精神不济的我受不了一再的折磨,忍不住对阿嫲大吼:“我说没有就是没有!”阿嫲愣了一下,像是给我唤回了现实,旋即瞄了我一眼,别过头低语:“这么大声……”
后来的后来,阿嫲慢慢进入临终阶段,长时间卧床,只食少量液状食物。她渐渐失语,对来探望她的亲人不再有任何反应。我们察觉她呼气渐长,吸气渐短,心知她不久于人世。一天半夜,我起身趋前探视,看见阿嫲原本起伏的胸口没了动静,鼻孔探不到气息,身体尚有余温。阿嫲走了……
阿嫲离世多年,那段烙印在脑海里,不堪回首的长照回忆,包含了几许遗憾。当初怎么就当失智症是年纪老迈的必然现象,没想到寻求医疗援助;而资讯尚未普及的年代,也没能及时掌握相关的对策,日子就在折腾中度过。略堪告慰的是家人一直以来都陪伴侍奉在侧,阿嫲晚年并不孤单。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