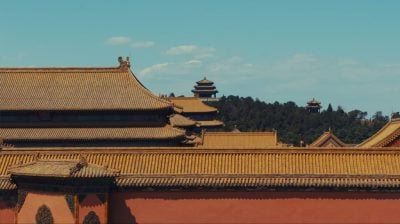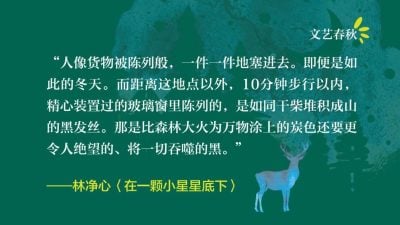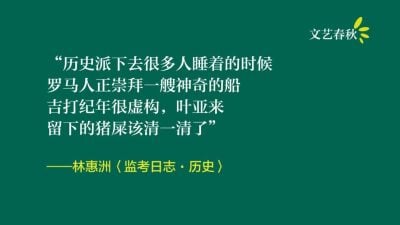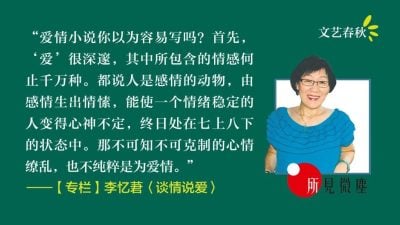【如意安详】她没有海誓山盟/何国忠



出自旧家庭,婚姻由长辈做主。16岁时,祖父将苏雪林许配给五金商人张余三次子张宝龄。二人后来在不同地方求学,迟迟没有完婚。1925年夏天她从法国回老家岭下,为完成病重母亲心愿,她同意举行婚礼。
张余三原籍江西南昌,因经商迁至上海,与寄居上海的苏雪林祖父和父亲相识。张余三受过旧式教育,从商后习英文,会话书写皆达实用水平。他在世时爱读媳妇著作,以她为荣,待她“似公主一样”。他有三子一女,对孩子前途毫无规划,除了次子,都只进私塾,未入正规学校。次子被安排接受新式教育,无非为了和未来媳妇水平匹配。一家男女除了次子,工作后入不敷出,两老贴钱,日夕责骂,家里气氛不睦。
ADVERTISEMENT
张宝龄思想保守。他肄业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修造船专业,数十年在上海江南造船厂服务。她在《浮生九四》说他有不少优点,人聪明,中英文俱佳,一手好书法。他为人正派,做事负责,上司视他为人才,器重他。他教过书,学生欣赏。朋友不多,但贵在忠实。为人虽木讷,但是“高兴起来,也能说几句诙谐话,引人嗢噱”。
婚前没有来往,她在法国留学最后一年二人通信,内容平淡,没有浪漫语言。新婚不久她写散文〈绿天〉和〈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以及剧本〈玫瑰与春〉,人物被美化诗化。这是她想像的“婚姻史”,她也向往爱情。
张宝龄同样期待美满家庭,一个月婚假,他掌握岭下方言。他说夫妇间用家乡话,才有情趣可言。闲着无聊,她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教书,又在东吴大学兼课,他周末从上海到苏州,后来请长假,在东吴大学教书。一年后,他回江南造船厂复职,她随他去上海,到沪江大学教书。1930年,她受邀到安徽大学工作,一年后转到武汉大学,他始终以上海为家,夫妻关系有名无实。抗战末期他应聘至迁校四川的武大工学院,二人又同住一年,但不同寝。
婚姻成了不堪的梦
值得回忆日子可数,彼此不能接纳对方弱点,只有在苏州天赐庄那一年生活“算得甜蜜”。他自小被胃病折磨,病发时脾气暴躁。她坦言二人结合是“一世孽缘”,她说他是大男人主义者:“妻子者顶好是个仅识之无的乡下女人,容貌美丑在所不计,只须三从四德,勤俭持家,每月尽心竭力,以侍奉他为事”。她出身于一个亲权压制极重的家庭,金色童年被铸成冷硬白铁,不料婚姻成了另一场不堪的梦。“真是命也。”她感叹。
她有文名,感情生活经常被人“乱猜乱写”。二战结束后,武大回迁,他回上海和失散8年父母团聚,不去武汉。1949年2月她到上海避难,住夫家,3个月后她赴香港工作,二人自此天各一方,没有再见。
1961年她从张家子侄信中得知他晚年住北京,一日侄妇辈为他织毛线短衫,线不足,见箱中有羊毛围巾,颜色相同,想拆开用。他摇手阻止,说是妻子物品,留作纪念。突然掉泪,懊恼过去未尽夫责,对她过分,“现在追悔莫及。”说完没几天,便去世了。
侄辈的信让她内疚,并反省自己:“可怜我虽会弄弄笔头,家事半点不会。”她敬仰母亲,可惜德行和才干未得遗传,“我至今还不能入厨煎荷包蛋、做一碗青菜豆腐汤。洗衣只能洗手巾和袜子,又何能做他半女仆、半妻子的伴侣。”她说他转对她冷淡的另外原因是不满她偏向娘家,协助姐嫂。她说自己赚钱,不靠夫家,二人为此争吵,“夫妻感情之坏,以此为之根源。”
《浮生九四》说因为这些摩擦:“叫张宝龄孤栖一世,不能享他理想中的家庭幸福,也实觉对不住他。”二人无子女,《浮生九四》提不离婚理由:“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且她也不可能再婚,离婚与否不差,她说遭受打击,“对爱情倒尽胃口,从此再也不想谈这两个字。”
1966年2月1日,在南洋大学教书时她往理发店,店中两位女生读过她作品,格外用心烫发,她们只收半价,她拒绝,但内心异常感动,日记里记下她们名字。她著书四十多本,在学界声名卓著,尤以《楚辞》研究自成一家之言,其文学创作亦同样引人瞩目。
“百事翻从缺陷好,只容心里贮秾春。”这是她集龚自珍《己亥杂诗》诗句所得。接受万事的缺憾不过是顺从天意,只要心里装着希望和春意,外在的不完美也就轻易随风飘散。1990年11月1日93岁时她在日记自我调侃:“世尚多不婚者,遇人不淑者,我有文学、学术自慰,何必婚姻?”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