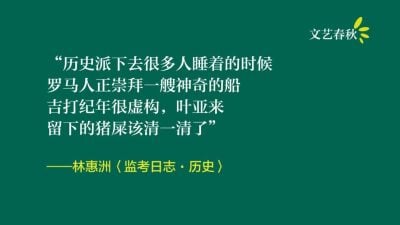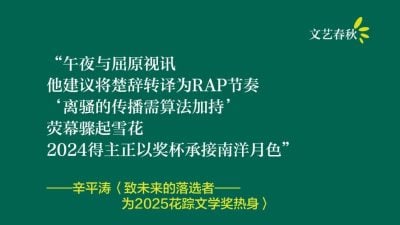福隆港观鸟手札(上)/牛油小生



2025年5月26-28日
20-26°c 阴天
平均海拔1200公尺
【手札 #01】
ADVERTISEMENT
托一对怡保赏鸟夫妻档的福,在寻找福隆港明星鸟——红头咬鹃(red-headed trogon)的时候,我们在Bishop Trail步道入口悬崖边的一株小植物里发现一对爪哇红翅鵙鹛(white-browed shrike-babbler)雏鸟和亲鸟。
雏鸟一动也不动待在枝桠里,亲鸟捕到虫子先在对面树上视察附近有没有危险再回到孩子身旁,举凡育雏的亲鸟都会这样做,而赏鸟人循此规律找到观察育雏的最佳时机。

机会难得,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才能让观察更趋近于真实,任何介入都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可是不观察又无法理解——两难的命题。不是有个笑话说,每个印地安人的家里都住着一位人类学家吗?
怡保大叔自我介绍叫Leong,10年来到福隆港观鸟上百次了,熟门熟路。他太太抱着一只可爱的博美犬。见我是J开头车牌,惊讶我大老远从半岛南部过来,但其实他们从怡保过来也不算太近。爱鸟人士,哪有怕远的?就是要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啊。
夫妻俩以广东话沟通,对我则很自然讲起英语。无论新马,观鸟人士之间第一语言往往是英语,毕竟这是跨族群的兴趣,英语是最大公约数,但追溯历史,博物学最初也是西方随殖民扩张传播至此,留下最早的系统化记录。而我们所处的这座山,之所以会成为避暑胜地,也与锡矿开采的兴衰、英殖民者一战后在热带寻找高原开辟复原疗伤的hill station有关。在我们这块多语的土地上,单从一个物种的中英马来语(还有印尼语)俗称命名,就能看出许多好玩的文化性格差异,一如这对爪哇红翅鵙鹛,中文名字强调了地方与外型,英文俗名除了形容外表,还暗示了它具有伯劳(shrike)的凶猛与鹛(babbler)的好歌喉,马来名称burung rimba cekop belalang透露其林鸟的性质外,直译还有“林鸟蝗莺”的意思。如果我能懂一点淡米尔语或梵语,肯定会比较出更有意思的东西。

Leong播放红头咬鹃鸣唱录音的时候,没有经验的我在山路上徘徊,有时走远了不知道是真的有咬鹃在叫抑或是听到了录音。拍鸟人常用录音与食物引诱特定物种,但这可能改变物种在野外生存的能力,毕竟每次鸣唱都要耗费鸟儿不少能量,远远飞过来还找不到伴,见到的是拿着相机的人类,不是很滑稽很悲伤吗?
蜿蜒山路两边的雨林藏着非常多娇小的鸣鸟,像是成群出没的棕胸雅鹛(buff-breasted babbler)、山雀鹛(mountain fulvetta),成双成对的黑头穗鹛(grey-throated babbler),与喜欢藏在树冠里的栗头鹟鹛(chestnut-crowned warbler)——在寻找某个明星物种的途中,总会意外邂逅许多不同物种。
【手札 #02】
福隆港平均海拔一千二百多米,山上物种与平地雨林里的大不同,只生活在高海拔的文背捕蛛鸟(streaked spiderhunter)在山里就很常见,在高山花圃中采蜜,因为爱吃芭蕉,又被称作芭蕉鸟,叫声很响,很容易循声发现它们的踪迹。长嘴又吃花蜜,不少人第一反应“那是不是蜂鸟?”但其实蜂鸟属于中南美洲独有的物种,在东南亚,吃花蜜的鸟儿有花蜜鸟(又称太阳鸟)和捕蛛鸟,而捕蛛鸟也捕蜘蛛来吃。会直接联想蜂鸟,许是大家常看的生态纪录片,总爱把蜂鸟塑造成看板物种,久而久之形成的印象,就像我们对各种创作的认识,总是先看外国的经典、时下流行的外国电影或小说,才在不经意(比如不小心读本地的中文系)的情况下,接触到一点本地创作。
城市鸟几乎都不会上山来,一只家乌鸦(house crow)、爪哇八哥(Javan myna)、家八哥(house myna)都没有,亚洲辉椋鸟(Asian glossy starling)倒是常出现在高高树木的枝桠上,但体型又比山下的要肥壮一点。不过在高尔夫球场边我还是见到了几只白眉黄臀鹎(yellow-vented bulbul),这种城市公园鸟出现在山上,可能是丛林颓败的迹象。
而我在哥打丁宜班底森林偶然才能遇见的古铜色卷尾(bronzed drongo),在福隆港山林里特别活跃,观鸟两日就见到不下七八只,还会模仿其他鸟类鸣唱,对观鸟初学者来说是极大的迷乱,还以为出现了什么别物种,肾上腺素七上八下 。
【手札 #03】
最终是在Silver park公寓外的一棵大树上找到红头咬鹃。老经验Leong持续播放鸟鸣录音,守株待兔,而我沿山路乱逛,遇到也按捺不住出去寻找明星鸟的Leong太。
当“呜、呜、呜、呜”的真实咬鹃歌声越来越近,一只红身白尾的大鸟越过山路窜上Silver Park的大树,就从我的眼前掠过,赶紧追到公寓外,大群燕子聒噪,在我头顶飞来飞去,抬头分辨不出属于哪一种燕子,低头偶有松鼠逃避我的目光,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更高处又传来咬鹃的歌声,才终于看见它,勉强用长镜头捕捉它的背影,那鲜红色的头扭过来,像是要告诉我它是一只雄鸟。静静观察一阵,才知道它鸣唱的时候会低下头,连同整个身体,尤其屁股都在发力,每一声都要震颤,长尾巴随着“呜、呜、呜、呜”连续顿音翘翘板似的摆动——鸣唱入木三分才能在这山里回响吧?难怪声乐老师指导我们合唱团的时候一直提醒,歌唱是全身运动,你必须善用全身上下的肌肉与腔体,才能发出具有穿透力的歌声,如刚出生婴孩的啼哭,一种赤子、原始的声音。

隔天我在山雾里发现一只金头缝叶莺(mountain tailorbird),大概拇指头大小的鸟儿,发出短笛似的高音旋律,乐句由几个半音阶升降组合,田园诗般好听极了,穿透迷雾,让我想起两个月前与斐在日本伊豆高原,清早窗外传来如歌的日本树莺鸣唱(Japanese bush warbler)——先是一个较低的长音,接着几个急促的百转高音,错落,悠扬。自古多少作曲家都曾借用鸟鸣创作,从韦瓦尔第《四季》、贝多芬《第六号交响曲(田园)》、大流士《孟春初闻杜鹃啼》到劳塔瓦拉《北极之歌》,欧洲常见的乌鸫(blackbird)、夜莺(common nightingale)、大杜鹃(common cuckoo)都是音乐缪思。法国作曲家梅西安更是深深为鸟鸣着迷,写过《乌鸫》《百鸟苏醒》《鸟类图志》,简直就是音乐界第一鸟控。二战时期,梅西安被关入Stalag 8-A战俘营,写下《时间终结四重奏》,作品的起点是第三乐章〈群鸟的深渊〉,沉静凄美的单簧管独奏,他后来写道:“深渊(abyss)是时间的悲哀与疲惫。鸟声则是时间的反面,它们是我们对光明、星星、彩虹和欢快歌声的渴望。”
鸟声是时间的反面——反刍这句话,是不是因为每一只鸟的鸣唱,每一声啼,都记忆了一个物种几百万乃至上亿年的演化史?我们因而有机会听见某种远古的声音空间,一如遥望星空,每一盏星光都是千万光年的历史距离,一个星系的存在证明。
新马物种繁盛,鸟鸣交响,个人特别喜欢四声杜鹃(Indian cuckoo)“ti ti dol la”的四声旋律与节奏,最近每遇作曲家朋友,都会诱惑他们写首本地鸟鸣大合唱作品,或舞曲,一定很好玩,也一定会跟欧洲中心那些作品不一样。
【手札 #04】
斐在丹绒马林就有点喉咙不舒服,依大讲座结束,我们到新古毛过了一夜,集装箱组成的Sarang by the Brook旅舍很有风味,窝居的概念,只是夜里壁虎声扰得斐无法安眠。旅舍主人Chen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10年前选定这个距离吉隆坡一小时路程的地方开展新事业,离开城市喧嚣,经营旅舍也带团走山玩激流。他养了五六只猫,都很愿意亲近人,我一蹲下来,小猫便躺下翻身露出肚皮,十足的信任。看见猫,斐也精神了一点,但有只小猫太缠人,跟着斐到房里,躲到床底下,最后得我出手把它抱出去。
在新古毛没太多时间观察周遭生态,但集装箱旅舍就在山脚下,旁边有溪流,吃早餐的时候,目及一株大树上有头马来亚巨松鼠(tupai kerawak hitam)跳跃,几只文喉鹎(striped-throated bulbul)一直在旅舍范围内发出鹎族招牌的类似电台转频的歌声,越过溪流远处的枯树上还出现了两只黑枕黄鹎(black-crested bulbul)和一只小须凤头雨燕(whiskered treeswift)。
不过我也观察到几只黑头鹎(black-headed bulbul)在嬉耍,它们喜欢生活在森林边陲或次生林,如果数量多起来,可被视为林野自然状态颓败的象征。犹记第一次在新山附近至达城的公园里见到黑头鹎时的振奋,但在认识它们与森林的关系后,每次相遇,我都难免忧心。这算不算是庸人自扰?(明日续完)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