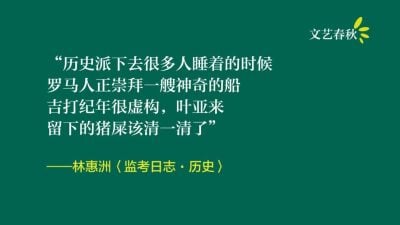张温怡/茧房




村口小径有一间老屋,具体来说那不是像样的屋子,只是小巧的木房间。我对老妇的印象停留在那里。
傍晚烈阳还睡,骑着脚踏车来回玩耍,常将老妇的单人房子作为定点。老妇饲养一只大狗,听说它在村子流浪十余年,后来便守在她家里。每日按餐喂食。她开着小木门围篱(那时还有围篱)大狗就睡在那里,邀请我进入她家与狗玩耍。伸手触摸狗的头,软软的,暖色系的毛发如阳光温和。大狗摇摇尾巴,伏下身体缓缓坐下让我摸头。老妇彼时已出现瘫痪症状,她的房子只有卧室的大小,里边有一张床褥和被子,小小竹藤两格抽屉,上面摆放餐具和杯子。床头还有包装狗粮,伸手便可触及的距离。
ADVERTISEMENT
昏暗的房间并没有多少人经过。偶尔,我会看见一个瘦小的印尼工人,提着打包的塑料袋装着软糯的食物给老妇。她孱弱地接过食物,糊状的米饭和淡黄色的汁水像极她无色无味的生活。我看着她吃东西时无神的模样,垂头对着木质地板,有时盘坐在床头看向窗外。
阳光照进房间时让我产生某种错觉。
眼前的老妇化为一株枯树。她就这样等待某种生命进来房间,望着窗外偶尔经过的摩托车和狗儿,或是火鸡追着路过的小孩把这里割成两个世界。
每当我经过这里望着老妇,总误以为她是一道无声的风景,别的世界派来观察我们一举一动的监视者。
我也无意走入这道风景。像是一场电影,我从老妇身旁望着她孤独地吃着粥食,然后看见碗里的食物残余,被印尼工人收拾后都丢到屋后的沟渠。流浪狗或蜥蜴在附近觅食,而它们也误入老妇的片场,吃着老妇剩余的食物充饥。那时的我还没上幼儿园,记得有这么一个老妇,还有一些客串的小演员、物件和不知名的东西。
每次老妇就静静看着我和狗,有时低声问话:“吃饱了吗?”“刚放学吗?”“功课做完了?”我点头答应,对话仅有简单的语助词。老妇银发铺头,小眼合上。下午明明很热闹,她卧在客厅,睁眼的时候露出一双灰白的眼眸,听不见周遭的背景声。起先,老妇话不多,看着她犹如微小变化的默剧电影,后来进化成静态的照片,周围的声音熙熙攘攘,唯独她依旧安静地躺在残破的木房,连同床铺缩成一个小小的盒子。
她卧在客厅一动不动的,看不见我,也听不见声音。盒子消失以后,周围的人不再提起枯木般的她。小小的我,不知道死为何物,以为所有像老树的生命都只是迁移至适合居住的地方。
而我,还有房间,从那时就定下某种奇怪的连接。
房间是随心变幻大小的空间。
一个人住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房间。或大或小,一张睡床或地铺草席也能构成房间。
时光拉扯影子和脊椎,毕业后我如常寻找一个小巧的房间。做一个除了呼吸、睡觉、吃饭的生物外,还有记得自己是一个活着的普通人,窝在一间10平方大的房间。床喂养我的梦境,躺下去,很久很久都无法从梦中醒来。
有时梦见自己变成动物,或被动物追赶,困在一个幽闭无比的房间。
一次,我梦见自己变成孕妇,挺着硕大的肚皮从荒野青草,被一头水牛追赶,逃进一间房间。房间很暗,伴随着雾水,肚子一下子消瘦,诞生两条半透明的幼鱼。
鱼在房间游泳,半透明蝌蚪状的身体,眼珠忽转向我,摆动尾巴慢慢往前游。我恐惧地望着鱼,伸手却摸不着它们的身体。房间变成透明的玻璃,隔着我。水中有两条初生的观赏鱼,而我在透明的鱼缸外注视它们的新房。
梦醒,床湿成一片。窗外有只傻鸽子拍打翅膀,看着我做梦,清醒。
很像去了远方,而又回到原点。我后来很少社交,上班后和同事之间毫无话题,平日只忙工作,回家就休息。偶尔,我会回家看看家人,还有轻微失智的爸爸。
爸爸自我念大学的时候,很少说话。后来搬到新家,有了自己的房间,每天他都在房间里睡觉,看视频,对着小小的手机屏幕唱歌。除了睡觉吃饭,一直都在唱歌。
房间里的爸爸什么也听不见。
爸爸吃饭,爸爸。
我叫了好几声。爸爸没理我。
音乐停止后,没人知道爸爸在房间里做什么。客厅里到处都能看见女孩子的头发。褐色、红色、黑色……都是长发,一些是我掉的。发丝之间缠成一圈又一圈,有一根小指的厚度。有的缠住灰尘。沙发没有位子,坐的都是堆积的衣服。有人睡在衣服上,当枕头。
每天半夜,饭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讨论爸爸,讨论每日重样的晚餐。这星期番茄鸡、下星期绿豆粥、再来番茄鸡、绿豆粥……
家里只剩下房间可以安静下来。只有房间地板没有灰尘,也只有房间可以睡觉,可以安静。
爸爸或许是自愿安静,变成一只薄薄的虫子,未脱壳,背着一个沉重的外壳活在这里。
新住处的墙上到处都是衣虫。它们贴在墙上,一动也不动。
爸爸,可以下车咯。
爸爸看着我好久,眼神呆滞。向左,向右了,他仍在左。
爸爸背着沉重的壳活在这里。用餐时,他盯着眼前的食物发呆,板着脸,没有表情。咽了几口饭,菜只吃了一些,然后离开餐桌。
走走,吃饱了就走走。
而他只敢近距离走。望着爸爸,那时已经是晚上,路灯昏黄打在他的半张脸,我看见那双眼,从那一刻清楚看见,眼睛里边装满水,有鱼缓缓游动。
爸爸用那双半透明的眼珠回望我。
后来的我真的害怕凝视爸爸的脸。曾经的巨人爸爸从我的梦里预示中游走,眼里装满水。我不敢再看。他背着很重的壳出现在我眼前,说很怕冷,去到哪里都想回家。回到房间,回到睡床。
而我看着他,薄薄的身躯,化作一只随时被风吹走的衣虫。到哪里都有自己的房间,听不见有人和他说话。重复几遍,他不明白。
他每天都在唱歌。
毕业之后和家人住一段时日。沙发的缝隙偶有唾液,夹杂着痰。爸爸口干了,就吐痰,然后唱歌。有点累了,还是回房间吧。
半夜两点,家人都会收到爸爸的早安图。
早安爸爸。
(我们后续需要很多的夜来说早安)
相关文章:
张温怡/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张温怡/雨童说(上)
张温怡/雨童说(下)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