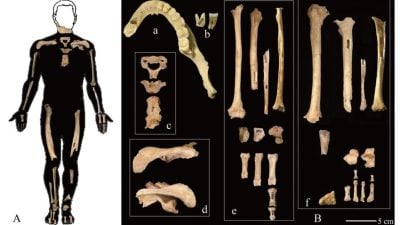毛紫蒨/一屋两家



在厨具的撞击声中,我从朦胧的睡意恢复意识。我的眼睛依然轻合,依稀听着楼下的动静。一把清亮、彻底而有力的刀声在木砧板上起起落落,这是巴冷刀独有的歌喉,阿嫲大概在剁猪肉。锅盖敲在灶台,水该烧开了,刚切好的肉碎下锅,很快就能闻到猪肉汤的鲜味。片刻后,阿嫲走出厨房,喊还在赖床的爷爷吃早饭,阿爷只隔着房门回应“哦哦”,却迟迟不闻房门打开的声音。若是等到早饭都上桌了,爷爷还没出来,阿嫲便会大发牢骚,推门把爷爷拽出来,那动静能惊醒一屋子人。
闹钟却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响了,睡意被逼退,身子仍懒懒地不想动。揉揉眼睛,略渐清醒后,发现房间四周都变了样,空气里也没了木质家具的霉味。是啊,爷爷和阿嫲都走了好久好久,楼下的那对老夫妻,该是房东夫妇。
ADVERTISEMENT
决定要搬进来之前,还是犹豫了几天。恰逢租约到期,适宜的地点都左看右看了一遍,不是房租太贵就是厕所太脏,或者“劏”得十分严重。对劏房的印象停留在《笼民》这部电影,虽说门关上后,就是一间普通的房,可心里多少有些抵触。努力工作,每个月还几百块的租金,只换来一间有门的笼子,实在不是滋味。近乎屈服之时,木门从内缓缓打开,宽敞明亮的客厅映入眼帘,门后的房东太太热情地招呼我和中介进屋。
屋子没有经过刻意的改造,透露出淳朴的气息。四面墙披着白漆,地板也是白色瓷砖,却打理得格外整洁,墙头角落都不见污垢。橱桌摆满了陈年旧照,男女老少的身影泛黄,笑意却恒久灿烂。尘封的钢琴上挂着几幅儿童照,那相中人如今应该比我还要大些。房东太太留意到我的目光,介绍道那都是她的子女儿孙,都搬到外头去了,屋里只有两老和其他一位女租客。领我去看了放租的空房时,房东太太介绍着条规和设施,我却被那温馨的黄色暗花窗帘吸引,她的声音遂成过耳的絮语。这间房和大厅的格调一样,纯净的白,没有多余的装潢。一张小床在房中央,旁边是日风木柜,床前有张木桌。就是这样的单调的背景,挂着鲜亮的黄色窗帘,阳光微微照进,隐约可见印在帘上的暗花,这间房,是曾被谁用心住过的。
于是当天付了定金,原本的租约到期后,就搬了进来。跟别人说起我跟房东一起住,大伙儿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夸我“有勇气”。需知在外工作,回到租屋疲累不已,常常袜子乱扔衣服乱丢,杯碗不洗甚至懒得锁门,但跟屋主共住,不利落些便少不了被念叨麻烦。
房东跟租客同住一屋,这气氛无疑尴尬且诡异。同一屋檐下,都是一家人,在此处,就行不通。作为租客,我想要的,就是一处安静的防空洞,一日疲惫,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洗洗睡,放空余下的时间。第一天搬进来,我没跟房东太太有太多寒暄,只打声招呼,便开始把行李搬进房里整理。房东太太没有走近,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我,不时提高嗓门问有什么需要帮忙,或在我把碗具搬到厨房时,介绍她的各种炊具,我敷衍地点头,到底我也只是需要一个放得下饭锅的小洞。
租屋的厨房让我想起老屋的露天灶房,那里原本大概是个庭院,临时搭几块铁片就成了阿嫲专属的战场,一日三餐煎炸爆炒,煮出让每个家人都温饱的美味佳肴。记忆中,灶头一直烧着旺火,做饭时煲汤,不做饭时烧水,入夜后那火才会熄灭。灶台旁的小桌堆满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想添些什么时还要一罐一罐抽出来看标签,阿嫲却熟悉得随手取出一个罐子,就往锅中撒调味料。换了时空地点,这里的厨房不似老屋的潮湿破旧,反而整洁明亮,在这现代化的背景下,灶头该是电炉,却燃着火光,笨重的水煲在上头低声打鼾。灶台的对面是洗衣机和一张小桌,桌上也蹲满了瓶罐,各种品牌的酱茶乖巧地等待主人挑选。
房东太太说过,老爷子中了风,行动不便,鲜少出房。某天下班后,进屋就见上身赤裸,坐在轮椅上的老爷子。老爷子见有人回来,口齿不清地说着“放学了吗”、“学校远不远啊”、“你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啊”。好久好久以前,回到老屋看见阿嫲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坐在藤椅上的阿嫲,她会热情地唤我们进屋,然后起身去找零食茶水。
我只略略回应,便到厨房准备晚餐。老爷子以为我不熟悉环境,又在喃喃地念“你在找什么啊”、“需要老婆子帮你找吗”,见我不应,又大声唤房东太太“那个女孩需要找东西,你快出来帮她找吧”。我赶紧出去安抚老爷子,不想惊扰正在小休的房东太太。老爷子一身沧桑,双眼却如孩童般清澈明亮,他并不像是看见一个比她孙子还小的女孩,而是看见邻家的姐姐,有点畏惧,却又好奇地想跟她玩。返老还童的老爷子身后,是数张受封勋衔、扬名立万、走红地毯的照片。如日中天的光景从身后擦过,浮华之后,财名散去,他只是一个想跟邻家姐姐玩的孩子。
相片中的他,可曾窥望过多年后的未来?偶尔关门在房中,也能听见房东太太厉声责骂老爷子,唤老爷子起来吃饭、唤老爷子去洗澡、唤老爷子赶紧换衣服上车。老爷子则大发孩子脾气,嫌饭菜不好吃,或纯粹等待谁拿着大红糖果来哄。相守到白头,该是多么浪漫的画面,来到现实却如此苍白。房东太太七十高龄,还能煞有精神走几步已是不易,仍然要撑起身子骨,照料当初意气风发,如今变成6岁顽童的丈夫。一天到头,相伴是有,房门之后是感恩欣慰,还是无奈叹息,则不得而知。
在这个地段拥有一间这样的房子,还用廉宜的价格出租房间,儿女偶尔驾着豪车前来探望,房东夫妇不是缺钱的。决定租房后,和房东太太提起租约的事,她张口便是别搞什么租约印花税,你付定金我交钥匙,你就挑个日子搬进来吧,提前知会我就行。搬家当天带了大包大袋的杯碗刀锅,房东太太说厨房里看见的你都能用,最后除了一套用惯了的餐具,其他的也都退回家中了。
都说20岁是美好的年纪。自由自在地玩,自由自在地吃。拿着打零工赚的薪水和父母给的零用钱到处去玩,也因为多走动好消化,上至山珍海味,下至路边麻辣烫,都能毫无负担地吃。但20岁的美好远不止于此,享受当下的当儿,回到家也能看到精神奕奕的父母,老爸在屋里腾来翻去,修修灯泡又剪剪花草,老妈则在研究新食谱和缝纫技巧。打工人回到家后能躺着就躺着,睡醒后,总有热乎的饭菜在桌上静候。
大概所有人都希望一生年华,能停留在这个阶段,只是时间总是自顾自地往前走。是否有一天,我的父母也会丢失记忆、返老还童,而后不能自理,退化成最不堪的自己;是否有一天我也会离开双亲,越来越少回家探望,即便逗留也非常短暂;是否有一天我也会韶华尽退,变成老爷子那般模样;但若真的有那一天,不管是父母还是我,老了能安心在家相守照望,如此黄昏,不失美意。
只是美总要留白,就像房东太太等待儿女前来探望的日子。我与房东太太的晚餐时间相同,房东太太会提前煮好,我一下班,就能用厨房。她的烹饪风格简单,清蒸几样就能上菜;我更随意,菜肉丢进锅里,撒点盐就吃。我们端着各自的菜,一张桌吃着两家饭。很多年前桌子该是围满了人,热热闹闹地等齐人起筷,只是老爷子傍晚便入睡,房东太太再也没有可等之人。我低头吃着那碗不成气候的羹,房东太太则一如预期地找话来聊。见我并不热情搭理,她好似觉得说错什么,又转头低吟“我只是好奇问问,没什么的”,而后以刷手机缓解尴尬。
租客与房东,就像员工和老板,总得保持些距离,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房东太太偶尔会以佣人要来清洁为由,提前告知我她会开我房门的锁,然而还是露了馅——佣人没有来的日子,离开时锁上的房门,回来时是没锁的状态。房里的改变细微,但还是能够察觉,像搁在地上当抹布的衣服被挂了上来,在路中间的桶被推到角落,拉开的椅子归了位,倾覆的水杯被重置。房东太太大概每天都会到房里看一遍,对租客来说的窥视,于她不过是日常查看。
我即便知晓,却出乎意料地不怎么介意。印象中阿嫲总是在屋里腾来腾去,到家中的每间房摸摸看看,搬出脏衣服,折折被单,半天也就这么过去了。和朋友聊起家中老人时,大家的记忆总有那么一两个共性,比如窥看房间这一件事。或是因为腿脚不便,或是对外边的世界感到倦怠,老人大部分的时光都在屋里。和看报纸刷手机一样,阿嫲洞察窗外事的方式,就是观察家人房内的动静,谁谁谁又买了新电脑,谁谁谁的房间多了异性用品,即便从地上乱丢的脏衣服也能推测出这孩子昨晚去过哪里。
这是另一种沟通和默契。大人们总是念叨阿嫲不顾儿女的隐私,阿嫲只抱怨你们都不和我说话了,闷起来只能没事找事。彼时阿嫲可以做的当然很多,但她最想做的,还是了解儿女在外面的生活。久而久之,大人们发现锁上门阿嫲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又或是为自己对老母亲的冷漠感到一丝愧疚,便由着阿嫲去了。人长大了不似孩子一放学就向父母噼里啪啦讲述一天的经历,但父母却依旧沉溺于儿女眼里闪着亮光,认真而兴奋地告诉他们今天发掘了什么新世界。
衰老,是每个年龄层都需要面对的命题。房东太太把房间出租,大概也只是想聆听租客们的脚步声,设想他们在屋里的动静。有些隔着门板的嘻嘻哈哈,厨房洗碗的流水声,便能驱散一些屋里的寂寞。说到底,打工人也只是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放低道德底线,我对房东夫妇可以故作热情地回应,但也无需对自己的冷漠感到惭愧。她借外人仿拟儿女存在的痕迹,我以隐私交换廉宜房租,我们各取所需,一同在这宽敞明亮,却透着孤寂的屋檐下生活。
相关文章:
毛紫蒨/吃垃圾
毛紫蒨/驯兽
毛紫蒨/离不开的安全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