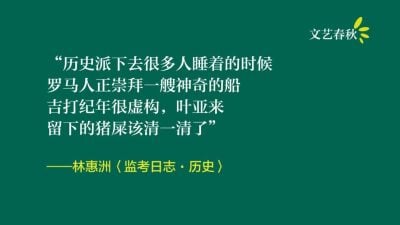阿恩/阿里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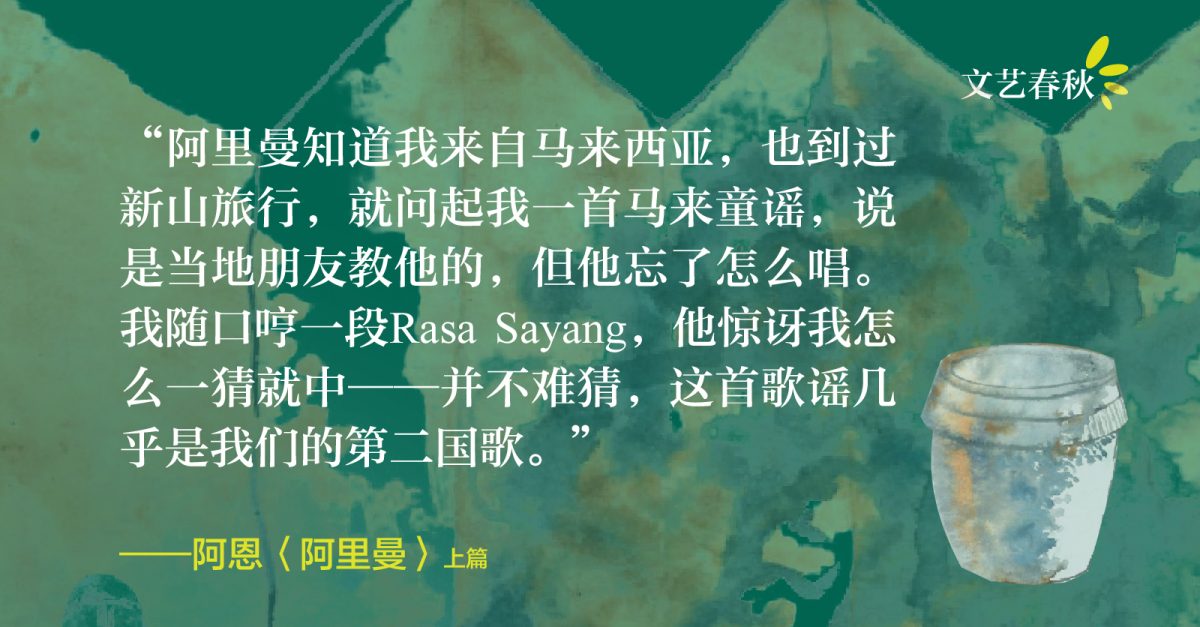 前年夏末,台北暑气仍盛,卡努台风徘徊不走,饱满的水气让晚风都是热的。是在这样湿闷的时节,我和研究所的同学随顾玉玲老师一同南下,往台湾最高海拔之地走去,到访位于八通关古道入口处的东埔一邻部落。这是一个布农族部落,二十几年前发生了一场临时工的职灾意外,族人向资方求偿不果,求助老师当时任职的工运组织。在漫长的抗争历程中,老师和部落的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许是这样的一个过往,让族人在农忙之余,还愿意接待我们这群研究生的到访。
前年夏末,台北暑气仍盛,卡努台风徘徊不走,饱满的水气让晚风都是热的。是在这样湿闷的时节,我和研究所的同学随顾玉玲老师一同南下,往台湾最高海拔之地走去,到访位于八通关古道入口处的东埔一邻部落。这是一个布农族部落,二十几年前发生了一场临时工的职灾意外,族人向资方求偿不果,求助老师当时任职的工运组织。在漫长的抗争历程中,老师和部落的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许是这样的一个过往,让族人在农忙之余,还愿意接待我们这群研究生的到访。
我便是在这趟五天四夜的田调行程中,结识了茶商阿里曼。
阿里曼和他的太太美秀姐,是老师为我们这小组安排的访问对象。在首次访谈结束的那个晚上,部落的晚祷之夜,我们在其中一位族人的家里共进晚餐。阿里曼知道我来自马来西亚,也到过新山旅行,就问起我一首马来童谣,说是当地朋友教他的,但他忘了怎么唱。我随口哼一段Rasa Sayang,他惊讶我怎么一猜就中——并不难猜,这首歌谣几乎是我们的第二国歌。虽说如此,这么多年以来,我也只记得副歌。应阿里曼的请求要献唱全曲,我还得把歌词及时谷歌出来。歌还没唱,阿里曼看着我手机屏幕里的马来歌词,说他知道布农语和马来语有一些相似的词语,但他族语不太流利,不太确定有哪一些。
ADVERTISEMENT
“1到10,我说布农语,你说马来语。”
我们开始了南岛语族的认亲环节。
阿里曼缓慢且用力,嘴型略微夸大的说出布农语的1,“Ta-sa”。
我回以马来语,“Sa-tu”。
“欸……不太一样馁。”
今晚下厨的大姐收拾好碗碟了,她从厨房探出头来,催促阿里曼赶快去跟晚祷的大家会合。阿里曼敷衍应和了一声,往下继续数。
他在伸直的食指旁边卷开中指,比作2,“Dusa”。
我说,“Dua。”
“有像,这个有像!”
我们来来回回,依序念出两个语言的数字,像是刚刚相认的远亲,互相对照家族成员的名字。
数到8的时候,阿里曼停了下来。他叫住正要前去晚祷的大姐,问她8到10怎么念。大姐匆忙之中快速念了一遍,大概是觉得很荒唐,走没几步后特意停下吐槽。
“连这个都不会讲哦!”
阿里曼不好意思笑了笑。我迟疑了一下,也笑。
因为就在下午,他才和我们说起那些关于国语的往事。
【语】
国小之前,国语还没开始改造阿里曼的舌头。
上学之后,灵魂到舌头的距离变远了。那些不小心溜过舌头滑出嘴外的族语,在国语老师的耳中是收音机里一波又一波刺耳的杂讯干扰,老师会像操作旋钮一样,用食指和拇指掐起阿里曼(那时候他叫做伊曼,布农族未成年男子的称呼)手臂或大腿的一小撮皮肤,扭转,关掉族语,把国语扭进他的身体里。多年后,伊曼成了阿里曼,也早就过了当年国语老师的年纪,但那些一撮一撮的捏痕没有因为时间而消退。阿里曼抿了口热茶,轻抚大腿,笑叹说,“到现在都还有一些啊。”
高中时期的阿里曼到台中念书,住在学校宿舍,身边没有什么部落的人,他的舌完全适应了阴阳上去的波动,语言记忆库里国语词汇也远远多于族语。偶尔放假回到部落,去找朋友聊天,很多布农语他想都想不起来,一句话不夹杂国语无法表达完整,朋友们取笑他已经变成汉人了。东埔一邻海拔高,群山围绕,部落里常常弥漫着山雾,从台中回到这里,青春期的阿里曼会不会觉得族语比雾还要缥缈?
隔天,我们又到阿里曼的茶铺进行访谈。
茶铺位于八通关入口处的对面,是一间绿色铁皮和木板简单搭建而成的小屋。茶铺的外墙高高低低地种上多种植物,让这栋小屋乍看也像从土里长出来的。
阿里曼爱聊,也容易跑题。我们围坐在茶铺桌前,三番四次要把他这台话题永动机拉回正题——关于他和太太的茶叶生意的创业事迹。但他忽然提起我的身分,不受控地再次进入南岛语族认亲环节。
“你们的耳朵怎么说?”
他拉拉耳垂、指着眼睛、摸摸眉毛、指着鼻子、指着嘴巴,一一和我比对马来语和布农语的五官称呼。听起来的确相似,其中,眼睛是一模一样的,都叫mata。
Mata,眼睛,目光。
这个演变是怎么回事呢?几千年过去,南岛语族分散太平洋、印度洋各地,与台湾本岛几乎互不往来,mata一词无论是发音还是字义却毫无变化地保留下来,像是切分至最小单位、无法更动的终极本质。
说起眼耳鼻口,阿里曼想到另一件关于器官的往事。
那时他爸爸的肝脏出了问题,去看医生,阿里曼担任两人之间的翻译。医生问,哪里痛。阿里曼回复了一个单词,他的爸爸即刻破口大骂。
“因为肝脏叫做hatas,我讲成haztaz。”
“Haztaz是什么意思?”
阿里曼先和在场的女同学说声抱歉,然后指了指胯下,大家笑成一片。阿里曼也笑开了怀,摇摇头,面朝着店外八通关登山入口,三两个登山客正缓缓地走上去。阿里曼嘬一口茶,热茶滑过舌尖,乌龙茶的清香在口腔里蔓开。
【酒】
舌是声音的,当然也是味道的。
阿里曼现在是一位茶商,但在学会喝茶之前,阿里曼先学会喝酒。说学会,就是原本不会。在台中念书打工的那个阿里曼不会喝酒,或者说不爱喝酒,美秀姐多少也看上了他这一点——上教会,不喝酒,应该值得寄托终身。结婚后,阿里曼决定回家继承茶叶生意。这就等于要回到部落生活;回到部落生活,就等于要重新适应部落的习俗,或说人情世故。部落的耆老对他说,年轻人要回部落,要尊敬老人家,碰到老人家要喝一杯。
“慢慢喝一点啦!”
耆老的话不好违抗。
当时阿里曼乖顺地拿起酒瓶,把耆老的杯子一一添满,也把自己的杯子添满。耆老们一干而尽,阿里曼只吞了一小口,杯里还有半满。酒是苦的,阿里曼从小就这么觉得。小时候因为好奇心,看到爸爸和叔叔们喝他也要喝。爸爸让他喝一小口,那米酒才抵达舌尖,他的眉头就皱起来了,来不及吐出来,酒就顺滑地流进咽喉,苦的味道也从舌尖一路延绵到底,他的五官纠成一团,惹得大人们大大声地笑。他觉得羞愧,转身就跑。阿里曼说,他那时觉得,这么苦的东西为什么大人都爱喝啊。
阿里曼吞了一口酒,在耆老的注视下,他压抑住五官的扭曲。那么多年过去,米酒在他的舌头上还是毒药般苦楚,越是靠近咽喉越是难受。第一口吞下去,耆老们要他把杯子里的也干了。
“慢慢喝一点啦!”
一口接一口,一杯接一杯,阿里曼感觉酒都满到脑子里去了,头重重的,回家的路上,走路都走不好了。初回部落的那阵子,阿里曼在厌恶米酒的日子里一直喝米酒。
不久后的他就发现,喝酒也是一种语言,是族语也是国语,很多时候喝酒比说话还容易交谈。
喝酒,让他这个在都市打滚多年的少年,很快地融入部落人际网,很快,像一杯小米酒干下去那么快。阿里曼开始了喝酒生涯,早晚都喝酒,逢人就喝。到茶园上工之前,喝,放工回来,喝。喝得越多,阿里曼的朋友越多。连那些来他店里买茶的客人,阿里曼也以酒接待,先喝个四五瓶再来泡茶。有时客人谈得兴起,也买了四五瓶酒回敬。最后客人茶叶是有买,但阿里曼也送了不少,毕竟酒喝多了会让人格外大方,就像部落的人对他一样。
喝得越多,朋友越多,交游广阔的阿里曼甚至当上了东埔发展协会理事长,负责部落的许多对外事务。责任有了,交际更多,爱喝酒的声名随着他的交游而远播。不知道是谁先开始的叫的,理事长阿里曼有了新的外号,大家也觉得非常合适。
“理事酒!理事酒!”
名字是天生的,外号是挣来的。酒一天一天的,从舌尖灌到肠胃,染醉了阿里曼全身细胞,这下也外渗到阿里曼的名号里。他明明是回部落种茶卖茶的,却在部落里活得酒里酒外,没有人用茶来指称他。
“理事酒”的名号大了,荒唐事也多。有阵子他迷上巴西水晶洞,买了不少放在家里和店里。乡长来茶店里谈事情,一个下午,阿里曼和他不知交手多少酒与茶。阿里曼谈到自己的收藏,眉飞色舞,拉着乡长看这个看那个。乡长对最大座的水晶洞赞不绝口,赞它的色泽亮丽,赞它的结构繁复。阿里曼,理事酒,见乡长识货,他仿佛看见百年难遇的知音。酒浸过的舌是软的,挡不住任何话语的冲动,“送你!”阿里曼爽快地说。隔天酒醒,看着原本摆放水晶洞的位置变得空荡荡,阿里曼好后悔,他想起当初买下这座水晶洞的亢奋,心也空荡荡了。他拿起电话想跟乡长谈谈,想了想,还是算了,就当做喝酒的惩罚吧。(待续)
相关文章:
阿恩/阿里曼(下)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