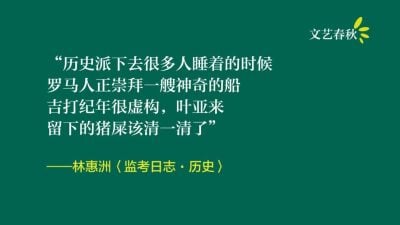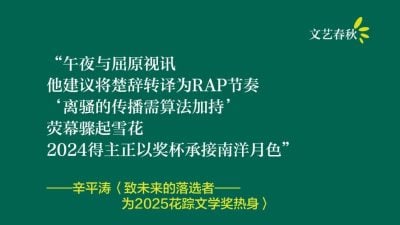树/张振皓(吉隆坡)



家外本该有三棵树——黄竹树、木瓜树,和一棵掩过那所处于草场边缘的幼儿园的大树。现在,只剩下了黄竹树一棵,显得寂寞;幸好香炉里的香还惦记着它。
说起这三棵树,就像一个家族的没落史。爷爷在世时,这三棵树过得挺好的,尤其是那棵不知名大树。几年前放学,我就见到外籍劳工身穿长袖,头包布巾,其中几个人用梯子爬上树,下面还有几个人在指点,最后那棵树连带着无言的树叶倒在大地怀里。
ADVERTISEMENT
我似乎听见那棵树的呐喊,却无法救下。平时我们很少关注这棵树,但是自从它被砍去,家里时常会有一股热意——是它之前一直在帮我们挡太阳。
本以为这种悲剧只出现在一棵树上,没曾想木瓜树“死”得更无辜。
木瓜树几乎每天都在生长,每过几天,奶奶便带着鸭子般的步伐走向屋子对面——那棵黄竹树后,把木瓜摘下。摘下的木瓜,有时是青色,有时是黄青色,我常好奇地问:“这熟了吗?”
奶奶总坐在电视机前说:“没有。早点摘好了。”苍老的眼皮及黝黑的肤色常让我看不清她的眼神。
后来我才知道,摘木瓜行动必须快,毕竟之前就发生过有人抢木瓜的事了。
树虽矮,但是木瓜甜得很,有时我还不免怀疑,这棵树是否被黄竹树前的香炉“净化”过。傍晚,那些木瓜就是我们的饭后甜点。奶奶把它们切块,放到碗里,里头再摆着小叉子,说是准备给我的。当时我还没搬家,奶奶家就热闹些,8个人坐在客厅,围着吃木瓜,甜意从舌尖散落到各个角落。
“甜吗?”奶奶时常这样问我。
“甜。”我咬着木瓜,舌头浸在饱满的果汁里,说出来的话都是幸福的。
这种欢乐不知什么时候就终止了。木瓜树的结局不了了之,它不知道去了哪里,或许是没有了心情去种,毕竟奶奶已不再年轻。我想黄竹树的下场也会如此。
黄竹树算是这个家成长的见证者。翻开陈旧的相册,就能看见父亲年轻时站在那棵黄竹树旁,当时旁边的草场一片空荡,只有看不清彼此的青草,父亲的笑容则在竹树旁绽放。那个年代,黄竹树树枝和我父亲一样高,竹叶则高过头顶,前方面对着的不只是我们家和一条马路,更重要的是一个香炉。
黄竹树是时代的幸存者
奶奶在竹树前搭了个小石台,上面放着白色香炉,香支的红末端一直都屹立在里头,即使拔除,次日仍见它们的身影。香炉大概是祭拜天神用的,所以每次饭前奶奶都会到那里上香。一到大日子,奶奶就会到竹树下,一个用砖头围起的烧炉烧金纸钱,这使我佩服起奶奶和爷爷的手工,几乎周围的东西都是他们自己搭起来的。
当天,奶奶会拿着一支细铁棒和火柴盒到对面的黄竹树下去,随后放两支红蜡烛在香炉石台上。点火时因为风大,加上奶奶的手有些颤抖,总需要花几分钟才能划出火来。直到蜡烛点好,烧炉起火后,奶奶就会拿出一叠金纸钱,双手摩擦着一叠,随后转出花形,这样才更容易燃烧。刺鼻的浓烟让我不自觉退后,黄竹树的叶子也在雄火中发抖。结束一切后,黄竹树周遭又恢复了宁静。
在我心里,那棵竹树似乎有点神圣。我觉得这棵树拥有神的力量,或者说,它就是神明。
黄竹树孤单的身影立在家门前,我饭后看着它,总觉得它是时代的幸存者。这种悲凉感,让我更想记录它。但也不只是它,甚至是木瓜树和大树,我也想记下。这样,至少往后能让它们留下自己凄美的身影。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