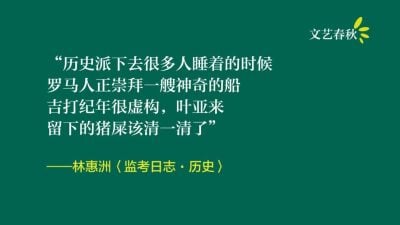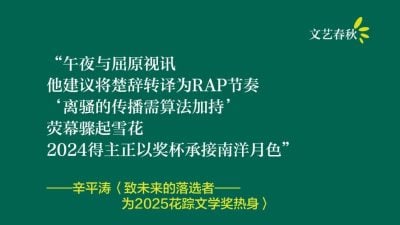张温怡/雨童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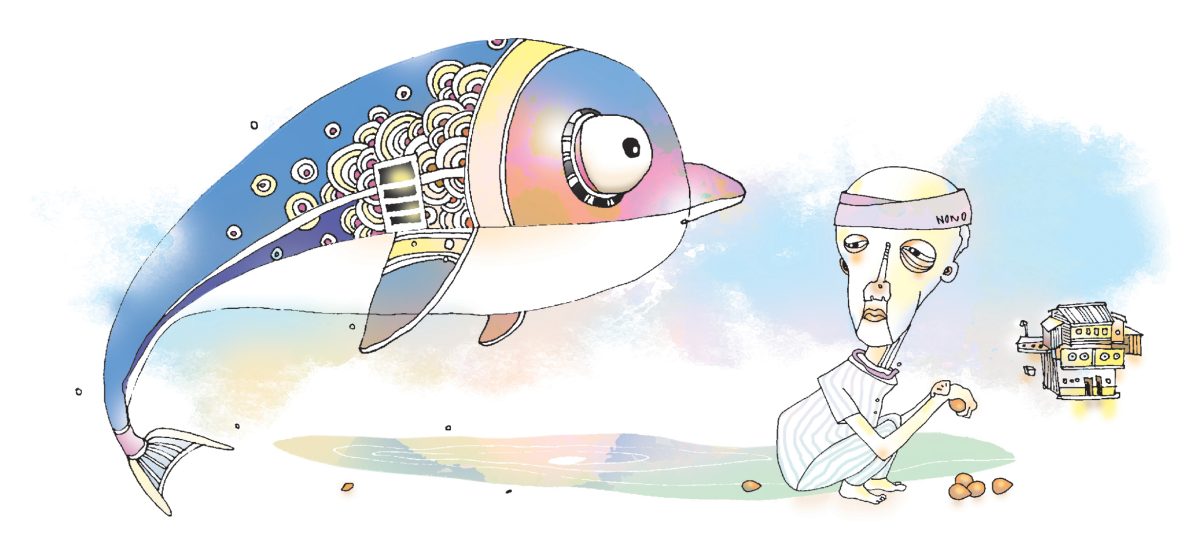
1.
爸从梦中清醒。摘下一颗印尼的蛇皮果。那已经是很深的夜,果子在冷咧的房间里像块冰,他握住那块要把自己冻死的东西,半身倚在床头。藏起冰块,双手缩进白色的被子,不让我发现几乎冻僵的手。
ADVERTISEMENT
里边其实藏着一颗几乎漏出体外的睾丸。15年前,他曾到过印尼故土,带了20颗蛇皮果。
爸说这些是村里摩托仔送的,放在家里后厨房底下。日光常晒着,蚂蚁也路过。因为太甜,家人不爱吃,爸每天晚上一个人剥皮。黑色果实像红毛丹,剥开就有白色果肉。像一朵花,分成几瓣,咬下去干涩沁舌,不像红毛丹多汁。妈看见他吃,念叨好久。
蛇皮果干又甜,难吃不要吃。爸后来双手藏在桌下,偷偷剥皮。偶藏不及,他用抹布遮住手,瞒着妈妈偷吃果。
妈妈根本不看他一眼,而他掩藏大半辈子。到了病房,被子突出一块蛇皮果状曲线,他把果子塞进裤裆里,佯装自己还是年轻时的样子。
20岁,我踢球跑步头一名。
木板做的屋院,走路噔噔作响,一群上半身赤裸的青少年在上面跑。跑过阿海,跑过老猴,跑过忧面,他们后来也都不见了。剩下爸一个人玩捉迷藏。
有时是厕所、码头、停车场。无人知晓,他去哪里。
睡裤印染一朵枯萎的玫瑰,染湿的月经片结出一块黑血。他怕死,哭着要我们救他。哄他好多遍,流血了别怕。平安无事,给他穿月经片,走路的时候,肛门出血,直到弄脏了裤子才换。他哭了,我们就会哄他。给他听歌。
热天的下晡
雄雄一阵西北雨
将阮沃甲澹糊糊
雨啊雨 雨啊雨
你哪会落遮粗
害阮煞覕无路
爸爸趴在床上,侧身起来走进厕所。连同假阳具也进去洗漱。我晃神,不小心睡了。醒来时,爸就没了。
爸,去哪儿?
天空逐渐亮色,从医院兜转三圈,亭子、休息室、等候的长龙不见他迅雷的身影。爸的肠疝压住身体,曾患腰伤,脊椎最后第七截异位,走路还是看不见,像飞的。不懂马来语,不识字,他能飞去哪里?
一通电话结束,医院的保安、姐妹们从很远的工作地点过来找爸。雨来了,窸窸窣窣敲打锌瓦。我在雨中找爸,水淋湿发梢和身体。湿透的衣服很冷,绕回病房,经过打针的地方,有个眼神涣散的病人,手插管。身边没人,自己对话。
停伫窗前,一直唱歌,鸟也没理他。
我和男子对视。他的脸有一瞬像爸,呆滞、瞳孔放大、微微开口,脸充满空洞。无法关闭的缝隙,我只是原地望着,直到男子突然口中吐出一句:燕鸟!燕鸟!它会飞。
他像孩子般笑,声音很洪亮,走廊回荡他的笑。手指着空气,麻雀从电线缆飞走。
湿漉漉的,雨停了又下。
下午,保安手拉住一个人,看上去很小一只,淋湿羽毛的鸟。紫色的病服湿了,爸爸微颤身子,拖着鞋子,地面留下灰色的脚印,脏水的痕迹。只有前半只脚丫,拖出一条蜿蜒曲折的水陆。
雨水来临之际,飞鸟只能拖着脚走。像断了腿,我牵着爸,两只湿嗒嗒的胳膊,从底层直达病房13楼,37号病床,距离窗户最近的位子。有个老母亲守在床位,隔壁是个瘦如干柴的巫裔男子,乍看约莫三十。
老母亲占着电视,将音量调至最大,是一出马来喜剧。
爸爸看不懂,旁边的女人自顾自地笑,一边对儿子重复台词。
男子只露出额头,那张脸太白,像尸体没血色。
医院很冷,像关在太平间似的。
爸爸换好衣服,不停颤抖,很冷要回家。
阿怡,我们快回家,叫车。每小时,我在医院三天,被爸一直吵醒。
带爸爸走走,下楼还要瞒着保安、护士。病人不可以出去,我骗保安只是下楼吃饭。早上6点绕到8点,我们躲在无人大厅,斋戒月没人上班。大厅有张休息椅子,中间有个迷你公园,我们聊天,看麻雀飞来飞走。
同样的故事,我听他说无数次。
他一生有四次被海吃掉。
乌索索蜿蜒小路,长着嘴巴,地用木做的。一到夜里什么也看不见,村里的人黑黝黝,赤脚裸身走在大街。身体总是充满咸味,沾染海的气味。从海的嘴巴出来,但不是每个掉进去的人都活跳跳。
雨季来临时,那里充满尸语。
大白灯,走马灯。爸爸说总会经历这些。途经村路,都亮着白灯。那年代的贫瘠之地,只有逢上白事才用得上灯泡。爸觉得,这些灯时常出现。光照进来的时候,他只好拉下窗帘,隔绝所有光源。整个房间犹如乌云密布的阴天。
他依稀记得,阿公走的时候,喉结发抖厉害。像是有股力量,割下咽喉。从此,阿公的声音就落在他了无生息钟摆。
某日雨天,他睡得昏沉,梦见穿着白色背心、长至膝盖的短裤、不合脚的橡胶拖鞋的阿公。走到桥头,阿公脱下鞋子,一只手搭在木柱跳入船只。
阿公和他说,下海前,要先学在船上走路。船摇摇晃晃的,他随工头到远方岛屿捞世界,呕吐物吐到一半,剩下的吞进喉咙。爸初学捕鱼,觉得晕晕的。连续两星期,夜深如白天。走路东歪西倒,后来真的掉进海里,误吞了海水。雨常年累月下着,一滴滴液态的灵魂从天而降。
而爸爸的身体装满不同灵魂。
夜深的爸爸从屏风探出头,站在床上,这次真的能站立了,不摇晃了。
爸爸头绑着毛巾,病房的灯光照在头顶,烧光四周的黑暗。
那时明明是雨季,房内燠热。爸爸睡不着,拿着手机四处拍照,拍到一艘小型渔船,他坐过这艘船。渔网是他织的,一对母子正睡在那里。
爸说,就是为了跳船才被海吞掉。
小伙伴要冲凉,一个个跳进去大海。爸爸学旁人跳海,掉进海的嘴巴。碰的一声。雨从天空垂钓,打捞一具具尸体,被丝线钩住的鱼拼命挣扎。
几乎奄奄一息。他掉入深不见底的雨池中,嗜水的阿伯将他打捞上岸,说这孩子藏得太深,再多一会儿就找不到。
脑袋磕了一下,雨很快洗掉污浊的血。
爸爸说走马灯时看见坟墓。有番仔拿锄头挖土埋尸。
番仔弄来许多枯草,编织成草席,卷起尸,一点点埋尸。雨季来临时不会有人发现村里又死了人。偶尔,有人在河里发现尸体,死了很久才浮出水面。
而那里的渔夫捞的不只是鱼。
听阿伯说,番仔不只埋尸,还会抛尸。有的将半死不活的人绑在一块大石头,从船上抛到海里。入海的人从不冲凉,皮肤脏兮兮的,争斗的痕迹。
泡水里久了会发肿。谁也认不清落难者身分。
一堆同品种的鱼,死在同一片海域。
不出远航的渔夫,永远捞不到其他品种。雨季更见不到鱼。
爸爸雨季前会出远。有时很久才回来。回来时刚好下雨,经过马路,走在行人街道上,会有路人嫌弃咸咸的海水气味。
雨中行人纷纷打伞,爸在雨中沐浴。一时间,他也分不清自己淋过头,发烧好久,身体怕冷。哪里也去不了,呆在一个地方很久。不知道回家的路。
阿伯说,有的人藏得深,在雨中或许更难找到。
爸爸走丢时,一家人来到码头找爸。雨打湿衣襟,路人如同川流反方向穿过我们。
爸爸蜷缩在码头的亭子一角。缩在一头油垢的银发里的,打湿羽毛的鸟儿,飞不起来了,好久发出一声低吟。
16岁的时候,爸爸带我逃税,被抓坐监牢,关半年。
19岁的时候,他们又抓我,我没在国庆时出海,他们还是抓我。没钱,拿去关半年12天。
我做过两次牢,做过两次牢。
爸爸一直念给我们听,湿湿的水滴落我的衣襟。爸爸继续说,没有停。雨也一直下,整夜未休。
没人能懂,它何时才能停。
2.
雨来的时候,所有不好的记忆都会翻涌而起。
某次他在寻找断指。
船开一阵,浪花四溅。我们去爸爸曾住的地方看看。吉胆岛要坐船去。我和他坐一块。坐在快艇的爸爸很安静,看着阳光,看着风景,看着皮肤,看着老人斑,思考生,思考死,思考从前,思考苦痛。
他用右手抚摸左手,伸出断掉的中指,和我说坠海的事。
他开始坠入时间交错的河流。
那时候病的太重,怀疑得蚊症。他掉进黑黑的海,感觉现实看到的却是很浅的水洼,被人打晕才会这样。
继母投诉阿公,说爸爸无礼,我的阿公拿着大木板从他后脑勺敲去,晕晕的,看什么都会动。又病又痛,云朵像歌仔戏演员旋转跳舞。走到桥的尽头,他头盖往下坠落海中。
之前见到的阿伯又出来,但在梦里他不说话了。阿伯和他玩打狗牌,抽剩的香烟盒子排成一列,黑狗,杂狗。橡皮圈猛的一碰,谁赢谁就先走出一堆枯杂草的地方。爸爸以前没少玩,很快就赢阿伯。走的时候,阿伯后来只说不要转头,直直走。
来到杀鱼的船只,表叔举着屠刀,另一只手捡起鱼尾巴,丢到另一旁分类。渔网有不同的鱼种,爸爸继续赶工,另一张网还在海中,还未拖上岸。
碰的一声,船卡住了。一条海豚被渔网缠绕身体,表叔急忙拿起屠刀,想一刀砍断它的尾巴。爸爸跳进海里,还在奋力解开缠住的渔网。海豚受惊发起疯,尾巴重重打在爸爸头上。
爸爸瞬间不省人事,沉入海中。(8月12日续)
相关文章:
张温怡/雨童说(下)
张温怡/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