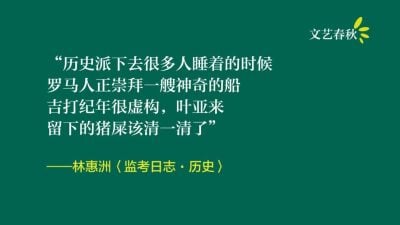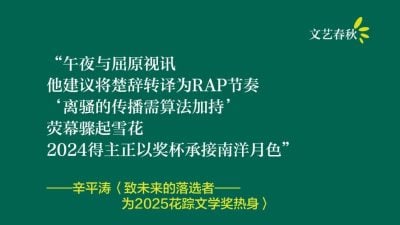【蒙面暂记】AI代笔,恶托邦找上你/周若涛



前阵子给了一场科幻文学讲座,提及《1984》和《美丽新世界》两本著作,有学生问道:“‘乌托邦’与‘恶托邦’,何者更适合用于新诗创作?”我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即席应答向来是我的死穴。过后这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像苍蝇挥之不去。直到某天,车里随机播放的播客传来一段相似的对话。那是《纽约时报》评论人Ezra Klein对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的访谈。Ezra问,为何爱特伍笔下多是恶托邦,却从不触及乌托邦?
这不太巧了吗?让爱特伍来回答这问题,比我高明何止百倍?那位聪敏的同学,忘掉我的胡言乱语吧,赶紧上《纽约时报》一听究竟。
ADVERTISEMENT
爱特伍是这么说的:乌托邦文学盛行于19世纪。那是一个大发现与大发明的时代:微生物学革新了卫生医学、蒸气机加速了生产、飞机与潜艇拓展了探险的边界。人们对未来满怀憧憬,乌托邦文学因而蔚为风潮。然而,到了20世纪末,就无人问津了。为什么?因为太多于现实中推行的“乌托邦”实验,最后都演变成极权“恶托邦”。苏联、纳粹德国、毛治下的中国,都曾许诺一个乌托邦,但前提却是,必须把“异己”尽数铲除。我之乌托邦,彼之恶托邦。
沿着爱特伍的历史脉络,我们不妨审视本区域。上世纪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那些开邦立国的愿景,依稀也有乌托邦式的语言在运作。但东南亚的民族构成原就复杂,要如何抹平差异,让各群体符合单一模子?于是,在一些国家,那些与主旋律相左的“异己”或被屠戮,或被强制同化。马来西亚呢,最初也有一个“多元共荣”的乌托邦理想,但很快变质,被另一套乌托邦取代了。我的乌托邦,比你的乌托邦,更乌托邦。
人类放弃最可贵的思考能力
但如今乌托邦真的像爱特伍所说,“无人问津”了吗?她说的,是针对文学而言。在现实世界里,乌托邦式的语言正甚嚣尘上呢。诸如“让XX再次伟大”“XX民族的伟大复兴”口号,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会让鸡皮疙瘩掉一地,在政治文宣里却让人如打鸡血,精神大振。此类语言,马来西亚人当然再熟悉不过。
民族/国族之外,另一套乌托邦语言,就是宗教。任何国家只要与其中一种沾上边,就鸡犬不宁了。马来西亚得天独厚,两者兼具,何其有幸。
然而,一个更强大的乌托邦正如天魔降临。19世纪对科技的乐观主义,借着AI又死灰复燃。AI能让产能大增、治愈百病、促成文明大跃进、人人躺平白领薪金……但科技巨头们的大外宣还没兑现,更严重的危机已悄然浮现。
我说的,是AI代笔。这问题不仅仅关乎写作业、交报告,或投稿。书写,原是把思想反复锻造、粹炼、深化的不二法门。AI代笔如同把思考外包,主动放弃人类最可贵的能力。如果压制异见是所有恶托邦的本性,那在AI加持下,异见甚至无从萌芽,因为思想本身已被消解。非常《美丽新世界》,只是手段更隐晦。
如此,我或许还能针对那位同学的提问,再添一二言。文学,为沉默者发声,为无形者赋形。它抗拒潮流,是异质的艺术。因此,真诚的书写,无论题材是否“恶托邦”,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一种延缓恶托邦降临的力量。
诗,尤是。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