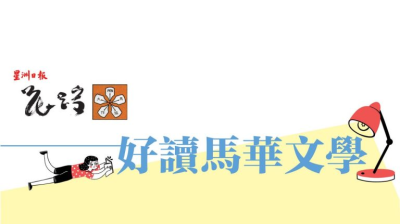告別的那天風很輕



我第一次觉得风是轻的,不是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而是在告别的那天。
那天我站在殡仪馆外面,风吹过额发,没有把我吹得睁不开眼,只是轻轻绕过耳后,像是谁来安慰我,又怕我察觉。
外婆是在凌晨3点走的。医院打来电话的时候,妈妈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我也看着电话发呆,脑子里是空白的,连哭都忘了怎么开始。
她走得很安静,像在熟睡。我记得前一天我握着她的手,她指尖还温热。她没说话,眼睛半闭着,只在我快走的时候,眼角滑出一滴泪。我以为那是生理反应,可现在想来,也许她是知道自己撑不过今夜了。
外婆喜欢风。
她家的后院种了一棵风铃木,每次风一吹,细碎的声音就洒满整条巷子。小时候我总是坐在她的藤椅上,听风吹过树叶时发出的沙沙声响,她就给我削苹果,一边削一边说:“风轻一点,声音才好听。”
外婆的葬礼安排得很简单,她向来不喜欢热闹。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所有人穿黑衣服,只有我带了外婆最爱的那条浅粉色丝巾。妈妈说不合规矩,但我坚持带了。我不太懂规矩,我只知道外婆生前喜欢那条丝巾,尤其是风起时,她会披上它走去院子里,丝巾随风飘扬,与身后的风铃木融为一体。
整个仪式我都没怎么哭。不是不难过,是太难过了,反而哭不出来。亲戚们轮流说话,主持人读悼词,说外婆一生朴素、善良,是个好母亲,好外婆。我站在最角落的位置,望着那个盖着白布的棺木,有一瞬间,我好像听见树叶摩擦的声音。
没有风铃木,只有风。但我知道那是她在回应我,像小时候我在房间里喊她:“外婆──”她总在厨房里用微弱的声音答应:“哎──”
我开始意识到,人的离开,不是一下子全部失去,而是慢慢消失的。
那天之后,家里饭桌上少了一副筷子;后院的花无人修剪;电视机调不到她喜欢的老戏;厨房的柜子里,泡着她没来得及喝的菊花茶。
看着电视机,我想起外婆其实很爱看偶像剧,但每次被我撞见她都装作不屑:“哼,小孩子演的戏有什么好看的。”但每次我放学回来,她又坐在电视机前,神情比我还认真。
又比如说收拾遗物时看到我送她的新裙子,还记得她说我浪费钱,说她一把年纪了,不喜欢穿裙子了,可第二天,我看见她穿着那条裙子在镜子前,摆着几个姿势臭美,笑容压都压不住。
所有的“她”,都慢慢变成“她留下的东西”。
几天后,我回了学校。
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把外婆给我的信翻出来读。那封信是她住院前写的,她让我过得自由一点,不要太懂事,也别太快长大。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说不定哪天就忘了你。但你要记得我,我很喜欢你出生的那个晚上,窗外的风轻轻地,很像现在。”
她写得歪歪扭扭,结尾画了一朵花。我在纸上描了一遍又一遍,铅笔芯都被磨平了。
有时候我觉得外婆并没有走。她只是换了一个方式陪着我——比如我跑步的时候,风从耳边擦过,像她温柔的呼吸;我走夜路的时候,风吹过树叶,像她轻声唤我名字。
再比如今天,考试结束后我站在校门口发呆,风忽然轻轻拂过脸,我下意识转过头,看到远处有一棵风铃木。我看着风铃木发呆,终于闭上眼,任由风在我脸上胡闹,嘴角却不由自主地微微抬起。
沙沙声轻轻响起,不惊不扰,就像从前,她坐在椅子上,阳光照在丝巾上,她看着我,眼睛总是弯弯的笑着。
我终于哭了,是因为风吹过我耳边时,我伸手想把风抓住,它却悄无声息从我指缝溜走。
那风不大,甚至不够把我头发吹乱。但我知道,那是外婆回来看我了。
她还是喜欢轻的风。

【林健文点评】
这是一篇感性度很高的散文。作者用了风(轻风)、风铃木来描写已逝的外婆。整体的书写流畅度很高,甚至用字也有考虑到和“轻”配合,但也有一些地方可以斟酌。
第一段有提到“第一次”,所以最后一段可以写“最后一次”(或用葬礼结尾)来闭环。
“我开始意识到,人的离开,不是一下子全部失去,而是慢慢消失的。”这一段写得很好,也是整篇散文的核心。要是可能的话,可以慢慢说。一点一点把外婆和风铃木、风的关系说得仔细一些,然后慢慢在叙述里让它离去。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